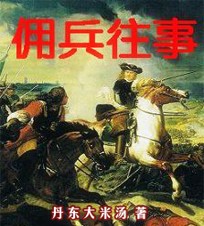书店情欲往事-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透过后视镜看着我,我也觉得说话时太一本正经了,正经得不太像我自己了,就赶紧点上一支烟掩饰一下,自己吸一口,也让罗素吸上一口。
晚饭后,罗素硬拉着我去参加一个沙龙,过去我们曾去过几次,就是上一回谈戴望舒的那个庭院沙龙。因为下午阴天,所以改在晚上的室内进行。这次的主题是“清华园·1932”,主要讨论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
东道主是个房地产公司经理,总以儒商自居,喜欢附庸风雅什么的,罗素何以跟这样的人打得火热,让我费解。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像化装舞会似的,据说目的是为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依我看,其实就是一种游戏心态作祟,本来与会者就都是些闲人,而且是些中产阶层的闲人。分给我的面具是一只狼,我立马儿成了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罗素选择了一个狐狸的面具,她说她喜欢狐狸,因为狐狸是美丽而妩媚的化身。她带着一种学究式的热情,穿梭于豺狼虎豹之间,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她一定觉得这里比动物园更好玩。
室内一片喧哗,所有人都像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似的,跟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亲昵得一塌糊涂,吴宓不叫吴宓,叫雨僧先生,朱自清也不叫朱自清,而叫佩弦师,给我的感觉,特言不由衷,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的那本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嘲讽的那样:说话的人说的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像鸭子呱呱叫一样。
我找个角落坐下来,在所有的热闹场合,我都习惯找个角落坐着,而且是一脸乏味的神情,不,我不是觉得三十年代的清华园乏味,相反,我十分向往那里。过去的清华园旁听之风甚盛,许多没考上清华的学生趋之若鹜,授课老师也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据说,只有冰心是个例外,那时她也才三十出头,每次登上讲台,都像狮子似的吼一嗓子: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于是,选修生留下来,而旁听生都被赶出去。不过,晚年的冰心倒是个慈祥的老太太。乏味的其实是沙龙里这些夸夸其谈的人。
“当年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以后由自己挑,这很科学,起码比现在科学,你以为呢?”跟我邻桌的一个戴兔子面具的人,侧过身子来跟我攀谈,听声音像是人到中年的样子。
“对不起,对这个话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当年还没我呢。”我说,如果他撩开我的面具,就会看到我紧皱的眉头和含着冷笑的嘴角,“当年我若能跟季羡林他们一起去旁听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那么我现而今起码也有九十岁了。”
“难道浦江清和季羡林两位先生的日记,你也没读过吗?”对方似乎很惊讶,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听说一个记者不知道范长江或是听说一个诗人不知道里尔克似的。他摇摇头,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一定是一脸的遗憾无疑。
“我确实没读过。”我点点头,还要继续说下去,被罗素阻截了,她狠狠地掐我一把,笑着对中年人说,“他是跟您开玩笑,两本日记他都读过,我们还常在一起探讨呢。”“噢,我想也是,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加入到这个沙龙里来呢?”中年人又仔仔细细地看我一眼,似乎仍是半信半疑。罗素压低声音警告我:“你装什么白痴,不怕人家看不起你吗!”我瞟她一下说,“我应该看不起他们才对。”她说,“人家都是些商界精英。”我说,“既是商界精英就去商界混好了,还来冒充文化先锋干吗?”这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争执,那个人说,“诸位,你们注意到没有,浦江清的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说叶公超、朱佩弦几个人吃饭,喝法国酒,吃菊花火锅。我觉得此处很不合规矩,要喝法国酒,就该吃牡蛎;要吃菊花火锅呢,则应喝陈年花雕,对不对!”一屋子人齐声响应,我猜,说话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位做房地产生意的东道主。
“你所说的精英,就是这类货色,简直是拿着肉麻当有趣。”我凑近罗素的耳边嘟嘟囔囔地说道。这间客厅里,挂满了名人字画,而且绝对是真迹,十之八九是从拍卖会拍来的,可是摆得欠讲究,仿佛把一堆宋版书垛成一座小山,自然也就显不出宋版书的珍贵了,整个一堆废纸。
“有风凉话回去说,好不好,现在你给我闭上你的嘴。”罗素生气了,又不愿让人看出来她在生气,嘴上恶狠狠地说着,脸上却挂着柔和的笑容,因为戴着面具,笑容只能感觉到,但看不到。她越是这样,我就越反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你怎变得这么没性格了?”我说。
“以后再告诉你。”
好吧,和为贵,忍为高。我起身走到墙边的一溜书架跟前,想看看书,都是些大部头的精装本,因为太新,从没人翻过,我也不好随便乱翻。
我在书架跟前逗留的时候,罗素又与那些人应酬了一阵,然后才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悄声对我说,“我们到阳台上去透透气。”阳台很宽敞,空气很清爽,可以尽情地吐出体内的二氧化碳。我们摘下面具,终于从动物世界里走出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喜欢这些人。”罗素说。她的脸颊挨得这么近,我都能闻到她的体香,是罂粟花的味道——所有美丽的女人都有这种味道。
“我厌恶他们俗不可耐的样子,你居然还要去取悦他们。”我一边抽烟一边说。她辩驳说她没有取悦谁,我坚持说她确实那么做了。接着,不知是谁主动,我们拥抱在一起,并且吻了起来,不过,时间不长,因为随时都会有人到阳台上来抽烟什么的。我们吻得十分冷静,似乎没有任何的欲望元素,跟手牵手差不多。
“你知道,我正在做毕业论文,我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假如我不能留校教书的话,我就得找一份工作。”罗素说,“要找工作,就难免得跟这里的这些人打交道。”很难想象,这么世故的话会出自无忧无虑的罗素之口,真的很难想象,我一直以为她只是生活在她的青春里。
“真没想到你心里藏着那么多的阴谋诡计。”我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说,面容也一定随着发生了不可言喻的变化,因为我看到了罗素惊异的目光。
“你一天到晚生活在故纸堆里,好像跟现实完全脱节了似的,”罗素白了我一眼,振振有辞地说,“我们的第一需要是生存,其次才是别的。”
“生存也要有尊严,不能靠媚俗来活着——媚俗是可耻的。”我的声音竟如此的激奋,不禁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显然,罗素比我更吃惊,她凝视了我老半天,表情特酷,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无情。
“媚俗是可耻的,孤独者更是可耻的!”她说,“依我看,那些旧书没能给你什么智慧,只是让你变得迂腐了。”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迂腐,只是你才发现就是了。”我用一种平静得近乎于很不自然的口吻说,其实我是不想跟她吵的,我觉得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比较好。
“是我瞎了眼!”罗素气鼓鼓地瞪着我,胸脯一起一伏,显然已经怒火三千丈了。
我火上浇油般地说了一句:“对不起,不幸被你言中了,你的视力确实有问题。”我坐到阳台上的躺椅上,双手交叉抱住膝盖,好像破罐子破摔似的又补充道:“不过,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谢谢你的建议,”罗素咬牙切齿地说,“我会考虑的。”
罗素气急败坏地抓起阳台茶几上的面具,掉头就走,我张开双臂拦住她的去路。她说,“我不会原谅你,不论怎么求我。”我平淡地说,“别误会,我没有求你的意思。”她说,“那你拦着我干吗?”我指了指她手中的面具,说道,“你拿错了面具,你的狐狸脸在那儿呢。”我递给她,她狠狠地哼了一声,回到客厅去了。
从沙龙出来,已经夜深了,罗素匆匆地在前面走,我只好跟在后边,都保持着沉默。来到别墅区外面的公路上,罗素说她回学校,要准备一些论文资料,这时候,有出租车开过来,她招手示意。
我知道她正在气头上,拦也拦不住,就很绅士地搂了搂她的肩,说道,“别介意我刚才的话,回去早点儿休息,不要睡得太晚。”
“你也是,拜拜。”罗素钻进车子,招招手就扬长而去。我愣愣地站在那,目送她远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俩变得越来越生疏了,而且都学会了装模作样,“见鬼,他妈的怎么会这样!”我骂了一句。
一夜都在做梦,断断续续地做那种一醒就被忘却的梦。还是“麦当娜”把我吵醒的,它喵喵叫着,近似于歇斯底里,同时还用尖锐的爪子拼命地挠床帮,轰也轰不走。“麦当娜”的坚韧不拔终于征服了我,我只好慢吞吞地坐起来。
“你真可恨。”我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谴责了“麦当娜”一句。“麦当娜”冲我眨巴眨巴眼睛,依然喵喵叫,脖颈周围的毛发都一根根地竖起来,好像跟我有什么话说。
哦,原来是有人来电话,因为睡觉前我把手机调到震动上,所以铃没响,“麦当娜”一定是见到手机自己在桌上跳舞,给吓坏了,赶紧叫醒我,直到我光着脚丫下了地,将电话拿起来,它才安静下来,摇摇尾巴走开了。
我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故意操着四川话问道,“你是哪一个?”我的话音未落,就听见柳彬震耳欲聋的吼声,“这么半天也他妈的不接电话,你小子钻耗子洞里去了!”震耳朵,我赶紧把电话离耳朵远一点儿。
“你这只夜猫子,怎么一大早就跑出来了?”我问。
“我在机场呢,一会儿飞乌鲁木齐,特意跟你告个别。”柳彬显得特亢奋,嗓门比帕瓦罗蒂还豁亮。
“早干吗去了,临上飞机了才想起来跟我告别,太他妈的不仗义了吧?”我嘴里不干不净地发泄着不满。柳彬连忙解释说,“前些日子一直瞎忙,做各种准备工作。再说,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我们又可以一起去喝啤酒了。”但愿如此,不过,一想到柳彬独自一人踏上荒凉的路,还是满难受的,像有一群蚂蚁在蚕食着我的心。
拉开窗帘,见窗外阳光明媚,是个飞行的好天气。我对他说,“哥儿们早点儿回来,兄弟等着你。”“最好是买好一打啤酒等着我,咱们来他个一醉方休。”他兴高采烈地说。“行,一言为定。”我说。柳彬还说他担心进入沙漠地带以后,手机没有信号,恐怕就联络不上了,不过,“我可以给你写信,你可不能挑我的语法毛病。”他打趣说。我笑着说:“不会的,接到你的信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问:“罗素在不在你那儿?”我说不在,她在学校。他说,“那么,你代我问候她。”我说好的。
“麦当娜”大概是饿了,一个劲儿围着我的腿绕来绕去,冲着我直叫唤。我把食指竖在唇边,小声说:“嘘,过一会儿就开饭,你再稍微忍耐一下。”
“你跟谁说话呢,是不是又新泡上一个小妞,把罗素给甩了?”柳彬的耳朵跟克格勃一样尖。
“你以为我像你呢!”我说。
“不对,我刚才听你跟谁说话来着。”
“好,我知道瞒不了你,跟我说话的是一个歌星,叫麦当娜,”我开玩笑说,“也许它的代表作你听过——《喵喵之歌》。”
“操,别逗了。”
“真的,”我嘿嘿笑着,“它就睡我旁边,跟我同居有些日子了。”
“就你那身子骨还想睡麦当娜,麦当娜睡你差不多了……喂,不跟你说啦哥儿们,马上就要安检了。”他挂了电话,我朝“麦当娜”努努嘴说,“走,吃早餐去。”
没想到,罗素比我来得要早,店门就是她开的。她正跟常来常往的两位“半老徐爹”聊天,见我进来竟没有任何反应,仿佛进来的是一缕空气似的,熟视无睹,倒是两位“半老徐爹”亲热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我知道,她和顾客的这种热情洋溢是做出来给我看的,是因为昨晚的事情向我示威。好吧,还来劲儿了,那么就针尖对麦芒好了,只要不动干戈,或者无须大动干戈,我会奉陪到底的。
我到书店尽头的一个角落去修补旧书,用夹板矫正变形的书脊,用熨斗熨平折角的内页,虽默默地做,动作却极度夸张,肢体语言跟指挥一首交响诗的指挥一样,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小桥流水,我还时不时地偷偷瞟上罗素一眼,我猜,她对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心里明镜似的,一定特恼火。
“你买的这本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远不如刘呐鸥的那本《都市风景线》有价值,如果让我评定谁是新感觉派圣手的话,我宁愿选后者而不是前者——只有傻瓜才会拿前者当天才看。”她虽然表面上是跟顾客侃侃而谈,其实,我知道她是故意气我,因为我正是她所说的那个傻瓜。
在我的记忆中,罗素是很少跟顾客攀谈的,今天好像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她不但谈起来没完,而且还谈得眉飞色舞,我平时喜欢的作家,她一律给予抨击,而我所讨厌的那些作家,她都褒奖有加。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她摆明了要跟我针锋相对。
看来,我们的敌对关系只好继续下去了,我想,我是能够继续下去的,只是能够继续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准。我一边干活儿,一边哼着歌,尽可能地不去听她谈的是什么,也许是为向她表明我并不在乎她谈的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唱的是谁的歌,但是音量和音质绝对可以跟臧天朔相媲美。
罗素则干脆把留声机的声音放到最大,企图以绝对优势压倒我,几个只看不买、拿书店当阅览室的顾客,可能实在受不了屋里的双重噪音了,相继逃之夭夭了。
这时候,两位跟罗素聊天的“半老徐爹”也觉出气氛有些异样,他们唯一的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赶紧走开,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书店一下子空旷多了,只剩下我和她,还有鹦鹉。我停止了歌唱,我的声带累坏了,火辣辣地难受;而她也立刻把留声机关掉,她是耳鼓受不了啦。可能是从喧嚣中一下子走进寂静,有点儿猝不及防,所以我们俩的表情都很特别,特别难以适应。
我们俩下意识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