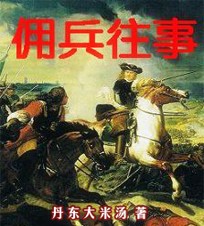书店情欲往事-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他如醉如痴的样子,我也备感欣慰,眯眯笑着,两条腿悠然地颠蹬着,像是戏迷在欣赏名角做戏。为犒赏我,老头儿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知道老头儿的性子,有点儿怪,见谁喝一杯可乐或抽一支“三五”,就说人家和平演变了。所以,有白开水喝,便已不错,属于破格提拔了。
然后,老头儿就追问,书是从哪里淘换来的,又问花了多少钱,我一五一十告知于他,老头儿仍是不依不饶,直问得我答不上来为止。“真不敢相信,得来的竟这么容易。”老头儿是想笑的,可是笑不出来,眼圈倒湿润了,嗓音嘶哑地说,“我为这几本书,花过多少心思,费过多少口舌,跑过多少腿儿……”
我问:“难道您不高兴?”老头儿独身一人,一箪食,一瓢饮,屋内摆设至今仍保持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遗风。许是受了老头儿的感染,我心境也不免纯简而端然许多。
“如愿以偿,当然高兴,高兴极了。”老头儿说着,声音已是颤颤巍巍,“只是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跟白日做梦一样。”
“您辛辛苦苦收集,收集这些左翼作家的书长达三十年,就差这么几本了,”我说,“而今总算功德圆满,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终于齐了,终于收集齐了,你小子说得在理……”老头儿摩挲着他的藏书,表情比神甫祈祷时还庄严神圣。房间里,贴墙环立了十余个书架,书架是特制的,宽大,高至屋顶,若取上端的书,须登梯才够得着。架中的书除了初版本而外,还有影印本和手抄本,都是心血。
老头儿小心翼翼地将书插进书架,仍迷醉般地抚着书脊,仿佛抚着葳蕤花叶。老头儿很君子地回赠我一本萧红的文生版《商市街》和一叠民国初年的藏书票。萧红和藏书票都是我喜欢的,我觉得挺划算。
我以为我这次是给老头儿帮了忙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我搞糊涂了,糊涂得不知自己办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一个男人说是你的老同学,找你,他叫赵楚。”罗素的电话竟打到许佩祈那里。
赵楚是我十年未谋面的同窗好友,一起没少淘气,登时诸多儿时的温馨涌于心头。我一边匆匆往回赶,一边嘱咐罗素:“叫他等着我,马上就到。”
见到赵楚,真有点儿动感情——十年不见,黑了,瘦了,沧桑了。拥抱一下是一定的,然后促膝而坐,我连珠炮似的只顾嘘寒问暖,毕竟久了,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大概罗素还没见我这么兴奋过,饶有趣味地在旁看着热闹。
赵楚倒显稳重多了,浅浅地笑。趁我沏茶倒水的时候,他才开口说话,“已经混成老板了,看来,你经济状况不错。”我忙说,“托您的福,还成,还成。”跟着,他从公文包里掏出许多的表格,摊在我面前——
这是什么?我正诧异间,赵楚已把钢笔备好,用牙咬下笔帽,硬塞进我手里,说道:“有俩钱,别乱花,多想想身后事是正经。这是保险单,我建议你,买一份人寿保险,将来老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之后,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上保险的种种好处,抑扬顿挫,激昂非常。
“还是老朋友替我想得周到。”我草草签了表格,推一边去,也好继续畅叙友情。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老同学这个如何、那个怎样,连罗素几次在桌下踩我的脚,都没去理睬。
赵楚把表格上下审阅一个够,又指点我改动几处,才精心收起,如释重负般地吁出一口气:“你把款子准备好,改天我来取。”说罢,竟坐也不坐,拍拍我的肩膀,要走。
“老九不能走啊,我弄些酒菜,咱们聊个痛快多好。”我挽留再三,赵楚还是走了,这让我很失望。
“你不知道,小时候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光屁股的交情。”我仍然意犹未尽,无限感慨地对罗素说。罗素却使劲儿撇撇嘴儿,一脸的不屑,“万喜良,傻吧你!”
咦,什么意思?今天阴转多云,罗素也显得反常。这时候,我养的那只鹦鹉突然仿着孔乙己的腔调说了一句: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店堂里的仨俩顾客都笑了。这是我精心调教的,绍兴口音极纯。可惜,就会这么一句。
罗素掀开记事簿,跟我交代我不在时谁取走什么书,谁又托我找什么书,还有工商局要我们订阅什么报,虽琐琐碎碎,但她都打理得清清明明。幸亏有她相助。
在我粘补残书的时候,宣纸、胶带及糨糊摊一桌子,罗素照例是该出手时不出手,兀自托着腮凝望一处,若有所思的样子,很是冷艳,像胡兰成说张爱玲的那样: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如同数学,而她的艳亦像数学的无限。因为是周末,甜妞来电话说要过来吃饭,电话虽是老式摇把的外壳,机芯却是新的,可还是嘎嘎的响,须大声才听得到,罗素这才竖起食指在嘴边,示意我小声点儿。
“其实,她并不适合你。”冷不丁,罗素丢出这么一句,我知道指的是甜妞,待闻其详,她又不语了,仍是托着腮的架势,宛若临水照花人,不过,仿佛隔着厚厚的雾。
我们——我说的是我和甜妞,此时此刻,刚吃饱,面对面坐着,听米卢在电视里兜售他的“快乐足球”。指望我跟她两人并坐一起看看书或手牵手逛逛街,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除了做爱,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充满着世俗的平和,才是她的所爱。
我以为太过庸常。
这些年,若即若离挂牵着,两人的情感发展史总掀不到新的篇章,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知道,她是个表里不一的女孩儿,老是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用“一半火焰,一半海水”来形容似最为恰当。我认为是一种恶习,纵容不得。有时她生气,明知哄哄就好,也偏不。
碗筷收拾停当,赶紧上床,这已成为例行公事。忙着去淋浴,浴后我就这么赤条条地在屋里荡来荡去,甜妞笑我是暴露狂,我亦笑,笑她有窥阴癖。她洗澡总是很慢,用时竟有阿杜个唱音乐会那么久,让人生急。
“哎呀,我忘了把红烧鱼撂冰箱里了。”正在有伤风化的时候,她突然想到。
“别去管它!”我不想这么快就下欲望号街车,问题是——还没到站呢。
“不行,会馊掉的。”她硬是推开我,匆匆去了厨房。
床一下子宽敞了。我汗津津的躯体骤然间冰冰凉,好似兜头一盆冷水,把那种叫欲火的东西浇灭了,连灰烬都已不见,高涨起的激情,也一直跌落到太古洪荒里。
甜妞回来,脸上是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见我静静地瞅着她,颊上红一红,忙忙地去遮盖阴部,上床来赶紧钻进毛巾被里,连头也蒙上。
“继续吧,死死地盯着人家做什么?”因为口鼻掩在毛巾被里,声音也就瓮瓮的,像早期电影译制片的画外音。
“先歇歇。”我已经冷却下来,心也似乎变得苍老许多,好像长了胡子。
“你这个大色狼,装什么装,你不要拉倒,不要以为我会来求你。”她用毛巾被劈头盖脸地把我俩包裹起来,腻在一处,她的身子很烫,烫得巫山云雨,然而,我的精神彻底惺忪迷离了,虽吻着她,阴茎却睡着了。
甜妞入梦了,我却失眠,到阳台去,俯视着下面一条条同样失眠的街道。
我去看母亲,却没有进屋,只把给母亲买的礼物放在家门口,按一下门铃,就走了。一年中于某一人总有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就是生日,而我则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特殊的日子应该是属于母亲的,那一天,痛楚、愉悦和幸福都是她的——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母亲是毛泽东时代的女性。“怀你的时候,我们钢厂正在搞大会战,加班加点,生你的前两个钟头,我还在广播站广播挑战书呢!”母亲说这些的时候,自豪得很。
在大学里,我最陌生的怕就是教室了,总是躲在宿舍读郁达夫,是郁达夫引我走进三十年代的疏淡轻烟之中,竟寻不到回来的路。母亲来宿舍,见我痴迷于书,只说“读书好,读书越多越好,”把带来的奶粉、辣酱什么的撂在桌上,便回。
毕业后,搬出来住,每次回去,母亲都烧火做饭、汲水洗衣忙个不停,忙碌间,仍有着那个年代才有的飒爽英姿,只是鬓发斑白了。我于心不忍,劝她歇一下,她连说不累。想她自父亲地震遇难之后,辛苦抚养我们哥俩,越发不愿再让她操劳。拦又拦不住,心里就酸楚得不行,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于是,我尝试着把母亲从厨房拉出来,一家三口,在附近的小川菜馆去吃饭,少受些累。母亲竟变得挑剔起来,嫌这个菜寡淡,嫌那个汤太咸,其实,我知道,她是嫌贵——她勤俭惯了。最后一回,她干脆去也不去了,我和弟弟怎么劝都没用,她就那么执拗地坐在床上,光阴在她的两颊徘徊。
所以,我生日的这天要母亲安静,不打扰她,懒懒地睡一觉也好,散漫地晒一晒太阳也好,或跟其他老太太一道去扭秧歌、打麻将也都好……
“妈,见到我给您熬的黄花鱼和清炒虾了吧,尝尝吧。”下楼,我像个顽皮小子一样一边踩着马路牙子走一边跟母亲通了一个电话,“这是我的手艺,照着菜谱操作的。”
“儿子,你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吗?”母亲问我。
“嗨,小小年纪过什么生日,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哪,再说吧。”我故作洒然地说,这时候,恰好有公交车过来,我便跳上去,又与母亲说三道四一阵,才挂掉电话。
其实,我跟母亲说的话,都是昨晚甜妞说与我的,听时很有一些逆耳,心里就系上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原以为她会建议我举办一个生日派对什么的,看她这样冷漠,不免小有失落。
“我就不过生日的,老了,到五十岁以后再过也不迟。”甜妞心思的不细腻,由此可见一斑。说罢,她掉过头去,又睡。她睡觉时喜欢蜷缩着身子,像个婴儿。
书店窗外的梧桐叶都绿透了,绿得书店窗内也是一片诡奇谲变,朝气浓得化不开,我连取书都是脚步轻快的。听到门铃响,头也不抬就是一声“欢迎光临”,这是我从麦当劳快餐店学来的,声音甜而腻。来客倒笑了,却原来是汉奸,仍旧是那么衣冠楚楚的,特人模狗样的。
“得了什么稀罕宝贝,这么喜兴?”我见他手里拎着一只精美的塑料袋子,很珍惜的样子。
“给女朋友买的芭比娃娃,”汉奸说,“她就喜爱这些孩子气十足的玩意儿。”
“好好珍惜她吧,别丢了。”汉奸的女朋友我是见过的,公务员,生就一张玛丽莲·梦露一样俊气的脸,汉奸把她领来的时候,她就小鸟依人地站在一边。不过,小鸟是长着翅膀的。
“我会珍惜的,”因是说到心爱的人,汉奸一脸的春色,“昨天,我们老板池田先生请客,我还是拉她一起去的呢。”
汉奸来,多是为他的老板跑腿儿。他的老板阅读范围很窄,似乎仅限于抗战年间的沦陷区文学,比如张爱玲、穆时英、予且,沈从文是不看的,叶圣陶也是不看的,显见是一个天性挑剔的动物。
“这回,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我?”汉奸趾高气昂地说,“尽管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吧。”
“去拿一本《结婚十年》吧,苏青的。”我指点最靠里边的一架书,让他自己去取,“有人拿周作人跟苏青做比较,说周作人写得平实而清淡,苏青写得则是平实而热闹。”
汉奸站着读,只掀几页就说好,他连连跷着大拇哥,很业内的样子,其实,除了畿米和朱德庸的漫画,他看过的书少而又少,没少看的倒是三级片,光着腚做俯卧撑的那种。我说:“只有你的那个大日本皇军说好才算数,你说好——那是扯淡!”
“谁说的?”汉奸以为我侮辱了他,竟脸红脖子粗,“我看好的,池田先生也必会说好,昨天喝酒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儿搂着我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啊呸,你以为你是谁!”我简直笑得不行,差一点儿吓跑一个刚进来的顾客,那是个学生,瞪着小兔子一样惊惶的眼睛,看着我们。
汉奸被我笑得有点儿狼狈,赶紧解释说:“这话是他喝醉时说的,玩笑而已。”
店门被推开,罗素来了,而且手里也拎着一只精美的塑料袋子。我和汉奸停止了说笑,像三毛学生意似的认真地一买一卖起来,汉奸走了之后,我才发现罗素今天竟穿一身职业套装,颜色深深的那种,反而倒把她映衬得灿若桃花,热力四射,尽管脸上依然是冬天。
“老板,来一下,”正想跟罗素说点儿什么,有顾客招呼,我只好过去,那人神经兮兮地问:有黄色小说吗,《肉蒲团》、《痴婆子传》那样的?我说:过一阵子,我给你写一本。对方笑了,有几分腼腆。
店堂清净下来以后,我把这个说给罗素听,我猜,那一定是个民工,罗素却说:“我看是大学教授——无疑!”
“大学教授怎么会变态成这个样子?”我一边把才从废品站收来的旧书摊开来分类,一边继续刚才的话题。书是残的多,因潮湿而走形,须先放进微波炉里消毒,然后用熨斗熨,再然后像裱画一样的装裱粘补,很是麻烦,好在我有耐心。
“是民工,他解决下半身欲望的途径更为直接,要么去找职业卖淫妇,要么去勾搭半老的风流寡妇,”罗素说,一副慢悠悠的,若是再叼个烟斗,就跟大侦探福尔摩斯差不多了,“而大学教授则不然,对前者是不屑,对后者是不敢,只好溜达到小说的性描写中去意淫喽。”
“小罗,这好像是俞平伯的书!”我捧起一本撕了封面的书,书钉已经锈蚀,纸张也就散落得没了秩序。
“没错,”凌乱中,罗素把零碎纸张一页一页拣起,说道,“是俞平伯的《杂拌儿》,开明1928年初版。”
对修理残书一道,我有信心,只要不缺胳膊少腿儿,全须全尾,经我一番梳洗打扮,保管可以“一倾倾人城,再倾倾人国”,绝对能嫁个好人家,瞧好吧您呢。
小心地翻阅着这些散页,绵绵的情致恍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涟漪,静雅地漾漾。我就兴奋得不行,抚开纸张上皱褶的时候,手都抖。
修一本书,比印一本书要难得多,每一页道林纸都得洇湿,用干毛巾抚平,再阴干,急是急不得的。罗素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看着我做这些,烦并快乐着。
“我们学校中文系有个教授,去南方开学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