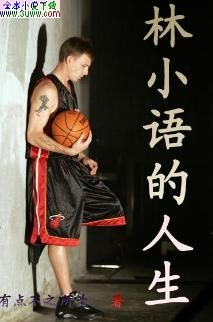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命运,凄凉的晚景,只是徒劳地为着收拾这场奢华的残局。
1995年,她在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故于美国洛杉矶。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故去了好几个时日,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空旷的屋子里,她躺在行军床上,比活着来得更是寂寞。
也许她不认为这是寂寞。她许是会说,因为生命的结束,没有意义的人生因此才产生了景象。如果是怀着这样的情感去迎候死亡,我想,她在晚年的自己守望自己的日子里,在守望死亡的最后的生命时光时,她应该是平和而平静的,她是这样在同死亡对峙。
所以,当时她的身边不必有人,也无须有别人。
这像她的某篇小说,更像她的
散文在直白地道出事情的本质:人们不愿承认或者故意去忽略的“那么回事”。这就是她对生命、生活的虚无感,也是她作为一个作家对读者的残忍。我以为,人们,尤其是生性敏感的人们,都是很容易产生这种虚无感的。所以我们才要去追求美好,甚至在一些时候要沉湎于某种幻觉。这是一种需要,或者是人的某种本能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或者叫向往其实也只是一种人所需要的幻觉而已。张爱玲却打碎了人们想要保留的这份情怀,道出了人们不想提及的某种现实。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女人,张爱玲都是一个极端的范本,一个在多变的时代中由于多舛的境遇强化了某种天性的个性鲜明的存在。她以冷漠而绝望的内心拷问人生,又在世俗的日子里热爱和讲究着生活的具体细节,沉醉于每一个日子的转瞬即逝的美丽。为了救赎自己,她用文字创造了一个华丽而苍凉的末世世界。她温文尔雅地写着这个挽歌里的末世,她从容优雅地同时又以薄情寡义的姿态,把人生中的阴惨与绝望娓娓道给读者。她面对人生的浮世的悲哀和虚无,借助文字的力量,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仿若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洗劫众生的灵魂,那种刻骨和透彻,像梦呓一样使人惊栗。而人的思维一旦与感伤进行搏斗,忧郁和焦虑的真相就会构筑起清晰的困境,也只有痛到深处。这是张爱玲作品的感染力,优雅中暗藏了魔咒的符号。
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种魔咒的符号,如她19岁时写的《我的天才梦》中的名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几乎可以说是她一生的写照,像一个谶语一样使她在事业、情感、生活中一生受着这种咬啮性的销蚀。也几乎可以概括她的作品给读者的百味杂陈。
比如《金锁记》里她写的曹七巧。曹七巧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张爱玲却用文字改变了她,把有着最世俗情欲的她许配给了一个身体不健康的大家庭里的男人,又在她眼前安排了一个她心仪着却又不属于她的男子。她同时让曹七巧承受多重的压力直至饱和点而变态:在给别人痛苦并看着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变异的满足感。然而,不管是被折磨,还是折磨着别人,曹七巧在母亲的教诲中记牢了要抓住男人、抓住金钱,等等。只是她用了一生,却是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这是小说人物的虚无,也是张爱玲自己的精神人生。
张爱玲的长篇代表作《十八春》是一个姐姐和姐夫合谋陷害妹妹的悲剧。一系列懦弱的、矛盾的,或者玩世并龌龊又可怜的形象,借着一些虚构的人物显露作者的追问和挣扎,倾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心迹。这是张爱玲的小说。
很多人说,张爱玲这样写小说,有这样的内心,因为她的家庭、成长、经历。她生在官宦人家,祖父张佩伦是清朝末年大名士,伴光绪皇帝左右。中法战争时,以一介书生统兵与洋枪洋炮的法国鬼子对阵,兵败后被朝廷革了职,发配到了边疆。数年后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做了李家的女婿。这样热闹的家庭,张爱玲却是进入得太晚,她出生时,家道已开始衰落,父亲是封建遗少、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母亲却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父母由争吵而离婚,后来的继母不淑。如此,张爱玲的童年在进出有汽车接送的同时却又没有钱交学费,没有钱零花,得不到父爱和母爱,只好逃出家庭。后来在母亲的帮助下,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转读香港大学,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学业未竟就遗憾地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以写作谋生,一举成名。这时的短短几年,是她一生最耀眼的日子。海派的文化放大了她的女性特质,她直觉的敏感孕育了文字的聪慧,青春的资本给了她目空一切的生机。静默里她雷霆万钧般出众,人群中她万里无云一样光彩夺目。除了才华、作品、名气,那时她的人也是活色生香。她用大红大绿的配色做成旗袍出门上街,临场拿起沙发罩布做披肩,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她标新立异喜欢着奇装异服,精致地生活在人们的眼里。她的十足个性,引领潮流,和不可阻挡的气质,让很多的人惊艳、赞叹。然而,这时的上海因为战争也是沧海桑田,有识之士远走他乡,她自己又不屑于那些浮光掠影的溢美之词,于是不问缘由、不问经历,以一种游离时空的生活态度,使她在23岁的时候爱上了38岁、有过两次婚姻又经常移情别恋的有妇之夫胡兰成,爱路至此无涯。这段情路刻骨,让她体验了“恋爱中的飞扬与放恣”。胡兰成终究是懂得她的,虽然这种懂得很是短暂。“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正如她在散文《爱》中写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所以她不计较。这种不计较放在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却是没有美感的:“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
于是她终于死了心,终于知道“落花不再返枝,流水难以回还”。却再也找不回以前创作的感觉了,她创作的巅峰过去,后来发表的作品也不再具有震撼力。后来她以完成因战争终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去了香港,后又转道美国。在那里,35岁的张爱玲邂逅了65岁的左翼文人赖雅,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居无定所、事无定职的张爱玲备感凄凉和无助,面对赖雅的关心,使落寞中的张爱玲有了依靠之感,更何况赖雅没有其他文人的清高与歧视,并对她的写作感兴趣。可是他们的婚姻也并不幸福,赖雅给过她爱与温情,还有安全感,但是由于年老多病,赖雅带给张爱玲的更多的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重负,经济的窘迫,生活的压力,不仅增添了她的忧愁,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在与赖雅的11年婚姻中,一方面她不得不为了赖雅的病而放下创作去尽心照顾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生计拼命写作,可是这样功利的写作无疑会是心浮气躁的,没有了内心的宁静和超然,哪会有好作品产生?何况经历了两次伤心的爱情与婚姻,她的灵气与才华已消失殆尽,写出的文章也如新瓶装旧酒,毫无创意。
也许爱不是怀念,不是热烈,而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以上种种,自然是与她的小说创作攀缘着的。事实上,张爱玲是一个用本能和感性写作的作家,她是自己的所见所感的记录者。她编那些故事,一方面,是她有条件看到过类似或者差不多的生活,一方面却是她懂得那样的故事能牵引着读者跟着她走,这许是人的本性之一种吧:向往着美好,却又容易被悲剧动摇内心。
这种本性或许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长,本能里便有悲天悯人的情结?无论如何,我倒认为,张爱玲是那种本性凄凉的女子,这种本性凄凉,是来自骨子里的,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忽略和克服,所以她能创作出那些像诱因一样的小说。这不是能不能编故事或者能编什么故事的问题,而是作品的一个整体氛围。氛围不同,给读者的感受不同。这也是同样是写人的丑陋,张爱玲与鲁迅的小说全然不同。
在生活中,张爱玲却又是另外的姿态:该放就放了; 该忘就忘。很多的事,没有因,没有果,却依旧上演。一些的爱,没有缘,没有盼,却依旧沉醉。这是因为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看透了人和事的本质。她的这种生存态度,在她的散文里比较刻薄地体现着:以遁出的姿态把读者停留于苍茫的可感可知; 并用冷眼看世情点出一针见血的结论让读者无路可逃。在对婚姻的阐述中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描绘着人们熟知的平常日子,忽地就总结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认为抱着基督的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圣母“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灰了心,灰了头发”。她的散文就事论事地面对世俗生活,如同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小说和散文,都是张爱玲自己,也是很多人的内心种种。而人的内心完全呈现,却又会带来骇人的一种摧毁力,对美的摧毁力。就此而言,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自欺欺人或者被欺骗。张爱玲该是懂得这一点的,在真实的生活中,她于是便就事论事,难得糊涂。但她却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这是一种刻薄,更是一种冷漠和寡情,心硬如铁的人容易如此极端。张爱玲便是这样的人。这也便是她的人生。
我想,任何真正能读懂她和她的作品的人,心里恐怕都会有一种惊栗:人生何以会是这样的虚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气找她的文字来读。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以用她在《倾城之恋》里给人物范柳原安排的一段话来解释,这是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多种原因,在每个人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都积聚着恐惧,对人生很多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事物和结局的恐惧。而恐惧的背景是悲情。张爱玲就是这样借助天赋直取人生的要义而抵达人的内心,满足着人们用别人的幻灭来化解自己的悲情的需要。这样的作家,往往也是歧义丛生的作家,各式各样的读者可以因知识水平的不同,或领悟精髓或攫取片断,而偏偏这些精髓或片断也是迷人的。危险正在于此。魅力也正在于此。
如此孤寒寡情涤荡人心,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里,张爱玲是少见的,明艳的。
而张爱玲自己,心却是轻易不动。本来是应该因体验到的苍茫而对人生琐事生出些淡漠的生活中的张爱玲,因着要逃脱这窒息的感觉;反而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火热的生活。于是,张爱玲在生活中便有了种种的“古怪”。她称自己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也确实给人这种感觉。生活中的她现实而且对日常生活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这种喜好像一朵可以永远开下去的花,像风在脸上留连过的痕迹,浪漫而真切地化解和调适着她对人生的虚无和看透。她喜欢听市声,喜欢热腾腾的人气,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以贴肤之感喜爱着。她能为一个工人修理电线,专注地观看半天。为街头一桩不打眼的事物,凝注着把四周都忘掉。她会为稿费同编辑斤斤计较。盛名之时,她是四十年代上海滩时尚而前卫的摩登女子,衣食住行很是考究。落寞之中,她又能直面生活困境而不陷入烦劳。她知晓人生百味,洞悉世态炎凉,直观地却又是恍若隔世一般地投入生活,并明明白白地让自己看见自己的生活。这种清醒,就像是一个在夜深失眠的人,自己醒着,还要把梦乡中的别人也唤了起来陪着。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图为张爱玲自绘插图《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张爱玲插图之倾城之恋
胡兰成由此这样写他对张爱玲的感受:“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胡兰成这样看张爱玲,看到的该是事实,却也只是看到了事实的表象而已。张爱玲宽容人性的弱点,说到底她还是在悲天悯人,她写到芸芸众生,嘲讽,刻薄,这都是基于她的这种悲天悯人。她把根扎在最低处,从这里长高,高到俯视人类的悲哀,但她又无法改变这些,她越是清醒便越是痛苦,于是有极端的描写,极端的文字和结论,以及种种一般人会以为的“古怪”。这有点像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大爱。当她喜欢着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