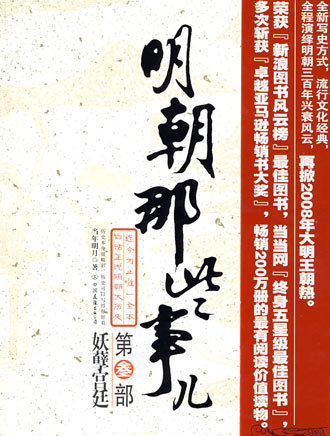北京北面儿-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文
引子 北面儿的伤感
(说明:这是我的一部旧作品,重发是为了把它置于新的作者名下,仅此而已。)
以前的北京能够被称为“城”的部分是如今二环以里的地界。据说以前二环路是一圈厚重的城墙,进出的通道就是各个方位的“门”:东直门、西直门、建国门、宣武门……由于它们严重的阻碍着交通,而且它们的存在使北京显得很是闭关自守,所以被无情的拆掉了。
于是北京城一下子变得豁亮、开放了许多,城里人和城外人也不再那么界限分明了,而拆下来的墙砖则被老百姓们拉回家盖起了房子、围墙,还真解决了不少的实际困难。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拆净,留下了诸如:前门、德胜门等几个楼子孤零零的耸立着,目睹着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
我小时候路过前门楼子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战争遗留下来的大炮楼,那会看过的战争片都是打鬼子,所以很自然的认为前门楼子是用来打鬼子的,幼小的心灵里凭空增加了几分对它的敬仰。
天安门一直向北顺着中轴路经过地安门大街、鼓楼大街和亚运会修的大熊猫环岛,可以到达北四环的北辰桥,如果往西一些到健翔桥后再一直向北,顺着高速路就可以到达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长城再往北?统称农村吧。
这就是北京的北面儿,纯粹的地理方向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因为北京很正,各种建筑也大多是正南正北。
然而——
生活的北面儿或者说生活的方向呢?还那么容易搞清楚吗?
我想,也许它需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一生去辨认吧……
……
我肃然的站立在北京城北面方向一个颇具规模的高档墓地里,呆滞的望着身前小莉的墓碑。照片里她的表情是那么的祥和与真实,向我投来的目光充满了信任和爱慕……
渐渐的,她年轻的容颜开始模糊,如她每次在我梦中出现时一样。我摘下眼镜,抹了一下双眼,可是那叫做泪水的东西却总也抹不净……
我从怀中掏出那首她离开时写给她的诗,再次贴在她的墓碑上,然后划着一根火柴,将它点燃。
那些沾满泪水的字随着火焰的光亮一下子消失,然后随着风飘散到空中……
毫无顾忌
自由 升起 不再有压抑
我听说自由的天地里只有无声的
哭泣
欲望 想起 为之而努力
疲劳的心计不再能有无限的
生机
你到来 然后离去 相信我无能为力
我哭泣 然后死去 没有一片枝叶遮蔽
希望 燃起 点燃了边际
你说过没有幸福骤至只有泥土的气息
泪眼 擦去 涂抹胭脂粉迹
灿烂的美丽不再有悲伤掩饰
你到来 然后离去 用尽你心瘁焦急
我肃然 不再回忆 为了现实而努力
听见了吗 曾经无声的你
你不再有圣洁的美丽
看见了吗 已经离去的你
我在红尘中逝去毫无顾忌
……
小莉从京心大厦五十层楼顶飞下去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此生要背负上无尽的歉疚,虽然她的初衷是惩罚自己,但真正受到惩罚的却是我——一个还活着的人。
那一刻她真美,展翅飞翔了起来,衣裙翩翩舞动,秀发迎风飞扬,像神话中驾着云飞翔的仙女……之后的很多年我总有一种尝试一下的欲望,并且随着岁数的增长,这种欲望愈发的强烈。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我能够承受住无边的自责,却承受不住自由落体拍地后的疼痛。
她拍下的那一刻声音是沉闷的,即使是在五十层高的楼顶,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沉闷……她被巨大的加速度的力量击碎了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神经……
我再次抹去泪水,小莉的容颜变得清晰了许多,眼前的她依然是那么的栩栩如生、充满活力。
天色已经不早,天边的白云已经变成了彩霞。我该离开了,回去的路还很长,又要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了,陪伴她的只有黑暗和孤寂。
我无奈的叹了口气,虽然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必须走了,我还要为生活去奔走、去忙碌,毕竟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呀……
回去的路上,我慢慢的收起了伤感。
李跃曾经不止一次的劝过我,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命”,都是命,阎王让你三更走,谁敢留你到五更?我理解老友的善意,告诉他虽然我不信命,但我不和命争。李跃说这就对了,活明白了就好,咱们哥几个的故事太值得深思了,什么时候闲了写本小说出来,不为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忆吧……
其实用不着他提议,我早就有了写书的冲动,只是思绪还没有完全理顺。今天终于起笔,但依然是思如乱麻,想到哪写到哪吧。
……
第一章 不着调的幸福生活
1
北京城秋风瑟瑟、略带寒意,空气中弥散着淡淡土腥的味道。出行的人们裹得严严实实,女孩们也换下了昔日靓丽的装束,甚至把迷人的脸蛋也用各色的纱巾包了起来,陡然变成了一个个蹬着自行车游走大街的蒙面女侠。
北面天空昏黄一片,据北京市气象台报道,又一股沙尘暴正在逼近这座百年古都……
下班我打了辆车直奔恩济里小区,邵军来电话催了几次让我提前溜号说三缺一就等我了,我说领导找我有事儿一时走不开,他嘟囔着说我装孙子挂了电话。刚坐上出租车,邵军的电话再次打来,我不耐烦地说,“你丫烦不烦啊,上赶着输钱是不是?”挂了电话,我催促司机师傅加快车速,司机问我是不是急着去送人、赶火车,我说不是,是急着去搓麻将、赢钱。司机师傅呵呵的笑了。
我进门只有邵军和陈枫坐在沙发里看电视,一屋子的浓烟好像刚着完火,我被呛得直咳嗽,冲邵军说,“不知咱俩谁装孙子,现在算我还他妈三缺一那。”邵军嘿嘿乐着甩过根烟,然后忙着给李跃拨电话,“……什么?在阜石路上那!赶紧的,三缺一……”
电视里播放着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男女做作地伴着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糙壮的模仿某歌星的“大男孩”扭动着,歌罢主持人们“YE YE”着装嫩,天上飘下一些碎纸片。
李跃进门边脱外套边骂,“傻X!这种节目你们丫也看。”
“你才傻X!找抽那!”我们几乎异口同声,都瞪圆了眼珠子。
李跃怕挨抽忙解释,“不是骂你们,我骂主持人那。不过你们看的这么带劲,品位也确实差点儿。”
“主要是他们俩爱看,整个两个忘记国耻的哈日族,‘Para Para’了。”我把矛头指向邵军和陈枫。
邵军起身,“我们也知道国耻,可看什么呀,不是满清就是破案,全国人民都他妈想留辫子,不留辫子就得和罪犯周旋。” 然后看着我们仨,“咱是搓杭麻呀,还是拉耗子?”
“随便,”我说,“玩什么不是赢啊。”
“我也随便,是赌就行。”李跃也不在乎玩什么。
“又一演唱组嘿,‘少女队’,你们说这塑料裤子热不热?”陈枫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电视屏幕,把屁股从沙发移到桌子旁,“拉耗子吧,好长时间没玩了。麻将我这阵子是玩一回输一回。”
大家都没意见,邵军从抽屉里抽出一幅新扑克,开始从8到A挑牌。
“拉耗子”又名“嗦哈”,香港赌片里的玩法,只是电影里玩的是整副牌,我们为了提高效率,只玩8以后的半副牌,最大的牌当然就是周星驰曾经搓出来的黑桃大顺10、J、Q、K、A,不过摸到那种牌的概率可能是我们四个人在风和日丽的晴空下同时被一个响雷击倒。
在我“嗅”了陈枫一把一百多块钱的“面儿”后,陈枫起身打电话叫比萨外卖。比萨很快送到,三个人直勾勾的盯着我,我不看他们抬眼盯着天花板数苍蝇。
“嘿,嘿!装什么装,那赢钱的,说你那,赶紧给人付帐。”陈枫对着我挤眉弄眼。
我把头转向邵军,“说你那,邵军,赶紧付钱,别让人小伙子跟这儿晾着,一点儿都不自觉。”
“你就装吧你,赶紧掏钱,我又没赢钱。”“方大你赶紧的。”邵军和李跃催我。
我无奈地转向送餐的小伙子,“多少钱?”
“一共是二百三。”小伙子递过单子给我看。
“我操,我才赢了一百多,付完帐我也输了。”
三人开怀大笑,“活该!谁让你丫先赢来着,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才是钱那。赶紧,赶紧,我们可先吃了,再渗着让你掏了钱还吃不着。”
我无奈地掏了钱,“票儿。”小伙子递给我张发票,我小心翼翼地揣进钱包,“明儿哄着姿姿给我签个字,混一块报了丫的。”
送餐的小伙子刚出门,我们四个就恶狼般扑向比萨,大吃起来……
战斗在凌晨四点钟结束,我们各自揣起桌上的钱,倒头睡去。床上睡了三个,沙发上一个。我闭上酸疼的眼睛,满脑子却是各种组合的牌型飞来飞去,在神经错乱般的混沌中我隐隐听到“茉莉花”的乐曲,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刺激得耳膜极不舒服,我睁开眼寻找声音的源头,这才发现是手机的闹钟服务,感觉只躺了一小会儿,脑子里还没有飞出一副大牌怎么就七点了,我摁断枕边的手机,坐起来醒了一会盹,再看那哥仨依然鼾声如雷。
我推醒李跃,只有我们俩需要正点上班。我们草草洗了把脸,从邵军的冰箱里搜出一瓶酸奶分着喝了,出门各打了辆车直奔单位,床上的那哥俩又不定几点能起,说不准为了昨晚的战斗又要换单位了。
2
我和李跃家住朝阳,高中我们同桌,他抄我的物理作业,我抄他的化学作业,一来二往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经常边抄我的物理作业边说,“操,这种题你也做得出来,你丫真是物理天才,二十一世纪的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然后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我抄他化学作业时也会有同感也会不停的赞颂他,在把物理化学作业交给科代表后我俩就躲到厕所坑里分烟抽。
李跃老家是浙江宁波,当年他祖爷爷在乡里怎么也算头几份的人物,也许还能和蒋介石家扯上点亲戚。高考报志愿时,李跃的父亲说服他考杭州的X大,一来那里是他父亲的母校,学校里有几个他父亲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是教授或者系主任,二来杭州有很多亲戚朋友日常可以有个照应,三来当然是最主要的李跃肯定考不上清华而X大又是国内仅次于清华的理工类院校。李跃没有别的选择,虽然他很想在北京上大学,于是他开始说服我,让我和他一起报考X大。我说我要是报了,他岂不是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我的学习又不比他差。李跃说没关系,他家X大有人,就算比我少考几分,也肯定会先录取他的。我说那他妈算了,我可不愿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招生体制的牺牲品。李跃赶忙改口说如果我也报了,就把名字一起报到X大他爸的同学那里,就算我俩都少考几分,也肯定会照顾我们俩的。我说我们俩排名分不分先后?他说不分不分,按姓氏笔划排。我一想我姓“方”只有四划,他姓“李”有六划,于是我也报了X大。高考成绩出来我俩竟然考了同样的分数,我物理比他高8分,他化学比我高8分,我俩都开始痛骂抄作业的百害而无一利。
我俩不需要找关系进了同一个系的同一个班的同一个宿舍。后来入校整理宿舍床铺时,我跟李跃开玩笑说他要是个女的就好了,夫妻双双考上了同一个系,还分在同一个宿舍,不过他太胖了,就算是个女人也肯定是个丑女人我肯定不要。他说算了吧就算他是个漂亮女人我们也肯定不能分在同一个宿舍,不如现在没有了家长管,我俩看看谁能先找到漂亮的女朋友。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于是我们俩约定谁输了回北京的时候给对方买卧铺票。
邵军和陈枫比我们小一届,同一个系。邵军家住海淀,高中是人大附中的,在班里既没有拿到过奥林匹克什么奖,历次考试的排名也从来没有进入保送好学校的名次,于是一生气考上了X大。陈枫家住东城,在一所普通中学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和超水平的考试发挥终于如愿以偿,为此他父亲奖励了他一张卧铺票。
我们四人一见如故,头一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抽了两盒“都宝”、两盒“绿杭州”,啤酒更是喝了不计其数。他俩为在这个陌生的美丽校园里有人“罩”着而欣喜万分,我俩为今后撮饭多了两个结账的而沾沾自喜。
在经历了新生刻苦努力的一个月早起晚归的学习后,邵军哥俩开始不学无术,并且愈演愈烈,当然这里边有我和李跃的表率作用,不过他们更加善于发扬光大,有过之我俩而无不及。比如我们一般八点半起床去上课,他们一般九点半起床赶在下课前去点名;我们一般一周旷个两三节课早退个四五节课,他们一般就不上课;我们一般见到漂亮的女学生只敢多看几眼,他们直接上去问是哪个系的叫什么;我们一般在食堂买牛肉,大师傅转身找钱时顺一个鸡翅膀,他们一般不买就顺;我们一般一场周末舞会只能请到两三个女学生跳舞,他们则一个曲子换一个。我们经常的教导他们:床还是要早起一点地;课还是要上地;鸡翅膀还是要先问问哥哥们吃不吃地;漂亮的舞伴也完全可以让给哥哥们嘛。久而久之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礼的说教,鸡翅膀我和李跃终于吃了几个,但其他方面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终于,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后,一个同学碰上我兴奋地跟我说:“你们北京的那俩哥们可够牛的,高数,哥俩的分数加起来都没及格……”
毕业后,我和李跃被分配到在京的两家研究所,邵军和陈枫则在各种公司里飞来飞去。我在所内苦了两年,猛然看破“红尘”,无心再搞科学研究,跌跌撞撞的混进机关,并在仕途之路上迈出了一小步,混上了个副处长,相当于地方的副县长。当然因为这是在北京,要是地方顶多是个副科长,而象我们这样的国有事业单位,领导的最低起点就是副处级。李跃则一直在做课题,目前已经成为了技术骨干,年轻的副主任设计师,独挡一面,并且由于他工作出色、技术过硬,单位特许他上了某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邵军的父亲曾经是个司局级干部,在他离开领导岗位前给邵军弄了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在羡慕之余,很自然的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家和赌博活动的场所。
3
路上还算顺,我是最早来到办公室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