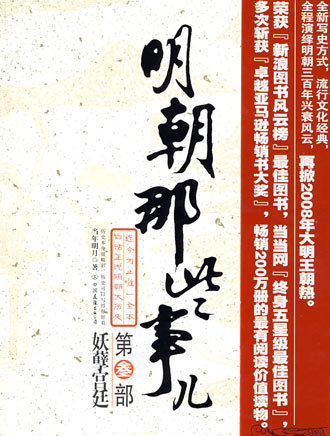北京北面儿-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一个人帮我们支蚊帐。我俩收拾床铺时小声嘀咕着今后要和这几个傻逼一起生活真他妈的扫兴,后来情绪好一些我俩开始商量比一比谁能先找到漂亮的女朋友,输的一方负责买卧铺票。我说李跃你肯定输了,因为我比他长的精神,他说不一定,南方姑娘就喜欢北方的胖子,尤其喜欢化学好的胖子,我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南方姑娘大多梦想着嫁给日本人,日本人就是小逼个儿一身肉,我说可你个儿还行不算小逼个儿,我又问他姑娘为什么喜欢化学好的,他说化学是和医学相通的,懂化学懂医学的男人都知道采取何种方法避孕。我不屑一顾的说操,这有他妈什么联系,全天下的男人都知道如何避孕,他的话纯粹是一派胡言,我还说南方姑娘喜欢物理好的北方汉子那,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摩擦。我们两个旁若无人的开怀怪笑。可能是我和李跃探讨的问题太出格了,同宿舍的另五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八成觉得北京来的学生怎么是两个流氓,我俩只管谈笑并不搭理他们。其实我俩都憋了一肚子气,再怎么说今后要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四年,怎么能死性到连帮忙的话都不愿意说一句。
还是“打红五”使大家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也开始不再陌生,熟悉起来后才觉得其实大家并不是很难交往。那是一种南方式的类似“双抠”的打法,四个人三副牌,一人抓了一大把。小吴教我们,洋洋得意,刚跟我学的“他妈的”挂在嘴上,指点着江山。正是因此后来我们选他为“寝室长”,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和打开水。小吴是宁波人,海风吹得脸膛黝黑,如果不开口说话,很像东北人。他的性格也有着东北人的仗义和豪放,当然那会儿东北人还不都是活雷锋。
牌打得正欢,一个自称是我们辅导员的高年级同学走进来,告诉我们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外语,明天早上到第七教学楼参加英语分级分班考试。宿舍里一片哗然,我和李跃面面相觑,骂着他妈的,以为逃离了苦海没想到是刚刚开始。其他的五个同学到处的翻着英语书,我和李跃是一点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于是决定出去看校园和女孩,我们还要为找漂亮女朋友的目标努力奋斗那。等我们俩欣赏一溜够回宿舍拿饭盆吃饭的时候,发现五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翻着英语书嘴里默默念叨着,我们俩怕打扰了同宿舍兄弟的学习气氛迅速的取了饭盆直奔食堂。英语分级考试成绩下来,我们宿舍小吴成绩最高,被分进了A班,直接读大学英语二级,我和李跃和另俩个同学被分进了B班,读大学英语一级,剩下两个同学成绩最低,进了P班,英语预备班。
开课以后,每个清晨我们随着晨号醒来,收拾停当,然后去食堂吃饭,打开水。回到宿舍后两排就座在干净巨大的桌子旁默读外语。新生的生活简单有序。但这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我和李跃就有点受不了了,此后,我俩经常被众人蚊子般嗡嗡读外语的声音吵醒,不情愿的起床洗漱、吃饭。
大学学生从来没有固定教室固定座位,这门课在这个教学楼,那门课又在另一个教学楼,我们每日穿梭在校园的楼宇间,很多同学为了占到前面的座位,行色匆匆,我和李跃则悠闲漫步,对我俩来说,后面的座位才是最好的,老师看不到。
我们的第一门课是高等数学,老师是个浙江老头,操着一口浙江味的普通话。起初我和李跃还是像高中时一样认真的听讲,认真的做笔记。但无论我俩如何支着耳朵如何的聚精会神,最终只能听懂老师一大段讲解后的最后一句话,“嘚不嘚(对不对)?”为了不让耳朵继续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俩决定放弃,与其打着瞌睡早起、饿着肚子赶到教室听n个“嘚不嘚”,不如在宿舍里睡大觉,回头再自己看书。正是大一的高数老师让我们学会了不听讲、不上课。在初尝了不上课的极大好处后,这种作风急剧蔓延到了每一门课。后来几乎所有的课我和李跃都没有认真听,都是在到了考试的最后关头拼命的自修学习的。不用每天都上课使我俩顿觉轻松了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美中不足——有的老师会在上课前或是下课前点名。
由于点名直接关系到学期末的考试成绩,所以显得异常重要。不过点名也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大学老师分成三类:不点名的、不经常点名的和点名的。有一些自恃不凡的老师把点名看作是一件不屑的事情,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自己的课有没有吸引力,所以一学期自始至终都不点名;另一类老师颇爱点名,几乎每堂课都要点;最不受欢迎的老师就是随机点名,一学期点个几次但毫无规律,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就点。我和李跃细心观察了每一门的任课老师,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制定了一张点名作息表,挂在床头,我们按照老师点名的不同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到教室时间,两个人轮流着点名。于是我们有了大段的自由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俩开始感觉到自由的生活真好,大学的学习太轻松了。
3
我们寝室的七个人,南北方比例4比3。后来经过“残酷”的考试淘汰,一人被降级,一人被迫抱病休学,南北方比例成了3比2。7个人里我的岁数最大,所以他们包括李跃都叫我“方大”。由于我办事公正,后来在学校里又交了很多的狐朋狗友,寝室里谁受了欺负都会请我出面平息,所以我应该算是依靠着个人魅力领导着这样一个南北方集体。不过,我也和同屋的兄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为此我曾后悔不已,好在仅此一次,那哥们就是小胡。他个儿不高,杭州男孩特有的白净,架副白框眼镜,文质彬彬,满口不利索的普通话。
小胡有一个女朋友,和他是高中同学,叫刘洁,和名字一样的洁白,挺可爱的。那时她频繁的出入我们寝室,于是我们誉她为“室花”,她很高兴,寝室多了这么一个漂亮女孩,我们也很高兴。当时我们谁都可以单独带她到校园里转一圈,让我们系熟悉和不熟悉的女生们知道我们并不孤独,后来由于太频繁,终于被女生们认定了是一个人。
刚入学第一学期八月十五前夕,我莫名其妙的收到了一封未署名的明信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面是“一个你帮助过的女孩,在我刚到这里来时,是你让我不再想家。”邮票斜贴着。一屋子人你言我语,吵吵着让我交待,然后请客。李跃更是为之一惊,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要输了。那时年轻冲动的我,完全的晕了,不知所措,怀若揣兔,七上八下。被逼无奈,我给每人买了一个肉粽子。
刘洁来了,背着她的大书包。似乎在无意间发现了那张明信片,大呼小叫,逼着我请饮料。“想喝什么呀?”“随便。”“红星二锅头,五十六度。”“啊?!”她又开始大呼小叫,非要吵得全系的人都知道我有了“艳遇”。
她的过分的做作的表演使我开始怀疑是她的恶作剧,“你吧,别装了。”“哈!哈!哈!哈!”小胡张开大嘴爆笑,证明了我的猜测的正确。一股无名怒火骤然升起,我有一种被愚弄和欺骗后的歇斯底里。
“笑你妈呀!好笑吗!”我声嘶力竭的大声的吼叫。小胡的笑声葛然而止,停在半空。瞬间,全寝室的人都象雕塑般冻在了原地,笑容麻木的滞留在脸上……
后来很多人包括李跃都责怪我,没道理不应该没理由。我沉默以对。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说:“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
年轻时的一时冲动真的不需要理由……
4
我们常欺负花子,因为他极瘦,皮包着骨头,脑袋尖尖的,眼窝深陷,戴着个大眼镜,鼻梁子上被眼镜支子压出两个深深的红印,支子在出汗时掉色,把鼻子染绿,很有个性。
出识时花子很认生,我常逗他。“你是不是在贵州抽过大烟?”我开玩笑。“没有。”那时他面无表情,很认真地只回答一句话。“那就是经常嫖娼。”“没有。”“那你怎么那么瘦?”“天生的。”
后来熟了,我们常把他压在床上乱摸一气。花子从来不急,总是大笑着,“你妈妈的”骂着。花子很想锻炼得强壮些,总和我一起去踢球。他总想打前锋,但每次只允许当后卫,冲上去就是一脚,踢着踢不着,都决不再追。有时我很害怕他被撞倒后齐腰折断。
第一个生日是给花子过的,我们喝了很多的白酒和啤酒,抽了很多的烟,大家轮流着声嘶力竭地做着那个经典的“棒子和鸡”的游戏。后来我们都沉默了,我开始放崔健的歌,粗旷嘶哑的声音震撼着每个漂泊的心灵。“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不知不觉我已是泪眼朦胧,忙躲到下铺的帐子里,靠着墙抽烟,我又开始想家。
几年的大学光阴,每每折磨我的都是那种凄楚、苦涩的乡愁,幸好还有个胖子李跃陪着我,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坚持下来。
5
宿舍楼的每层厕所旁边都开辟出一间冲凉澡堂子,当然只有凉水。大学四年我只去过一次学校有热水的大澡堂子,那简直不叫洗澡,确切的形容应该算是同性间的肉体摩擦。在你闭着双眼洗头努力不让洗发液钻进眼睛时,你突然感觉到有若干个男人的东西从你赤裸的屁股、腰间摩擦着过去,当你意识到了那个东西是什么强忍着呕吐转过身睁开双眼试图寻找到那是谁的肮脏的东西时,那东西连人一起已经在毛巾的抹来抹去中出了澡堂子去穿衣服了,在你正愤怒间犹豫着是不是冲过去一把拽下那个东西时,突然又有人连带着他的更大的东西蹭着你赤裸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坦然的再次摩擦过去……去过那一次澡堂子之后,我坚信自己不是同性恋者,我甚至开始厌恶男人的身体。我总在想,外国人的澡堂子是不是也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在中国学校这样的澡堂子洗过一次后会有什么感想?于是我决定再也不在大澡堂子里洗澡了,除非是到了国外。
我和李跃开始了冷水洗澡时代。寒冬时节,我俩穿着衬裤、背心抱着脸盆哆嗦着进入冲凉间,放下脸盆,打开冰凉的水龙头,然后开始呼喊着脱光衣服围着圈跑步,然后不做任何准备的大喊一声一头钻进冰冷的水里,然后就是一声杀猪般的惨叫……一般我们都边哆嗦着往身上打着肥皂边上牙碰着下牙声嘶力竭的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第一次和姜涛一起冲凉是我们一起踢完球出了一身臭汗,我迅速地脱得一丝不挂,却发现姜涛已经穿着裤衩钻进了喷头下,他搓搓这儿搓搓那儿的,一会又把肥皂伸进裤衩里搓,我光着身子好奇的注视着姜涛的每一个动作,自己竟然忘记了洗。半天,姜涛发现我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问我怎么自己不洗老盯着他干啥?我舔了一下嘴唇,“姜涛,你丫洗澡怎么不脱裤衩啊?”姜涛说他们那里洗澡都是这个样子,洗完了再脱,裤衩一块洗了。我不信,心想一定是姜涛的家伙小的可怜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于是装作不在意的不时窥视他的家伙,终于,在他换上干净裤衩时我相信了他们那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按照我的逻辑需要穿上裤衩洗澡的应该是自己,对此我惭愧不已……
6
我和李跃经常到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喝酒,虽然我俩都不胜酒力,但我们决心通过四年的锤炼使自己的酒量发生质的飞跃。起初,我俩一人一瓶啤酒就已经晕晕糊糊,云中漫步,练着练着发现一人两瓶才会有一些感觉,我们都很高兴。但是到饭馆喝酒太费钱了,那时我们上大学,每学年学费200元、书费100元、住宿费25元,剩下需要开销的费用就是生活费了,那时不奢侈的每顿饭只需要6毛钱,所以每月父母给寄100元生活费,我们已经算是“大款”,手头相当宽裕了。但由于经常在饭馆吃喝还要买烟抽,所以我和李跃的生活费从来都不够花到月底,为了能够保证每日有烟抽、经常有酒喝,我俩想了很多办法。
李跃家有几个亲戚朋友住在杭州,于是每到周六李跃都会早早的起床,饿着肚子饥肠辘辘的坐上公共汽车去拜访各位叔叔大爷大伯大妈。他先在人家爆撮一顿中午饭,然后再打包一顿晚饭,好的时候再捎带上百八十的零花钱。我周六一般都睡到中午,起来后顶多泡上一包方便面,然后就饥肠辘辘的望眼欲穿的盼着李跃回来。每次李跃都会气喘吁吁的跑进宿舍,左手拎着一大摞餐盒,右手拎着三四瓶啤酒,呼哧带喘的叫我,“方大,快吃,知道你丫一定饿坏了。”我会一下从床上或是座位上蹿起,接过美食和啤酒,嘴里骂着,“你丫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再晚我就over了!”李跃会憨厚的笑着,“快吃,快吃,我先喘口气。”我会一边大口的嚼着五香牛肉或是大鸡腿,一边向李跃比划着,“给哥们开瓶啤酒。”
但是好景不长,当李跃把亲戚朋友吃过了两三遍后就再也没有带回来过美食和钱,李跃可怜巴巴的望着饥肠辘辘的我说,“你丫再想个办法吧。”于是我给姐姐打电话,先描述了一番大学美好的生活和每日忙碌的学习情景,然后开始痛骂学校伙食如何的差劲,按照我的抨击,学校食堂的饭菜猪都不会吃,可是我只能在食堂吃,因为小炒和饭馆的饭菜太贵了,爸妈给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姐姐从小到大都疼我,于是姐姐心疼我的说以后每月她再给我寄100块钱,我没有推辞,但让姐姐不要告诉爸妈,不然他们会生我的气,姐姐说不会告诉的,如果100块不够,我就告诉她,她会给我再多寄些。于是我每月的生活费涨到了200元。
从此,我和李跃每月的生活费变成了300元,我们觉得很宽裕,不仅经常可以下馆子喝酒,偶尔还能来盒好烟抽。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我俩的开销与时俱进,到了毕业那学期,我俩每月的生活费突破了800元,当然管亲人要这么多钱已经不可能,于是我俩又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勤工俭学什么的,当然这是后话。
有了钱,我俩经常会在喝得晕晕糊糊的时候再奢侈的加两瓶啤酒,喝完,我俩就相互搀扶着跌跌撞撞的进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