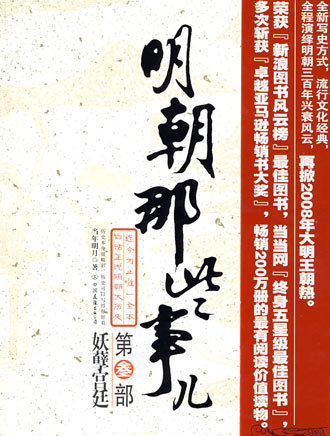北京北面儿-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了女生宿舍门口,我说,“今天就算了,你可答应我了,改天可得陪我——”我又拉长音。
“你真敢我就同意。”雪儿异常的镇静,盯着我,面不改色。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说讨厌也没有用小拳头打我,而且如此认真。我一下不知所措了,窘得厉害。
半晌,雪儿羞答答的半低下头脸涨红着小声的说,“要不——,你吻我一下吧。”我感觉到全身热血沸腾,哆嗦着嘴唇慢慢的靠上去,滚烫的嘴唇真正的碰到一起时,我才知道原来接吻是那样的甜美,我们长吻了很久直到嘴唇都有些发麻了……
11
放寒假,雪儿执意要跟我到北京玩上几天,我坚决的不同意。
“花着你父母的血汗钱去旅游,你忍心吗?等你工作了,花自己的钱再去。”其实我家的条件不是很好,房子又小,所以当然要阻止她去了。
“我父母同意让我去见见世面,钱算我先借的,将来挣了钱我再还他们。”
“那也不行,跟家好好看看书好不好,外边那么乱。”
“北京是首都,最安全的地方。”
“北京冷着那,零下十好几度,你根本受不了。”
“我已经买好了羽绒服和棉皮鞋了。”
“……那也不行!”
“凭什么不行?”
“凭什么,我不带你去。”
“那我自己去!”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买好票招呼也没打,和邵军撒丫子逃回了北京,不再露面。雪儿也真有办法,我到家的第三天她就东打听西打听的,找到了我家。
我爸妈都不在家,我在地当中支着圆桌,正在翻书,准备开学后的补考。我想这几天抓紧时间复习,过年那几天就可以到处的玩了。
雪儿刚一进大杂院就吓了一跳,没想到北京还有这样的居住环境,门洞里黑咕隆咚,不宽的过道两侧堆满了各种破旧、沾满油腻的柜子、桌子,水房、厕所的门大敞着,泛着骚味,各家各户的厨房,里面摆放着黑色的炉子、煤球、煤气灶、煤气罐,窗户玻璃碎了,订着个纸壳本,风从窗户缝中袭进来,刮得各家门帘子飞舞……
雪儿拐了几个弯,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再找到出口。从能够看清的门牌号数着推算过来,终于找到了我家的门。
“当当当”敲门声,“请进。”我在里面喊。
门被推开,“这是——啊!是!”雪儿看见了我像见到了亲人。
我一愣,紧接着很无奈,“你说我不让你来,你偏来,你就不能给我留点儿自尊。”
“怎么了,我就来,看看你在什么环境里长大。”
“什么环境,就这环境!”我有股无名的怒火,说话很冲。
“你瞧你怎么啦,我又没说什么。”雪儿怯怯的。
“说什么呀说,比你们家条件差多了是吧,要是有你们家那条件,我能考上清华。”我没头没脑语无伦次。
“我——我又没嫌你们家。”雪儿更怯了。
“你嫌得着嘛!”我说的话好像都是横着出来的……
也就是雪儿的脾气好,要是别人早气跑了,雪儿不语,委屈地站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雪儿也没招我,其实我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我家的笑话。
隔了一会,我收了书本,“找地方坐吧,又没人让你罚站。”
雪儿找了个嘎拉坐下,带的一大塑料袋东西拽到圆桌上,“给你父母带的。”
“什么东西呀?”我语气缓和了很多。
“自己看。”雪儿还是很委屈。
“西湖藕粉,龙井茶,豆腐干。怎么不给我带几个肉粽子呀,我就爱吃那口。”
“油乎乎的怎么带呀。”
“你说我为什么千方百计的不让你来呀,你就不能想想。”我开始语重心长,又转回主题,态度诚恳了许多。
“你这人就是瞎要面子,我来看看伯父伯母,又不是来查你们家底的。”
“这回满意了,我们家是一穷二白。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
“不过我觉得你能在这种环境下考上咱们学校真是不容易。”
“你才知道啊,没跟你说嘛,要是环境好,我说不准还能考上清华那。那会高考前一个月我妈给我借了间小屋,给我乐坏了。”谈到这事我来了精神。
“你们家怎么住啊?”
“我不住家里,我们哥六个住一个宿舍,就外边院,厕所对面。老大开出租的,老二修电梯的,我是老三,老四厨子,老五不务正业,时不常公共汽车上顺个钱包什么的,去年给判了,老六职高,今年该毕业了。”
“都什么人那。”雪儿有些怕了。
“都是我兄弟!明儿我们坐老大的车一起去老五那探监。”
“你说的都是真的?”
“什么意思呀,你要没事儿,明儿跟我们一起去。”
“不去!”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自强不息的成长起来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我们大杂院的高考状元那。”
“你毕了业,干脆留在杭州吧,回来你也没地方住。”
“就杭州那破地方,半个小时就从西湖走到钱塘江了,也就比县城大点,冬天穿着羽绒服打着雨伞,我可呆不下去。”
“习惯了就好了。”
“习惯不了!行了,甭扯这个了,你住哪了?”
“建国门那一个招待所,我爸来北京就住那。”
“哪天回去呀?”
“我刚来,你就想让我回去。我怎么也得玩一阵子。”
“你还打算在这过年呀,你爸妈多孤独啊。”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呀?”
“初十吧,我得早回去几天看看书,开学了还得补考。”
“那咱们一起回去,行不行?”
“行是行,就怕时间太长你爸妈不放心。”
“没事,我常打电话呗。”
“那你干脆搬到我爸他们单位招待所住吧,离得近,又便宜。”
“行!”
那些天雪儿快乐极了,我带着她地坛逛庙会,什刹海划水冰,天安门观升旗,红楼看电影,大街小巷挤电车,小管子吃爆肚羊杂……反正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很快我们踏上了南行的列车,雪儿给我买了张卧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躺着坐火车,舒服极了。只是我的父母这次对我很不满意,唠叨着就放这么几天假也不陪爸妈好好说说话,整天在外面野。那年补考我很心虚,因为书还是没怎么看,战战兢兢的勉强及格。
从北京回来,雪儿更加的信任我了。
12
我在学校不是经常打架,在我的意识深处是不愿意打架的,因为打人的和被打的都会疼痛,但是有的架是非参加不可的,大三下学期的那场架,让我现在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
那是一个星期天,阳光灿烂而明媚,宿舍里睡在我上下左右铺的兄弟们相约去植物园打牌,我因为雪儿要来给我送从家带的水果就没有去。雪儿来了我给她弹吉它唱歌她给我削苹果,正浪漫着,罗西寝室的一个小个子窜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罗西让你快抄家伙下楼,打起来了!”
我蹭地蹿了一丈多高,爬上床换了便宜眼镜,在墙角抄了个啤酒瓶子就要往外冲。可是,雪儿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一把拽住了我。
“不许去!你说过不再打架!”
“不去不行!以后我怎么混!”
“就是不许去!”
“别捣乱!快松手!”
“就不!我求求你了,别去。”雪儿急得哭音都出来了。
见她要哭我的急切劲没了一大半,不再较劲。觉得有这么一个好姑娘关心自己,此生又何求?我转过身,温柔了许多,不忍让她真哭出来。可那头又都是仗义的哥们,不管不行,我左右为难。
半天我才想出个主意,“我保证不打,不过我得去劝劝,别真出什么事。”
雪儿半信半疑,迟疑半天,“你把瓶子放下。”
我扔了酒瓶子,“这样行了吧。”
“你得保证不打,你要是真打我再也不理你了!”雪儿收敛着嘴唇狠狠地说。
“好!我保证!”雪儿终于松开了手。
我一猛子蹿了出去,下楼时一脚蹬空险些摔倒。
到了楼下,我傻了。一群保卫处干事已经把所有的人围了起来,圈子里有罗西、关军、老三等几个哥们,还有几个捂着脑袋和肚子的挨打的学生。干事们推推搡搡着众人往保卫处方向走,关军和罗西看见我忙使眼色让我别靠近。雪儿跟着跑下了楼,见了这场面吓得脸色苍白,我回头望见她愈发白净的脸,庆幸多亏她使我躲过一难。
事情处理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处分下来,白榜贴到了校门口,凡参与打架者均记过处分。众人都没有了学位。正是由此关军几欲退学都被众人劝住,后来休了一年学,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我躲过了一劫,从此视雪儿为福星……
13
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我们几乎成了“待业青年”,专业课一个星期就几节,剩余的大段时间同学们无所事事,打牌、跳舞、旅游、看录像、陪女朋友、打工挣钱……我一直为大专的学生鸣不平,和本科只差一年,将来参加工作后的差距可是天地之别,而事实上我看本科也就学了三年的知识,稍微紧张点,两年半也完全可以拿下,非要让学生们玩得到毕业时学的也差不多全还回去了。
交了女朋友后我和李跃更加的缺钱了,我们不好意思老是管家里要,觉得管家里要钱花在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上心里总是不落忍。于是我和李跃、关军一起商量怎么挣钱。我们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去餐馆打工。于是我们沿着西湖转圈,每一家餐馆都进去询问要不要服务员,在碰了一路钉子后,终于我们在断桥桥头的一家名为“彩云阁”的台湾人开的馆子找到了活,工资很低,但有小费。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长相一般、身材出众、皮肤白皙的杭州姑娘,她是大堂经理,当时我认为是关军吸引了她,关军人长得很帅,健美练得体形健壮,说话得体,又是大学生,后来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那姑娘在结婚前一个月和男朋友分了手,关军和她交往了几个月,发生了无数次关系后,在我们辞掉这份工作时和她分了手。
我们安分地工作了三天后,找到了挣钱的门道。那是一家绝对高档、有情调的餐馆,不说别的,一扎啤酒就敢要五十块钱,那年月五十块钱可比现在值钱多了。进出餐馆的一般都是男女成对,那个年代就举着大哥大,招摇撞骗,牛逼烘烘的,最重要的是为了显派结帐时极少有要发票的。客人点完菜我们填好菜单送进厨房,酒水单子送到吧台,吧台兼收银,经常是忙得一塌糊涂,所以服务员一般只喊一句“一扎啤酒”就自己先打,送给客人,事后结帐时再把单子一起交给吧台。于是我们在喊完了“一扎啤酒”后自己打完送给客人而不开单子,结帐时我们在夹子里附着帐单然后把总数加上五十或一百的扎啤钱,来这里的客人很少有查单子的,真碰上“穷鬼”要查,我们解释这是菜钱,啤酒五十一扎,一般也就搞定了,吧台要真是知道了(当然从来没有过)我们可以解释说啤酒钱忘了填单子,结帐时刚想起来,先让客人结了再补单子。事情计划得天衣无缝,不过这只限于“扎啤”,一桶究竟能打多少扎没人算过,也没人管过,其他的酒水我们可从来不敢算计。我们哥仨特别喜欢长着啤酒肚的男士,每有进来的总会互视然后默契地笑,心想,“傻逼,看我怎么黑你!”,其实我们黑的是那个台湾老板,谁让他们丫非要闹独立来着。
于是每天我们哥仨额外挣上五十一百的,几天下来,我们由磴自行车改为了打车上班,平时在学校出手大方,俨然变成另一副嘴脸。
我给雪儿买了一个职业女性背的皮包,折两扎半啤酒,雪儿又惊又喜,因为平时我总是穷嘻嘻的,冷饮什么的都是她买,水果什么的都是她带,我突然送她这么贵的礼物,她很意外也很高兴,拼命问我哪来的钱,我说是天天不吃早饭省出来的,她很感动,命令我决不许再不吃早饭,我满口答应。其实早饭我是真的不吃,因为起得太晚食堂来不及去,早饭省下来的钱也都用来买酒喝了。
14
西湖断桥畔,“彩云阁”,晚上。
我拉开餐馆的门,弯腰鞠躬,“先生小姐慢走,欢迎再次光临。”那爷们喝了两扎啤酒,我挣了一百块钱,所以格外的殷勤。
天天上班,我和李跃、关军耽误的课太多了,也加上太累,所以我们哥仨找经理调了一下,我们三人上一个班,每人一星期上两天,这天是我的班,那哥俩也不知上哪鬼混去了。
刚送走这波儿,一对男女推门而入,我忙拉开门。“先生晚上好。”那哥们岁数不大,一身笔挺的西服,手举大哥大,指高气昂,目不下视。“里边请。”
“小姐——”,我愣了,是雪儿,白裙飘飘,她也愣了。“——晚上好!”我把剩下的半句话吐出来,“里边请。”我弯腰鞠躬,她穿一双透明的趿拉板似的凉鞋,脚面白净如玉,脚指甲染成了暗红色。
雪儿迟疑一下,还是跟在那哥们后面往里去。我尾随着,介绍他们到里边靠窗户的位子,我拉开椅子服侍两位坐下,快步拿来菜单。我表现出格外的殷勤,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当然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那哥们点完菜,满脸堆笑地问雪儿爱不爱吃,雪儿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转移回来,说爱吃,那哥们挥挥手象赶苍蝇似的打发我,“先这么着吧。”
“您不来扎啤酒?”我问,腰一直都没有直起来过。
“不能喝,他还开车那。”雪儿象朋友一样的跟我解释。
“没事,先来一扎。”那哥们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我转身快步离开,“啤酒一扎。”我冲吧台喊。
他们两人在那吃着昂贵的菜,窃窃私语着,我站在几步外双手搭在身前含笑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们。雪儿偶尔装作很自然地往我这里看上一眼。
那男的招招手,我急步上前,“加点水。”“是,稍等。”……
那男的招招手,我急步上前,“来点餐巾纸。”“是,稍等。”……
那男的招招手,我急步上前,“拿一烟灰缸。”“是,稍等。”……
那男的招招手,我急步上前,“再来一扎啤酒。”“是,稍等。”……
那男的招招手,我急步上前,“买单。”“7号买单!”我大声冲吧台喊。
“先生,总共是628元。”我加上了两扎啤酒的钱,又凭空多要了一扎的钱。那哥们往我的帐夹子里扔了700块钱,“不用找了。”
“谢谢先生,谢谢小姐。”我像个日本鬼子似的点头哈腰的道谢。
两人起身,我忙跑到门口,拉开门,“先生小姐慢走,欢迎再次光临。”我弯腰鞠躬。
出门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