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郎的圈套-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啊!我没事,你也不要有事好不好?大白痴!你陪我说说话吧,不要不理我,否则……否则我就不要你!你还想不想和我做夫妻啊?”为了不让孟千波睡着,白函情不得不捡孟千波最关心的话说。
“想!我想!娘子,你……你不要离开我。我知道……我不好看,但是,我一定会对你好的。”一听这话,孟千波果然精神得多。
白函情稍稍松口气。“你要对我好吗?有多好?”
“就是……就是……很好……很好……”孟千波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急得满头大汗。
“好啦、好啦,你乖乖躺下。我知道你想对我好,但是只有等你身体好了,才能对我好是不是?”
“我……我没事的,我身体好得很……”
“胡说!你看你现在站都站不起来,你要是不好起来,就不能和我做夫妻了。”
“为……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还没有给我下聘礼,还没有跟我拜堂呀!你想不想和我正式做夫妻?”为了引孟千波说话,白函情没话找话说。
“想!我……我想!”
“所以你一定要好起来,否则光是聘礼你就拿不出来。”
“娘子,你想要什么聘礼?”
“我想想看啊!”白函情想了一会儿,说:“我是白家的少爷,聘礼当然不能一般,我要北方长白山的千年人参,南方海南岛的鲛人珠,东方蓬莱岛的血珊瑚,还有……还有西边火焰山的防火金蝉翼!这四样都是很难拿到的,你要是不快点好起来,就没法子娶我,更加不能和我做夫妻!”
孟千波精神一振,道:“你放心,娘子,我一定……一定会拿到的。”
他艰难的爬起来,白函情连忙扶住他。
孟千波感到浑身骨头都好像散了,疲累欲死,但是要拿到聘礼迎娶白函情的强烈念头支撑着他打坐疗伤。
可是他伤得太重,内力微微运行,顿感经脉寸断,痛得惨叫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躺倒在地。
白函情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扶住他,大叫:“大白痴,你怎么啦?大白痴,你醒醒!”
“水……水……我要喝水……”孟千波呻吟着,没有睁开眼睛。
白函情这时才觉得自己的咽喉也在冒烟。
失血过多,需要补充水分,可是哪里有水?
白函情将自己的长衫撕成了布条,简单包扎一下自己和孟千波身上的刀伤,暂时止了血。
他摇摇晃晃的站起来,眼前一阵发黑,几乎站立不住,随手找了一根手臂粗的树枝做拐杖,一拐一拐地向林子里走去。
走了好一会儿,一阵山风吹过,隐隐传来潺潺的流水声,白函情大喜过望,加快脚步,面前树林渐渐稀疏,山坡下是一个巨大的山谷。
山谷前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数十丈开外,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月光下,反射出水银般的光芒。
白函情喜不自胜,想立刻冲下山坡喝个饱,可看看距离,似乎有些太远,手边又没有装水的容器。他想了想,转身就往回走,决定拖也要把孟千波拖到溪边让他喝个够。
可是,白函情显然低估了孟千波的体重,陷入半昏迷的孟千波简直像一个大铅块。
白函情只得抓住孟千波的手,将孟千波往小溪边拽,好几次用力过度,几乎要昏厥。
路上不知休息了多少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孟千波拉到山坡上。
白函情累得气喘吁吁,身上的刀伤再次裂开,浑身上下都是被锋利的草刃割的血痕,遍体鳞伤,狼狈万分。
一阵阴冷的山风吹来,白函情打了个哆嗦。
不会有鬼吧?白函情打量一下身后,林中一片漆黑,一阵晕眩感袭来,隐隐看见似乎有几处绿光荧荧。
白函情心惊胆战,连忙拖着孟千波往草地跑。
一不小心,脚下被什么东西绊倒,白函情趺了个狗啃泥,来不及翻身便顺着斜坡往下滚。
三转两翻的,一时分不清东西南北,只觉得石块草梗弄得浑身上下疼痛不堪,连平日里最宝贝的脸也被草叶划得隐隐作痛。
好不容易才停下来,白函情已是头昏眼花,什么都看不清楚,忽然觉得身边一暖,一个热呼呼的人压在自己身上。
他忙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孟千波也顺着斜坡滚了下来。
白函情推开他,伸手摸他额头。如火一样烫人,孟千波已经开始发烧了。
白函情只得勉强站起来,拉着孟千波的手又往小溪边拖。
此时,一向娇生惯养的白函情,也不知是哪来的毅力,只想着赶快给孟千波退烧,自己的伤痛全都抛至脑外。
几乎走一步就摔一跤,蹒跚地把孟千波拖到溪边时,白函情快要虚脱,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坐倒在地,只顾着呼呼喘气。
孟千波的脸烧得通红,嘴里嘀嘀咕咕的说:“娘子,我……我们洞房……”
“呸!命都快没了,还洞房呢!”白函情骂道,但一想到孟千波的伤势竟然这样严重,心中又是焦急又是难过。
还没等白函情喘过气来,一阵猛烈的强风吹过,冷得白函情打了个哆嗦。
抬眼一看,天边迅速卷起一片乌云,片刻间就挡住月亮,紧接着,一道闪电划过,竟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大雨很快就把两人淋了个透湿。
白函情呆呆愣了半晌,闭着眼睛抬起头,破口大骂:“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个时候下!老天爷,您是不是来耍我呀!”
他辛辛苦苦才把孟千波弄到小溪边,这时候下起大雨,先前的努力等于白费,气愤难平,他不禁骂起老天爷。
大雨密集,两人成了落汤鸡。白函情被头着散发,水滴顺着头发下滴,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
山间的雨格外的冰冷,白函情原本就失血过多,冷水一浇,冻得嘴唇发青,直打哆嗦。
而孟千波却仍是浑身火烫,烧得迷迷糊糊。
冰冷的雨点落在孟千波的脸上,似乎让他清醒了些,喃喃地道:“娘子,你、你别哭啊……我……我一定会保护你……照顾你……不、不让别人欺负你……”
白函情见他昏迷之中依然对自己念念不忘,心中感动,口中却大骂:“保护个屁呀!自己都快死掉,还在这里说大话!有本事你快点醒过来啊!有本事就别丢下我一个人啊!你知不知道……我、我一个人会害怕呀?呜……呜……”
骂着骂着,他的声音哽咽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混在满脸的雨水里,也分不清楚是泪还是雨。
孟千波却依然迷迷糊糊的说:“娘子,不……不要哭……我没事的……我身体好得很……”
白函情吸吸鼻子,大声道:“你想得倒美!老子才不是为你哭呢!我是在为自己哭,好不好?你真是我的克星,遇到你真是倒霉!不但你欺负我、黑衣人欺负我、林子里的鬼也欺负我,连贼老天都来欺负我,都是你!都是你!你这个孟千波!大白痴!黑炭头!”
白函情自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不但身受重伤,三更半夜在荒郊野外淋雨,身边还守着个生死未卜的重病号。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救无门,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紧紧抓住了白函情,教他越想越伤心,不禁趴在孟千波身上嚎啕大哭起来。
孟千波喃喃地道:“娘子,你……你别哭……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我会保护你……照顾你……永远……永远不离开你……”
白函情抬起头,抽泣着低叫:“这可是你说的哦,你可不要光说大话。我以前都不相信别人的,这次就相信你!你要是做不到,我就砍了你的脑袋当球踢,你明不明白?”
白函情摇摇孟千波,却见他双唇紧闭,似乎没了生息。
“喂!大白痴,你怎么了?”白函情吓得肝胆欲裂,顾不得伤心,紧紧揪住孟千波的衣领,用力摇晃,大叫:“喂!大白痴,你不要吓我啊!不要死啊!你说过照顾我一辈子、保护我一辈子、一辈子都不离开我!你答应过要娶我,和我做夫妻,你不要说话不算话呀!呜……呜……你醒醒……你醒醒,不要离开我……我也不要你的聘礼了,一辈子都乖乖做你娘子,好不好?大白痴!你醒醒呀,你看我一眼啊……呜……”
白函情哭得昏昏沉沉,可是不管他怎么威逼利诱,孟千波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滂沱大雨依然在下,白函情双眼失神,心好像被人挖走了一大块,空空的像是失去一切的知觉。
蒙胧中,似乎有一个白色人影缓缓而来,白函情想努力睁开眼睛看清楚些,却又飘飘忽忽,什么都看不清。
要死了吗?就要死了吗?那一定是来接他到阴间去的牛头马面!可是,如果和大白痴一起死,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吧?
大白痴说过他一定会照顾自己、保护自己,什么妖魔鬼怪都别想欺负他!
紧紧握住孟千波宽厚的手掌,白函情心中逐渐安定,缓缓闭上双眼,终于晕了过去。
第七章
痛!全身上下都痛。
像有千万把锤子、钉子在自己身体里乱敲乱刺。
“啊,好痛……”白函情轻叫一声,猛地睁开眼。
这是什么地方?一间小小的陋室,桌子、墙壁、屋顶全是翠竹编织而成,一股浓浓的药香弥漫在空气中。
白函情皱起眉头,捂住鼻子煽了煽。“好臭!”
他从小就怕吃药,虽然良药苦口,但被逼着吃了几回,每次闻到这股味儿就直皱眉头。
“臭?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子,竟然敢说我的药臭?”
一道尖利的声音传进白函情的耳里,白函情惊跳起来,牵扯到身上的伤口,痛得龇牙咧嘴。
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子走进房间,瞪着一双混浊的小眼睛,气得三羊胡子一翘一翘。
会走路的竹竿!白函情立刻想到这个词,并且说:“你……你是谁呀?”
老头子冷哼一声,“气死阎王!别问!”
白函情身子往床里缩了缩,嘀咕道:“不问就不问,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
老头子气呼呼地给了他一个爆栗,尖着嗓子说:“我的名字就叫别问,我的外号叫气死阎王!你这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知道个屁?”
白函情几乎跳起来,大喜道:“原来、原来您就是神医气死阎王前辈啊!这么说,我……我没死,是您救了我们?”
气死阎王瞪了他一眼,“当然,让你们死在我家门口,丢的可是我的脸!”
白函情不顾身上疼痛,爬下床来,对着气死阎王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笑道:“晚生是白家堡白函情,拜见前辈。”
气死阎王袖子一甩,“我管你白函情、黑函情,我救你只是不想让人死在我家门口,不过,既然救了你,你得给我干活!”
白函情笑嘻嘻地道:“没问题、没问题,前辈救了我们的性命,让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说完,他小心翼翼地问:“前辈,和我一起的那个大……大块头呢?”
“他啊,他跟你不一样,你不过是皮外伤,那个家伙却内脏俱损,经脉寸断。”气死阎王一边说,一边摇头。
白函情吓了一跳,脸上却呵呵笑道:“前辈,您医术高超,救人无数,武林中人人敬仰,这点小伤,前辈您哪里会放在眼里呢?您说是不是?”奉承讨好之意溢于言表。
被拍马屁拍得高兴,气死阎王得意道:“那当然,我气死阎王的名号是白叫的吗?”说完,他却皱起眉头,“他内腑的伤虽重,却难不倒我;难办的是,他体内还有一种罕见的毒!”
“毒?什么毒?”白函情大吃一惊。
“我查了三天三夜的古书,翻遍了十九本毒术大全,基本上可以断定,这种毒名叫‘过家家’。”
“过家家?”白函情差点噗哧一声笑出来,可是看到他一脸严肃,强行忍住,苦着脸问:“什么是过家家啊?”
“这种毒世间罕有,是一种十分歹毒的慢性毒药;看样子,那个家伙已经中毒好几年。中了此毒,外观看来与常人无不同,而且也不会伤人性命,但是随着食入的毒药增多,中毒者的智力会渐渐衰退,最后完全退化到几岁小孩子的水平,只会玩家家酒的游戏,所以这个毒就叫过家家。”
白函情这下子笑不出来了。
原来这个孟千波不是天生的大白痴,而是被人下毒陷害!
是谁这么歹毒?白函情脑袋瓜飞快的转动起来。
要做到长期在孟千波的饮食里下毒,只能是孟家庄的人!孟千波变成笨蛋,最得利的人就是……孟千里!
孟千里最近几年掌管孟家大小生意,着实大出风头;但是如果长子孟千波好好的,这份家业无论如何都落不到庶出的孟千里手中。
白函情又想起这次出门,孟千里跟踪自己和孟千波。自己无意中说破孟千里的阴谋,逼得他杀人灭口,搞不好这次被杀手袭击就是孟千里的主意。
该死的孟千里竟敢打我白三爷的主意,等小爷恢复了武功,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白函情转头又问:“前辈,这种毒……可以解吗?呵呵……想必这种毒到了前辈手里,也不值一提吧?”
气死阎王狠狠瞪他一眼。“臭小子!想激我为他解毒?这把戏太幼稚了吧?哼!天下间还没有毒能难得到我,不过你得给我干活儿!”
他伸手拎住白函情的耳朵,不顾他一路哀叫,拖着他来到一间大屋子。
大屋子里有一个大灶,上面有一口大锅,正翻腾着滚水。
旁边有一个大木桶,而孟千波双眼紧闭、脸色苍白、浑身赤裸的坐在木桶中间,一动也不动。
“大白痴!”白函情急忙冲到桶边,看他消瘦苍白的脸庞,有些心疼,忍不住伸手摸去。
“别碰!他现在浑身都是毒!”
气死阎王把白函情拉开,“你就在这里烧水,每天八大锅,少一滴都不行,明白吗?”
白函情连忙讨好道:“没问题!前辈,只要您能治好他,我给您做牛做马都可以。”
“这傻大个是你什么人?竟然为了他可以给我做牛马!”
白函情脸上一红,“他……呃……他是我的好朋友,为了朋友,我白函情向来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气死阎王抬抬眉,“呵呵,现在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倒也少见!”
白函情脸红红地低头,不好意思的坐在灶前看起火来。
气死阎王命令白函情把锅子里的开水全部倒进桶里,然后又加上水和草药,开始烧第二锅。
可怜白函情这个从来不近庖厨的翩翩君子,为了孟千波,在灶前挥汗如雨,被烟熏得连连咳嗽,不一会儿,就被烟灰熏成了个大花脸。
气死阎王却优闲地在孟千波身上扎银针,“看你朋友的样子,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落到这等地步真是可叹!殊不知红尘多富贵,红尘也多磨难,他中了这种奇毒的原因,不是为权就是为利,不过白家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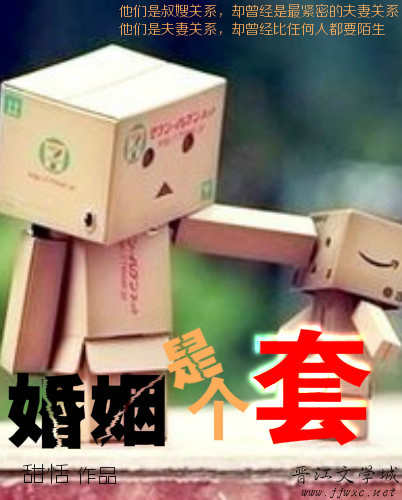

![[古穿今]龙套的逆袭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