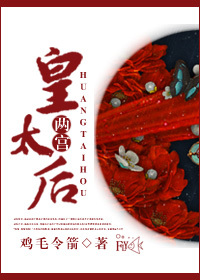太后与我-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相信我,亲爱的宝臣”(他的字;我二人已经渐觉亲密,之后更近),“这是唯一可行之计。我知道总管太监的脾气,对你我来说,宫中有友,非常必要。”
“那就大好,我看得出你对我有意,只管随心所欲便了。”
于是,约会当日,占早早来我处,打扮得恰如“时尚的镜子、礼貌的典范”,戴着六七个价格不菲的戒指。显然没有人会将其当做下人,他看起来像是位爱冒险的骑士游侠,他本就如此。自桂花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如此姣好的少年,优雅秀丽,近乎完美,是“除下面盔的年轻哈利”(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夜很快来临,我们径自往宫中去。暮色仁慈地遮住了我这“书童”的丽质,西苑门无人查问我们,经勤政殿沿中海岸至皇后寝宫驾车只需几分钟。我一到就有人通传:李出来迎接我;占伟给他请安,行满族之礼,态度之恭敬超出骑马侍从应有之义,即便是对主管太监这样有权柄之人。(我猜占是因为他心爱之人同意在当夜与之偷欢,他须随车在外候几个时辰,因老佛爷不到子时不会停歇。)李为了便宜行事,体贴地掌了一盏灯笼,以示我为老佛爷传唤,闲人勿近。
密会桑树下(4)
我离开占之时,他如清晨饱食的公马一样春心动荡,迫不及待。此处无须再三重复我本人的性爱经历。李又备了卢库勒斯式的豪宴,我们对坐一桩桩讲粗俗故事。他满腹都是太后的妙语,她曾这么开始(结束)一则笑话:“从前有个太监,”接着停顿,似乎在考虑下文。“咦,老佛爷,这太监这么了,底下怎么样,接着说啊?”“底下没有啦!”——这是咬字眼的俏皮话,无法译成英文但中文一目了然。可以如此解释:“太监没裤子,就是这故事。”李去探问老佛爷,她正在享用睡前鸦片,连郁小姐为她读书。她问她的熟识鬼子是否已到,叫李莲英去备必不可少的春药。很快她便传唤我。我肩上披件斗篷,穿了双李好意借我的鞋趿拉儿。我步入太后寝宫时,因心有秘密而内疚自责,如担重负。或许老佛爷亦觉察到我略显委靡,但猛烈的春药很快催得我那阳物蠢蠢欲动,膨胀充满欲望。太后做得心满意足,尤其是那晚,我们“倒挂蜡”。太后根本无须春药,已是性欲亢进:除了我所熟知的手法,她欢喜从我身后交合,这归功于她技巧高明,深谙春宫之道。若我未记错,时值六月初,正当每年朝廷迁至太后钟爱的颐和园之前;夏夜短暂,倏忽而过,但老佛爷仍未尽兴,便似永无餍足。她半似母亲般斥责我的同性之好,是年轻人贪图新鲜,糊涂不经事;她以为这会令我折寿,或许还会导致失明。因中国有种迷信说法,经常性或专业地从事男妓之业(不是像我这样纯粹只是被动意义的“兔子”)最终会目力受损。类似还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从后面性交,若被动一方(在交媾当中尤其是射精之时)放屁,那么会引发败血症。已故的医生克里格(Krieg)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名唤西摩尔(Seymour)的英国人,在北京与一名妓女偷欢,罹患血毒症,三日后身亡。不过,就此打住,言归正传。
天已破晓,老佛爷意兴高涨,最后要我和她一番云雨(二人都疲惫痛楚);她没睡过觉,我也同样。她显然淫欲激荡,且颇有些狂躁固执,不单是对我,而是一概而论,尤其是对即将早朝觐见的大学士。
令我惶恐的是,她从凤床上坐起,说:“你就等在这儿。披上袍子,天冷了,等我回来。我会叫连郁服侍我更衣。她来了你就可以告退,到外间去穿衣。”显然,太后是心有邪念:她会如何?“面对神灵之威,凡人无可作为”,就像席勒的《钟之颂歌》所说。
老佛爷出去了。穿过佣人所在的房间只需五十码。通常,太后房内一切动静,从那里都听得到。天意总是弄人,喜欢打乱“鼠与人”的设计。太后径自进了侍女的房间,愉悦地发现——何事?我亲爱的占伟和他中意的连郁被当场拿到;他后来告我,他当时正骑在她身上,不似人而似兽一般,正处于最高潮。他既不能停止又无法抑制,只能一鼓作气行完事,留着老佛爷像愤怒之神一样板着脸站在门厅一侧,但缄默不语,或许此刻沉默是金,而太后在与我欢好之后,看到他人的欲求,不由心怀同情。
尽管我不在近旁,还是听得到太后的长篇斥骂,声渐高昂。“你是把宫里当妓院了吗?”(对占)。“你这小娼妇”(对连),“光天化日就在此处接客,在天子辇下?你们不知淫乱皇宫禁地,于法不容、罪可及诛吗?你怎么进来的?”接着我听到占伟——我也猜到(可怜的孩子)——吓得魂不附体地解释道,是洋侯带他进来的。老佛爷听到此辩白怒发如狂。“洋侯,不错;你叫他猴,他的确是只洋猴儿。”她疾步穿过宫殿,毫不客气地呵斥我:“你竟敢将你这色鬼同伴带到我的深宫内院来,是什么意思?真是胆大包天。我不会姑息你。你也太托大了,尾巴翘不动了。回答我,巴恪思,这次你作何解释,你向来巧言善辩:这下也理屈词穷了吧。”
密会桑树下(5)
我跪下叩头直至额头出血。“老佛爷,我该死,不,在您手下万死莫赎。我是想着您对我的仁慈,请原谅我这个远臣。我如此爱您,我的皇后和女神,我的守护星,我日出的黎明,我宁静夜晚的光芒,您的圣恩给我莫大荣光,我知我不配消受。正是这样,我这可怜虫才斗胆设计了这卑鄙的欺骗。我只觉内疚:陛下怒我是理所当然,就让我这罪人从此永远被关在天堂之外;但我求您,就算是我在临死之前的恳求,饶恕这一对不幸的爱人,让占伟返家,不要告知他的父亲、大学士昆岗,他会用鞭子打死他的;至于连郁,她同我一样,都是罪该万死。但太后陛下是观世音下凡,恳请您对我们三个罪人大发慈悲,令我们再得您恩泽,受您宽恕。我们也深知,原不配如此。”
老佛爷看似被我的求情打动了,这番话说出来远比写下来更有力。“你这放肆的孩子,我可不是非饶你不可?我刚亲过无数次的身子,怎么下得去手打。”
此刻李莲英及时出现。我猜是听到了我情急的求恕;无论怎样,我应该庆幸自己预先向他求助:这事若瞒着他,那才要命了。
老佛爷怒火稍平,对李道:“这真不成事体。巴恪思大胆妄为,破坏规矩,将这公子哥儿偷偷带到宫中,我猜你会说你毫不知情?”
“不是,太后,我知道的,他告诉我了:我的罪,我的罪。我知道太后喜欢有情人,我想您一向心软,会饶了这两个年轻人一时胡闹。”
“要不是我无意撞见他们‘云雨’之中(引自《孟子》: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你会禀报我吗?”
“不会,太后,”李道,他的机敏和远见令人钦佩,“我知道老佛爷行善不喜张扬,您右手如何动作,连左手都不消知道。”
刚才老佛爷引用典故之时,我便知道已经风平浪静了,她的怒火已经逐渐平息。我再次叩头直到额前满是鲜血。“傻孩子,”太后道,“你这俊俏的脸很快就成笑话啦。好吧,我且饶了你们三个,成事不说,既往不咎,遂事不谏(《论语》)。”
李和我一起拜倒,我无力继续磕头,但他的话也弥补了这一缺憾。“老佛爷有口信儿,谢太后恩典,我们便有九世轮回,世世生生,永感太后大恩大德。”
“去传那一对儿。告诉占伟把衣服穿了,刚才他是赤条条的;不过我猜他这会儿没那样激情似火了吧?”
李和我找到二人,已经吓得呆了,相互拥着躲在侍女小室深处,好像两只被猎犬吓破胆的兔子。“跟我们来吧。老佛爷饶了你们了,你(占伟)可回家了,连郁要去伺候老佛爷。”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安慰他们,把他们拉出来。我们回到太后尊前。太后仍旧穿着贴身小衣,但凛凛之相,丝毫不减。即便是几乎赤裸,她依然有翻云覆雨之威。他二人磕头无数,叩谢隆恩,我和李跪在一旁,目中含泪,心存感激。“我这洋侯把责任一己担了;照理他鲁莽妄为,应鞭打四十,但他能言善辩,我已原宥他,也原谅你二人。至于连、占二人,我准你们成婚,作你们的媒人(其实这在她应该叫‘拴婚’)。你父母那边,我想我挑的媳妇他们会接受,而且也不会发现你这孩子的胡闹。”
我们一齐颂道:“太后皇恩浩荡,您对我们有再生之恩。太后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密会桑树下(6)
老佛爷此刻已经恢复了兴致,令其余人等退出寝宫;她命我除去衣衫,只剩一件袍子,跪在凤床旁边。“撅屁股!”她道,她手握一枝藤条,抽打我大概十几下,下手颇重。
李在外间等我:“你受训了!”
“是的,挨啦打。”
“欠,该着啦。也活该我帮你。不过算你机警(一向如此),又逃脱一场大难。千万别跟老佛爷犟嘴,一个劲承认罪过就是(就好像著名律师约翰·西蒙爵士某次在牛津讲到诉讼之时所说)。解铃还是系铃人!”
“快穿了衣服,老佛爷已经到正厅去听奏疏了,军机们已在恭候。你就在前面我们用午膳的侧厅等着,太后陛下回来后,你再离开。占伟可以坐在你车前,我把你自己的戈什护叫来,既然现在都不追究了,老佛爷恐怕也不愿他再做你的下人,毕竟贵为清朝大学士之子。”
老佛爷此刻准备离开寝宫,我跪在外面的厅里。她慈祥地笑道:“我饶了你啦。但下不为例,可一而不可再。”不过她的警告无甚必要,我当时是感情大于理智,犯这个错是出于一己私欲,只想赢得占伟好感,以便他日有机会与他交好。事实上,也确实让我碰上这样的机会。
“给侯爵上点药,他额上出血了。”走向正厅时,老佛爷吩咐道。无数面镜子从各个角度反映出我的可怜面相;我的前额因在砖石地上不停叩头而血流不止。不过,我一个劲磕头也不是徒劳,感动了老佛爷,对我心生怜爱。
稍等片刻之后,占伟和我返回家里;他简直是兴高采烈,不知如何才能报答我的慷慨相救:“仰承保佑,焉得答报,高情若天之高,如地之厚。”
“只要最简单的,”我道,“让我俩更加厚密。若能常相亲近,身体如胶似漆,心跳如一,那便是至极。”
“我说再好没有,”占伟道,“适才我二人已是情投意合,但还要约定个地点,可以互享彼此之情。”其实我们已然无法把持。我们拥抱着,激情似火地亲吻对方,相约一定要在某日得偿所愿。
如此这般,我开始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我所知的太子、贵族和显贵子弟实属不少,无人如占伟这样令我入迷。他对我而言就像失去音讯的桂花,而记忆更清晰。我们常在新净(澡堂)或者他介绍的一个贵族场所相会。这样的爱情在我看来颇具诗意:始终是投缘,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但我无法理解前些日子死去的那个英国教师的想法,他就像野兽般徘徊寻找一个个猎物,哪怕是街头的下三滥,热衷于以五美金发泄他的淫欲(每人或每次,两次就是十美金),在他们肆意放荡(或者是唯利是图)的诱惑中抚慰他奇痒难搔的猥亵。
占伟于六个月之后大婚,场面喜庆;幸运的是发现二人八字儿相合;老佛爷给新人赐了厚奁;他与我的亲密,丝毫没有冲减婚礼的喜悦。连郁生养了六七个孩子,我想他们到今天都仍在世。她一直对我心存感激,说道是对景生情。因为无人比她更了解太后,后者动起怒来,不啻山崩地裂。倘若有人冒犯凤仪(或她认为其有所冒犯),绝不会轻饶。“她发起火来,谁也不敢求饶;她暴怒之时,可谓残暴无匹。”楚楚动人,但是笑里藏刀。
我与占宝臣之交往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事实上,我们最后一次令人陶醉的欢合,是在我六十岁、他逾五十五岁之时。任逝者如斯,我至死不会忘记(这记忆终会成为快乐)维吉尔,《埃涅伊德》。。他后来去了满洲里,接受设在新京的朝廷的委任,他以之为合法政府新京,指日本在满洲里设的傀儡政权,名义上以溥仪为帝,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自那以后我再未见过他和他的妻子,正如诗圣白居易所说:音容两渺茫。我会再见他吗?我无从知道,也无法预见。其时,我已经是耄耋老朽,苟延残喘,看着我那些“英勇的”同胞与德国人玩着并不在行的战争游戏。但我猜,占宝臣和他的妻子会常常想到三十八年前,一个六月的清晨,我们三人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地下跪,求太后饶恕我们在坤宁宫淫乱,老佛爷当时统管着历史悠久的大都元朝的都城(1271—1368),后来的北京。。“一切如影而过,我们都将消亡。”作者注:《旧约·诗篇》。老佛爷,原谅我们所有人吧!
浴室里的不速之客(1)
新净浴室位于后门大街东边的一条胡同里,曾是满族贵族之时髦去处,今日久已关闭。对于皇亲国戚,此处并非寻常的会聚之所,实为男妓之馆。老板与寻常浴室一样,亦是定兴直隶省(今河北)的一个县,在京师西南约九十公里。人氏,但其家族在乾隆朝已经迁入京师。侍者全系直隶本地人,就像我所见过的那个叫荣的男子,面容姣好,忠诚不贰。雅座需预定,大堂上通常的节目是沏茶敬烟、飞短流长。热汤池中,侍者各尽所能。若客人没有其他约会,侍者亦可与之云雨(通常是被动角色)。费用固定为五十两,侍者与老板分得。沐浴及精心薰香之后,我们与事先定好的伙伴尽情缠绵,有时是三人爱得难解难分。通常互有往来,各种花样一一行过。此后,欲望得偿、爱火渐熄,大家在大堂休息,赌博、下棋或者说笑男女情事,尤喜后者。长夜之中,常有按摩和畅饮。此地直似一俱乐部,我想,若无熟人引入,不知端地的客人恐难进入。与淑春堂相比,此处的侍者出身低贱,然而个个招人喜爱。他们善于为客人带来久违的激情,恰如当年庆亲王(奕劻)沉睡的身体被热吻唤醒,得其所欲。
这本充满性事的编年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