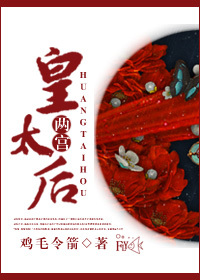̫������-��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ǣ���è�����㣬ȴ��ԸŪʪצ��������
���ǵģ���̫��˵���������뷨�����ƣ����۽��硣��
����Ӣ��ʱ��������������˵��
��ɳ�ʴ壬1902��3�¡�
ֿ�������Ĺ�ĸ����֪���Ѿ����ؾ��ǣ�������ο�����뿪���������ӣ������ͬ�顣������֪����ʼ�����������ѣ����������ҵļ�֣�ŷ������һ�³���������Ϊ����������ʵ�������������ڣ�����������Ŀǰ���Ѻù�ϵ�᳤�ó������������ҵIJ��Ӽ��ճ��������ֻ�����ֱ���������·�����±����ر������١�
Я����ֶŮ������ɽ�������Ѱ¶���ܽ�Ȼʺ�Alexandra��Feodorovna��������ǰ��Ը���챣�����������ڣ�ϲ������
�������ѡ��ҳϵ���ֶ
�����˹����
�������ɳ���𣿡�
���ǵģ����£�����ǰ���Ӽ����ң�����������֮����������ˣ�����Ҫ˵�����dz����ڡ�����ϲ�ҵ�ͬ������֮Ϊ��̫�ˣ������Ϊ���������Ӣ����Ϊ�Ӵ�
������¸����ң��ʺ��������֪������������ȥĪ˹�ƲμӼ�����
���ǵģ����£���̫����һ������������˵����Ů��·������Lucifer����������ռ����Ԥ�⡣��
���ðɣ���̫��˵�����������з�����˯��ʱ��������Ӣ���д������ţ�ϣ�����θ�ڡ��������
���뿪�ˣ��ҵȴ����ʱ�����Ϸ�ү�Ļ����������ݶ����ƹ뷿�����������������ڲ�ͬʱ����ӱ�����ɫ��ʯ��ɵġ�����ɽ�����������ӣ������ij���С��״���ȵķ���̩�������裬��������ӣ�������棬�廨���ŵĴ��������̣���Ǯ�ң���������̴ľ�Ҿߣ������������ڴ˼����߱���С�Ľ������Է���ײ��ҹ������ʱ����δ�ӵ�·�������дҴ����ߣ��ض����������ձ����������ݲ��������аڷŹ���ij��裻�Ҽǵ�1921���ձ����ڵĹ�������ʱ��̫�ӣ��ݷð�ɪ����Atholl���������͵Ͽˣ�Bardic����ʱ���߸����ң����ӵĹܼҲ鿴�˹�����Ԣ����Ҫ��ʮ��֮�ŵļҾ߶�̧��ȥ��������̫�Ӿ�ס��
������������������������������������һ��ʱ���Ŀ�ʼ��6��
�Ϸ�ү�Ը�������ӢһЩ�������������Ҵ����������������ų����IJ�̨���ڷ��Ŷ���˹����ǰ�ˡ��ơ����Ϻͳ�ƿ�����ã�Narzan����Ϊ������ɽ��ˮ�������ƴ����Կ������ǣ��д�ƿ�����ݰƣ��в��ں����Ѿƣ����п�θ�ƣ��ϳ˵����ġ���ʿ�ɵȵȣ�Ӧ�о��С�����ʮ����С���ģ�����Ӣ�����ң���һ���������������գ��������������뵽��˵��ȫ���������ƥ�ȱ���ᡣ����ֻ�������˵IJ�ʳ���ǹ��������ˣ����ҷdz��м�̫���ʢ�顣
�ԵҸ�˹���츳���ض���ϸ��������д����ʢ�磻ȴ�����ҵ������ܾ����������ڶ���˹�������գ��Զ��������൱��Ϥ���������й�������˳���˵����ˡ���ᡢ��Ѽ�������֮�⣬�м����������棨����Ӣ��ʵ��������������Ŀ������ֻ����������δ������˽�¸������м�����������ƫ���ģ���˵��ʳ����С��ҹ���ֳ��м���������ҹ����Ҫ��ЩС�㡣��˯�ߺܲ����һ��Ҫ����Ů����ޣ���������һ��ѻƬ��������˯֮���뿪������˵���Ϸ�үҪ���չ����ɡ�����������ʵ���ϱ���ʳ���㹻һ�������á��������ҵĻش�������Ȼ��
����ʱ˵����������������ǧ����л������ҵ���Ʒ��������Ϊ�����ҡ���
����Ӣ������һ����ǧ������Ʊ������˽��¯�����ߣ�����һǧ�����ҵ����ˣ����������빬�����Ҳ���˶�����֮�ࡣ��̫������֮�������а����������˼�˵���������ͣ���Ҫ�����ڴ���������ƣ����ᵽ���ǿ飩��ƾ�������ʱ�������У����˸�������
���ܿ����ǽ����ȥ�к�������������Ͻ��ǹ�䣬�ȳ��������뿪֮���������⡣��
�Ҷ���˵���Һ�����̫��Ĵ�
���������ǵģ���Ϊ�˿��������������С���������ĺ�ˬ�������→��ˮ������֪ÿһ����Ʒ�ļ۸���������������Ҫ�ۡ����磬���ĸ����谮��̫��۾�����ղſ�����С���ӣ���Ҫ���¡��������������ѲʱЧ������ģݶ���˵���������ڣ���Щ�������������������ӡ���������Ȼ������۸����Ǹ��˶�ʮ�����ࣻ�������������м��Ƕ�ʮ��Ǯһֻ��ʵ�������˶�֪����ֻҪһ��Ǯһֻ��������Ȼ��������ŭ���Ҿ�����ʮ�������࣬���ҵ�ǰ�ΰ��º����˽�̫����������Ƣ�������³����ң����ڶ�̫��������������ע���Դ˽�����Ȥ�Ķ��߿ɲμ���̫��ͳ���µ��й���һ�飬���ֶ��٣�Milton�����ԣ�����������ҳ�ޡ����Ķ��ǣ��ұ��˲����Ƽ����������Ϊ����������ָ���Ǻ����߲����¡����ݡ��ź�̫��һ��Ҫ���ǣ���������Ů�ӣ�����������һ��ϲŭ�����������뵽��˹������Disraeli����дά������Ů������䣺����������Ů�ˣ������Ů�������ԣ�Ҫ����������ӭ������
���ʼ�����š������������Ϊ��ȭ������ȷ�ܱ��䵶ǹ���룬��ϧһ���������ɱ�ΪѪ�ȱ��ҡ�����ǰ����ʷ��Ҳ�ż����ʣ��Գ൨����֮�ģ��ݿ�����֮�ƣ���ͷ��������𣬻�ͷ��β��Ȼ��������֮�ң�1900��������������ǰ������̫��ĵ�λ���������˶��������й���ʥ����ͳ���ߡ�Ҳ���Ƿ�̩������
��˵��������������Ӣ�����ݲ��ء�ղķ˹��Huberty��James����ʹ�ݱ�Χʱ����֮�£�����1900��6��22�գ���ȷ�����ţ���Ŀ�����ڻʳǶ����ⱻ��������»��ͼ��ȣ�����������˵���ν��ھ�ʦ��ѧ�ã����������ߺģ���ѧ������ͬ����ά�µ��ཻ���ܣ�������������ղķ˹������ն�ס����������ʵ�����������顣
������������������������������������һ��ʱ���Ŀ�ʼ��7��
����ʼ���ճ�����»���Ҳ»��л��ϣ���ʱ���������Դ���������������֮�⣬���ǽ���������ţ������������ڣ���������δ���ԡ���������������������������ɼ���ģ���Ҳ���������ӣ��Ҳ¿������ҵĶ������Ѵ����������Ҳ�������������
�̶���̹�����������ʹ�������У������ݵ�ʱ�Ǹ����������������ġ��������˹�������о�����������Ϊפ����ʹ�IJ��Ƶ����Pokotiloff��˽��Ҳ�ܶ��˶�֪�����ܹ�̫������Ӣÿ��ӹض��뵺�ܶ��������ᶽ������Ү��Alexeieff��֮����ȡ����¬����������������ʾ�ν������µ���������ǩ���������ṫԼ����Cassini��Convention��������������Լʱ�����ֲ����������ǽ������ﹰ����������������Ǻ����ն�ս����д�˾��ƣ�����������ʧ�˶���ʡ�����������ͬ��������̣�����������Ļ����ѡ�
������ң�����ÿ���������Ӧ���Ƶ��۸�����֮����ã���ʵ����������֪������ʵ���ǻ���������Ͳ��Ƶ������̸������֮�¡����ἰ����ŷ��ʹ�ڵ���������Ȼһֱ������ͷ֮ʹ���Ҳ���Щ��ʹ����������λ��Ȩ�أ�������ⵡ��������ֻ�DZ�����������ң�ŷ���Ƿ���Ϊ��־����ʹ��ר�����õ���ѵѧԺ�������ޣ���������������Ӧ��ѧУ�������Ǿ�ֹ�������������Բ�ѷ����Ϊʧ�����Ҳ¶����������⣡�������������빬��������ּ��ռǣ�¼��������ע����Ϸ�ү�����е�ÿ�¼���������������ҿ������б�Ҫ�ᵽ��1911������Ӣ����֮���Ȿ�ռǼ�Ϊ�������ܣ���һ����Ϊ��Ȥ�������ʵ�������˽�һ�У��ͻ�ԭ��һ�С�������Ϸ�ү���Ĺ�������ʱ�Եÿ��ţ�����Ψ���Ǵӣ����ռ���������ʵ����������ɿ������ռǺ�ֵ�÷��룬���ڵ�ʱ��ֻ�ֲ�©����Ƥ˹��Pepys����Ƥ˹��1633��1703����Ӣ�������ռ����ߡ���Ʒ�������ʽ�ġ��Ҵ��Թ��ƣ���������ij��ŷ�����Կ��Դﵽ����ʮ������������İ�ͼ�߶���L��Estoile��Ƥ��������ͼ�߶�����������ͳ��ʱ�ڵı���ʷ�ҡ���Ʒ����һ�����峯����������Nineveh�������ޣ�Tyre��һ�������Ѿ���Ҳ��ij�գ���������Ҫ�Ը�����������һ�����������ռDZȾ���֮��������������Ʋ����ǵ���;˵������Ӣ����ȴ���������е���ʵ��
�ҵ������������¿���ʶ���ƣ�ǰ����ȴ��δλ��������ģ���
�����Ҷ��ԣ����������죺�����ζ�������Ҵ��ੲ��ݡ�ʵ�����ܣ��ұ�ľȻ��ԡ����ᰮ���������գ�������ֹ����ʵ�����³����ң����ݵ��ձ��������뾮�С���
������Ȼ�����𣿡����ʡ��������������δ���������װ�����������ԣ�ʧ���Ǹ�������������˵����װ�����ƣ��ⲻ�ܳ��£���
�����˸��������������˵�����ҵ��ֵ����Ҵ�Ϊ�ʺ�������˵��������һ��Ӣ�����Ƚ�����ν���䱦���䣬���������е��⡣��
���ǵģ����£���Ҳʵ����Ը���ҵ�ʱ��Ӣ����˾��֮����ͨ�룬��ʵ����������֪�����Ƿ��ڱ������Դ�Ϊ�ɣ����������Ѳ顣��ָ�ӹ����в���Ϊ�˰�����Ŀ��һ�У���Ӣ�����˵ĵ��ͣ�����˹���������������ء���һ����һ�����̱㽡����ɣ������ⳡս�����������Ĵ���Ľ��������ǰ�����ֵ������������º����¡��������ۻ�����ͬһͷ�������磺����ֱ��������֮�ġ��Ҽǵÿ���������������ʮ��Ǿ�β�ޣ���ʹ���ӣ���Щ����������������������IJƱ������ĵ�ϱ��������һ�ߣ���������������һ��н�����档�������Ǿ��ٵ�ע�⣬������ն��ֻ�����뿪�������̧�����������������������С���ɣ��Ǹ������۾��İ׳գ�Ӣ�������ĵ��Ͳ�Ʒ�������ϸ�ľ��ˡ���
������������������������������������һ��ʱ���Ŀ�ʼ��8��
̸�������˵Ŀ������Ҹ������˸����������˹������Ȥ�¡�1891�������ʶ���֮ʱ�����ij��ӵ��ù㶫����͢�����ܶ�������ʢ������һ���൱�ڴ��ܹܵ��˸����ң��Ǵ�����������ŵ��������Ϊ��м����Ϊ̫�ӵ��¾�Ȼ�����¡�ص���ϯû���κμ���֮�⡣������֮������֪����ԭ������̫�������˸ߴ���ǧ���¬���ķ��С�ѽ���ͨ�룬����ת����������ͽ�̫�����ˣ�̰����ͨ��һ�IJ����˽���ˡ������˹����֪���й������������������ܻ��൱�ɻ�Ϊʲô���ܹ�û���ἰ�������ͣ�Ҳ����Ҳ�Ƿ�Ȼ��ȥ����Ϊ�����˲�ʶ̧�٣�Թ��֮�ģ�˿����ѷ���ܹ���Ϊ�����ĵıɱ�֮�⡣�Ҽǵ��з��ж�˹̩��Ҫ�Ҵ�һ������Ÿ�ɳ�ʣ������һ��Ҫ�������⣬�мǸ������͵İ��������Ƕ��һ��һ��¬������Ǯ���������ٵ���Ŀ�ˣ��Ҳ¶���������͵ø��ࡣ
̸��С�ѣ���˵�����ʲŽ���ʱ����˵����ʹ�ڸ�����С�Ѳ������⣬�⻰�����������ƺ�������Ҳ���뵽��������ÿ������������һǧ��л���Ҳ�������С��Ŀ������Ӣ�Ӵ��������Ŀ�ϼ������Ժ��Բ��ơ�ż����Ҳ����룬�Ժ�ÿ�������Dz���Ҳϣ���Ҵ������л�����������������Ļ����ҵIJ����Ǿ��Բ�����Ӧ���ġ�ƽ�Ķ��ۣ���̫������൱�����Ժ�����û���չ��ҵ�л������֮���������У�ÿ�������Լ����硢����������Ҫ���죬���Ƕ��ụ�����������ۺ�ʱ����ҡ����൱Ƶ����������������Ҫ���ҵ�������ʮ�����ӣ�������Ǹ��൱�ܻ�ӭ�Ŀ��ˡ��Ҳ���Ϊ���ǻ��ˣ�����̫���ȷ���Ĺ��������������ģ�ֻ�����Dz�����Ц������������ҵ����ڴ�����δ�ܾ��֡����ҿ����������Ϸ�ү��Ӱ����������»��������ȡ�����β��ɴݣ��������˹�ն���Rasputin��֮�ڻʺ��������ռ�Ǽ�Cossimo��Ruggieri����ŵ�鵤��˹ͬʱ����ռ�Ǽң��������������֮��÷��ϣ��Midicis�������Ŀ�ɪ�գ���û������Σ�ա���ʹ���������ˣ���ȴ�����⣬���ҿ�������ˣ����з����˷�������Mgr��Favier������ɫ�����ּҺͺ�ѧ�ң�Ҳ�����ĺ����ѡ��������ἰ���ռ��п��Կ���������������˵��һ���൱������ˡ����磬���Ե��������˿�ν������ְȨ���Ҿ�������ʼ�ʼ��ض������µ�̫��������ָ¹Ϊ�����Դ˸�ɱΥ���ߡ����������еġ�Baka����Դ�����ĵġ���¹������ָ��ɵ�ϡ������dz��Ըõ�ʡ���
�����¶���»�кθ������ۣ���
�������ҵ����ѣ��������dz��������ڻ��ǣ������������������ڼ䣬��Ҳ֪����������ͬˮ������֪���쳼�����ϲ���������Ϊ�����£������������ˣ����ڸ���ˣ��������Ϸ�үһƬ���ģ��ڱ����䰲ȫͬʱ��ϣ������λ�����������������˽�һ����������;ͬ�飺�����ĵң����Լ����ˣ�Ц�ˣ����������ҳ�����֮�ϣ����㱾�ˣ��Һܸ�����ˣ����������һ���dzɹ��ģ�����������ǿ������Ը���ֻ�ܳ����Ϸ�ү֮λ��ȡ������������������ֱ����������������̫���ˣ���Ҳֻһ����������˳ƺ���ȫ���ô��������������ӣ�ִ��ʵȨ��������ͬ���裬�����Ǹ���Ȳ��ֵĴ��Ӷ��ѡ���
������������������������������������һ��ʱ���Ŀ�ʼ��9��
��θ����ã�����֮��������һ���ƣ����������������ڽ����ˡ�
��˫�ֲ��������ó�������Ҳ���ó��������Ⱥã���ˡ�Ҳ��ܼ������㣬�ֻ��ߣ���Ҳһͬ��������һǹ����
��Ŷ�����£���û��ô��ĸ�����������Ϊ�ҷ��ģ�����������λ�պ��������˻��棬����һ����̸������֮������
���뿪֮ǰ��˵���Ϸ�ү��˯�����ᴫ���ҡ������������������裬���ؾ���
��һ������ʥ�٣�һ�߳��ſڸм��õĶ���˹ѩ�ѣ�һ��˼���Ŵ��������뵽��һ�ˡ�������������Dz����ء�����о����ˣ�Burdett��Coutts����ʮ�������к��ڵĴ��Ƽң��Կ������Ƶ��������£���òƽ��������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