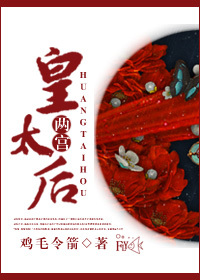太后与我-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一边坐等圣召,一边抽着口感极好的俄罗斯雪茄,一边思考着慈禧令我想到哪一人。最后终于想起是伯德特·库茨男爵夫人(BurdettCoutts),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慈善家,以慷慨著称的名门淑媛,相貌平凡。尽管一国太后与男爵夫人相差迥异,但她们的话音和举止十分相像。小时候我经常被邀参加她在皮卡迪利附近的寓所举办的青年人圣诞派对。我清楚地记得她略带假音的讲话,还有半是强制、半是妩媚的态度,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妇人。另外苏珊·唐利夫人,驻华代理大使的妻子,其夫后来做了荷兰海牙的大臣,也曾与太后有数面之交,她也觉得两人甚为相像,对太后本人也评价颇高。
我坐在那里,恍如梦中一样,正当这时,年轻俊美的小崔子进来召我;他服饰艳俗如女子,但不以为耻,反而神态傲慢,就像亨利三世朝中的爱宠,或者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伟大作品《罗马衰亡》中的一个角色。他对我很恭敬,甚至有点谄媚,令我想起“圣坛的老鼠”,还有一句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奉太后命害死皇帝的崔德隆是他的叔叔;小崔子应该尚在人间,我相信他叔叔也还活着。
行至太后尊前,我叩谢她的厚赏。
“总管太监言道,那顿简餐还合你心意。我猜你不吃烟的?你这个年纪,是不宜碰的。像我这样的老人,浅尝辄止,无伤大雅。我的兄弟桂公爷就太过沉溺了。上海的鸦片船就是你们珠宝商的,你说你们可曾有愧吗?”
“陛下,那确是有碍观瞻,辱我国名。”
接着太后又慷慨地为我封赏。“陛下,我已经无言表达我的感谢:即便再生百次,生生效忠于您,也不能回报您浩荡天恩之万一。”
“下次再传召你,你就可以乘高抬大轿,身着官袍,头戴红珠觐见;你要多用些家臣,才当得起新晋的身份。告诉我,你一定是孑然一身,尚无女眷吧。有否想过情爱之事?不过也无妨,正如佛家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尽管太后只是出于好奇,才有此一问,但我还是想到了凯瑟琳·梅第希(Catherine de Medicis)某次曾以同样的问题,问年轻的蒙哥马利伯爵(Montgomery),他在后来的一次比武中(可能是意外)导致了亨利二世的死亡。蒙哥马利把这当做年轻皇后的示爱。皇后因国王另结新欢戴安娜·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而失宠。自然,我当时无此臆想;不过那时太后的确令我想到卢浮宫陈列的一幅凯瑟琳晚年的画像。太后宽厚地赐座,继续问我:“与我讲讲维多利亚女王之事:她是和她的犹太总理大臣(迪斯雷利)相爱吗?”
“不,陛下,据她丈夫所言,她十分忠贞。”(我不知道是否失言。)
“然则她何不退位,安度天年?”
一个时代的开始(10)
“权力无边,不甘引退,陛下:另外,她也不信任她荒淫的长子。”——“便如同治帝那般”,——慈禧脱口而出——“可叹,此子也相当不孝。”——(便如光绪帝,她插口道。)“那么,”她问,“总理大臣爱她吗?”
“在他的回忆录中,是用了暗含爱慕的语言,但此人向来夸张肆意。他称她为天后、仙人,但他酷爱逢迎,正如其他臣民对女王陛下一样。”
“皇帝既不孝,为什么女王不废黜他?”
“陛下,法律未赋她此权。要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必须由社会三个阶层的代表,通过一项废除法案才能执行,即便他被废,根据长子继承权,王位也会被传给他的长子或长孙。”
“这权力果真大,”太后说,“也果真小。你的家族中有人做过总理吗?”
“父辈中没有,但母辈中有一位,在拿破仑时代(嘉庆年间),另有一位在您摄政初期。”作者常将许多政治人物冒认为亲戚,此处显然又是将和他毫无关系的政客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说成他的先祖:奎克王朝的商人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
“英国还会发生政变吗?”
“回陛下,不会了,除非水往高处流,日悬中天而不落;有人企图发动过一次,确切说是两次,但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说,除非黄河水变清,”老佛爷道,“不过你们朝代也是外族所建,然否?”
“是,陛下,直至今日,德语仍是宫廷语言。”
“我朝亦如此;满语曾是宫廷语言,我们的风俗与蛮子(对汉人的蔑称)大为不同。俗语说,旁观者清。你认为我朝会发生政变吗?”
“陛下厚德治国,绝不会有。”
“北方国民爱戴我,但南人对我既怕且恨。我不会活到千秋万岁;我有生之年,这所有荣华富贵,难道最后只是昙花一现、南柯一梦?”(我想到“被喜爱者”被喜爱者指路易十四。的话:“我在世一日,便延续一日……我的继任也必须善待。”)
正在这时,太监端来三碗剁碎的肝脏喂京巴犬;其中两只打将起来,太后敏捷地分开了它们。接着她迅捷如电地立刻转入另一个话题,她立在当地,言语激烈:“我猜你也听闻珍妃的事了?”
“是的陛下,她对您不忠,您……”
“赐她一死,”老佛爷说,“不错,但你未闻其详。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表情完全变了,倒似更美了;怒火压抑,威仪更现;她看上去好像复仇女神,像是把愤怒直指特洛伊人的赫拉,“天人一怒,焰焰何如?”维吉尔:《埃涅伊德》。当日她得知东宫太后戕害了她心爱之人,必是这样的神情;当日她怒斥端亲王狼子野心,不愧他的狗名,(他的第一个名字“载漪”中,有一个“犬”旁。)必定也是这种神态。我每每想到那时,都觉得心惊胆战。四十年过去了,这一幕依然深深烙在我记忆深处;就像硫酸在我的脉搏里灼烧。即使是贝恩哈特(Bernhardt)夫人扮演的克利欧佩特拉(Cleopatra)和狄奥多拉(Theodora),或者西登斯夫人(Siddons)扮演的麦克白夫人(Macbeth),都无法超越。她哀伤而优雅,态度激烈,双手纤纤可爱,嗓音即使在极端激动之下依然悠扬动听,那个不恭顺的妃子给她的嘲弄和屈辱此刻仍历历在目,那样的痛苦实在无法忍受,她才会大失常态。如果这是表演,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女演员;然而,这显然不是专门为我呈演的戏剧,不是为了宣传渲染而刻意编排出来,以唤得全世界来同情一个横遭诽谤的妇人。她这一扬声发怒,又有几个太监(已有两个在旁侍候)进了会客厅:他们早已听说此事,吓得如同钉在地上一般。
一个时代的开始(11)
李莲英走近前来,但却不敢出声,四肢发抖,诺诺不言,脸色发青:“老佛爷,别再为过去的事烦恼。”
太后对他的劝诫置若罔闻,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悲惨的时刻,她看上去没有任何歉悔,反倒像没有报复痛快,只恨不能再杀那妃子一次。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到优雅的莎拉(Sarah)在《费朵拉》(Fedora)中的台词:“杀了他,杀了他,杀了这个不忠的爱人”,还有在《蝴蝶夫人》(La Tosca)中说的:“为什么我不能再杀他一次(她的爱人背弃了誓言)?”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能将激情净化为怜悯和恐惧:当时我并无激情可净化,只剩了充沛的怜悯和恐惧。我知道太后陛下的脾气,猜测不知她盛怒之下,会不会忘记我是贵客,突然再次排外攘夷起来,那我就万劫不复了。这想法可能荒谬,但当时我猜太后正是歇斯底里,神智失常:今天回想起来我为自己的怯懦颇感羞惭,不过那时我真的希望地上能裂开一条缝让我藏进去。我就好像一只被眼镜蛇吓到的兔子。
太后言道:“7月20、21日,你们洋人轰炸京城,宫廷四周弹片纷飞,我和几名大臣连同太监急于离开北京。荣禄当时不在,若他和我一起,或许……”太后没有讲完(可能她的意思是倘若荣禄大学士在,一定会劝说她饶了珍妃的性命)。天正破晓,我们备了四辆大车出行,扮成农夫行状,等在通向神武门的路上。我派人叫了皇帝和皇后来,我根本无意带珍妃同行,甚至不愿见到她,我知道她对皇帝的影响,她飞扬跋扈,对我相当不敬。不料,她与皇帝同至:我们等在后门,那里有口深井。你既得了我的谕旨可以随意出入紫禁城,下次你再来可去亲见。
我问那胆大包天的女子:“无我的旨意,你前来干什么?”
她答得相当无礼:“因为皇帝不能离开北京,你爱逃你尽可逃。皇帝可以与洋人谈判,他们信他而不信你。”
“大胆贱婢,你知道你在和太后讲话吗?”
“你,你不是太后,你对咸丰帝不忠,现在死罪难逃;你是荣禄的情妇!”
“我听到此处,便命小李子和另一太监架她起来,投入了井中,这等忘恩负义之辈,绝不可姑息。我在车中等着,直到她的呼声止歇,下人压了块巨石在井口,方自离开。”
接着,她沉默片刻。“你是外人。你说:我是对是错?宫里的规矩,有妃子犯上不敬,罪及至诛。”
“她是自寻死路。”我道,“太后也是别无选择。”我还能说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服侍的太监听了我的回答都大为宽慰:李莲英后来告诉我,他当时骇得半死,只怕我言辞稍有不慎,必遭大祸,他更将大难临头!
令我安心的是,老佛爷渐渐恢复镇定,仁和慈善,令我再次联想起我方才提到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伯爵。她说:“现你已知真相,倘外间再有讹传,污我残忍好杀,你可为我澄清。今日就到此处,但我会再召见你,不在此间,就在颐和园或万寿山。你小心保重。孔子有言:‘时不我待。’你这就跪安吧。”接着她优雅地挥手示意我退下,我再拜了一次。
李莲英礼貌地送我穿过皇极殿。六年之后的十一月,我身穿丧服,外披羊皮背心,头戴既无顶珠也无红樱的官帽,脚穿白鞋,头发蓬乱——国葬中规定如此——在巨大的灵车前致礼,里厢安放着太后的圣体。喇嘛们唱着同一调子的挽歌,祈祷她安息。我和李一同走到门外,他引我看九龙壁,那是乾隆期间建造,代表迷信的威严。我的马车候在当地,凤谕钦点我享有特权可停马车在宫门。
“我会再传你的,”李道,“下次再觐见时,勿忘乘轿来。”(李莲英果然信守其言,以后几年中,我们常常见面。)
“无须再送,请留步。”
“遵命。”返程中,我健谈的仆人一路道贺。刚才他不仅被待以上宾之礼,还受了一笔厚赏。
荣禄大人(1)
爱德华七世突发阑尾炎、导致加冕礼夭折之日,几乎是我四十五年居京生活最炎热之时。该日,我惊喜地收到荣禄的名片(其字体平实细小,令我想到英国公使,此人名片上,名字的三个字母大如小号茶杯),门人还报,一位满族官员希望见我,为大学士传话。大学士荣禄是帝国最重要之人物,老佛爷的坚定拥护者,未来摄政王之岳父和今日“满洲国”皇帝之外祖父。
一位高大英俊的满族官员被请至我面前。此人是明显的鹰钩鼻,面色清新健康,三品顶戴。我们互致传统的屈膝礼。他说:“大学士刚刚晋见归来,想邀您即刻到他府邸,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您能否前来?他将传令门房,您能直入他的书房。”当然!我是否愿意访问已被逐出教会的奥坛教区(Autun)主教、与之讨论雾月十八日政变或者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一起讨论第一执政官Charles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在被逐出天主教会之前,任奥坛教区主教。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是他所在时代的政治领袖之一。如前文所注,巴恪思常常毫无理由地自认为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亲戚。?我为之大喜,但是,因为对此荣誉几乎毫无准备,我也明显地不知所措。我说:“敬请向大人转达鄙人的景仰之情,有幸凝望泰山北斗,聆听他的言谈,看牦牛尾拂作者注: 古人在社交聚会时使用此物,尘谈一词即保留下来,成为传统符号。(这个词似乎并不存在;也许巴恪思想说的是清谈。这是一种机智的哲学谈话,产生于汉代末期。清谈老手经常手执马尾拂尘。)指点迷津、导人平静,是无比的荣耀。”
荣禄的代表,五官俊美,名叫耆善,告辞回报去了;我知道中国人讲的“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因此感觉,此时最重要的,乃是咨询一位权威之士,以确定打赏门房需要几何。因而我急忙找到一位朋友,他曾是湘人瞿鸿玑(外务部尚书,后升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7年因“交通报馆”而去职)的秘书,又是满族人,对此重要关节多有了解,能够知道在此情境下,合适的数目是多少。他告诉我,每月,荣禄的门房从访客、求职者那里至少收到两千五百两银子,约合四百英镑(我想,实际数目可能大得多)。通常,总督或巡抚需付五百两,次级官僚递减。根据我的情况,因属特别召见,一百两即可。于是我备足银两,细加包裹,小字署名,由戈什护(满语,意为骑马侍卫)携带,一同前往东厂胡同。此地在京城东部,与皇宫方向相反,离我住处并不太远。胡同之名来自明朝的一个重要机构,它由宦官掌管,是类似于“星法院”的秘密法庭,以拷打和非法处死政治犯闻名。魏忠贤是十六世纪三十年代的总管太监,被尊为“九千岁”,东厂在其治下恶名更著。我的目的地即是魏的私宅。那时,严格意义上的“朝廷”位于皇城之中的宫廷区。
一到荣府大门,我就想起人说,“大学士荣府繁华如市”。狭窄的巷子里挤满骡车(那时少有人力车,也不会聚集应召)、官员的扈从及其马匹、蓝白顶戴希望得见的官员、在门内便利地方的两顶轿子,更不用说到处是卖食物和清凉夏饮的小贩、乞丐、衣衫褴褛的旗兵。荣禄的一队亲兵全副武装,一脸凶相和警惕,守着大门。
荣禄大人(2)
戈什护呈上我的名片,以及最重要的“门赏”;一位面色肃然、留胡须的门人出来迎候,他着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