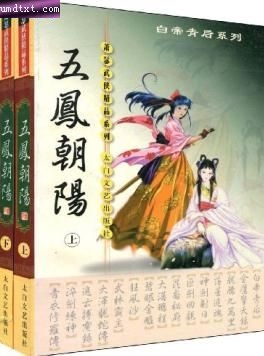金鸡朝阳-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声门响,近来一个浑身散发着古龙香水味的少女。她替我和海浪松了绑,说道:“大姐大说了,只要你俩能帮我们打次架,给一万的酬劳。”她丢过来一叠整齐的百元大钞,说:“这是五千,等你们把事情搞定,再付五千。”这份酬劳是我和海浪幸苦一年才可赚得到的,我正要问个详细,她已出门去了,我忙跟了出去。
想不到从库房出来,过两条长廊,出现的是一间大迪吧。震耳的音乐和五光十色的幻影灯加速着不停扭摆的人们的疯狂,领舞台上及弹簧板上着三点式的金发女人不停的叫嚣,不停的扭摆,展露着她们勾魂夺魄的美乳和俏臀。辣妹儿在左边楼上的看台向这儿招了招手,一脸的笑意。我视而不见,向一边的柜台叫了两杯啤酒。海浪接了一杯,一仰脖子干了,我和他心照不宣,这事算是接下了。辣妹儿走下楼来,坐在了我右首,她接过调酒师递上来的一杯红酒,轻轻咂了一口,问道:“怎么样?” 我叩了叩桌子,说:“你手下那么多兄弟,犯得着请我们俩个吗?”她撇了撇嘴,一本正经的说:“呆会一场硬战,搞不好是要丢命的。”我怔了怔,海浪跳起来说:“你不是只要我们打场架嘛,怎么会有丢命的危险?”他推了我一把, 不悦道:“我们走,犯不着。”我坐着没动,只是看着她。辣妹儿盯着我,微微笑了笑,我一眼瞅见她握酒杯的手颤了一下,看的出她害怕了,我握了握她的肩,如同柔若无骨一般,一股涌起的激情让我义无反顾的答应了她:“我帮你。”这绝非是一种冲动。
大厅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嘎然而止,舞动的人群也瞬间静止,五颜六色的幻影灯光换成了刺眼的大日光灯,剩下的便是大家因跳动而粗重的呼吸及口中浓重的烟酒味,还有那散发的各种香水味掺杂着浑浊的空气里刺鼻的汗臭,让人恶心。我忍不住捂了捂鼻子。
大门被推开了,涌进来一大帮子人,皆是手持钢管和西瓜刀。为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一脚将旁边的桌子踢到大厅中央,拍桌喝道:“辣妹儿,滚出来!”周围的人群一窝蜂的涌了上前,当中一小子跳将道:“姓张的,你湖里的敢跑到我们思明来砸场子!”那男人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往桌上一碰,右手上的西瓜刀狠很劈下,嵌入那小子的肩膀里,鲜血长流。
厅里的人都操了家伙,可不论装备还是是否能打都不敌那男人的手下,皆是弄的头破血流。辣妹儿抢上前去,一个跳跃翻上了桌面,那男人眼疾手快,一个扫腿将她掀翻在桌上,上前一把扯住她的头发往桌面上猛磕了几下。我一咬牙,正要冲上前去,却叫海浪拉住了。
“张汉兄弟,久违了。”厅楼上走下来又一名中年汉子,他近前扬声道:“我阙冬在思明区里当了十三年的东家,没人敢犯过我,辣妹儿是我手下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吧!”
张汉说:“这小婊子剁了我儿子的两根手指头,我今天要不废了她一只手,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是你王八儿子毛手毛脚,先犯我的。”辣妹儿仰着头,往他脸上啐了一口。
张汉就是两巴掌,他旁边的一名手下上前扯直了辣妹儿的左手按到桌上。张汉瞅了瞅阙冬,邪笑道:“思明区十三年的东家?我呸,老子早瞧你不顺眼了,今天我还亲自动手卸了她一只手,你又能奈我何!”阙冬正要发作,他身后一名手下忙拉住了他,附耳细语了几句,阙冬一脸爆炸的愤怒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张汉一脸得意,说:“迪厅太小,我还有两百多号兄弟候在外面呢!”阙冬一张脸顿如霜打了的茄子,他低头原地转了两圈,龟缩着头指了指被按在桌上的辣妹儿,说:“你真剁了人家宝贝儿子两根手指头?该受罚了。”一个转身,便自顾上楼去了。
“王八蛋,你怎么当人家老大的?”我在后面吼了一声。
阙冬回头,眯着眼睛看了看我,一脸的陌生,说:“归哪条街的?呆会煮了你。”
“煮你妈!”我扔出手中的啤酒杯,砸中了他的额头。酒杯没碎,他头破了。
张汉一边看的高兴。
阙冬两名贴身手下提着七八寸长的东洋刀过来了。我夺了海浪手中的啤酒杯,奔了过去,在离那两人一丈距离处,我将手中啤酒杯往空中一抛,喊一声海浪。后面奔上来的海浪飞起一脚,啤酒杯在空中拐了个九十度的弯,砸在了张汉的脸上。酒杯碎了,他脸也烂了。海浪一个小擒拿手夺了旁边一人的西瓜刀,架在了正嗷嗷乱叫的张汉的脖子上。我两个长拳,印在了那俩人的眼眶上,顺手收了一柄东洋刀,制住了一脸茫然的阙东。
辣妹儿从桌上滚了下来,她一手按着流血的额头晃趔趔的走到阙冬面前。阙冬缩了缩脖子,不知道是畏惧我的东洋刀还是她犀利的眼神?他一脸乞求的看着她,苦笑,憋的难看。辣妹儿盯了他片刻,转身走了。
我们三个离开了。当然,没有人敢拦。
救了辣妹儿,我很高兴。不是因为冒险;不是因为英雄救美; 不是因为要名震厦门,我感觉我像在蜕变、在飞扬,也感觉到脑后盘旋着两双复仇的眼睛。我想,阙冬和张汉是不会放过我和海浪的。我义无反顾,这好比我手中锃亮锋利的东洋刀,致命的武器,同样也是最能在打斗中逼发出人的最高潜力和求生欲,欲罢不能。
第二章 混沌 (上节)
2
我、海浪、辣妹儿,我们三个离开了厦门,搭上了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她说,她有个当大官的表叔在北京工作,为人和蔼,可以投靠。
我们都知道,等的时间是最漫长也是最难熬的,做火车便是这样,静静的等候终点站的到来,郁闷的很。从一上车,我边晕、狂吐,一点东西吃不下,到的后来只能吐黄水。海浪只是帮我搓后背,他说这样会好受点。我头晕乎乎的,身子发软,心想这卧铺比硬座好不了多少,治不住这可恶的晕。辣妹儿睡对面一张铺上,她剥了个桔子递过来,我没接,她猜是我手上无力,便送到了我嘴边,我没张嘴。她笑了笑,说:“怎么连张嘴的力气读没有了?看你这么能打,想不到还会晕车。”我半眯着眼瞄了瞄她,张开了嘴,她便掰了片桔囊递到我嘴边,我头稍微往前一挺,一口咬住了她的拇指,她倒没有作声,一手捏紧了我的鼻子。
火车忽然进了隧道,车厢内瞬间暗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一阵冲动,一手揽紧了她的腰,一手抓住了她的右乳。海浪就在一边,她不敢吱声,只颤了一下,便挣扎着想逃离。我发软的身体充满了力量,只是头更晕了,醉酒般的要吻她,她手上的桔子一把拍在了我脸上,稀哩哗啦的。我忙伸手去擦,她跳开了。
车厢内突的光亮了,火车出了隧道。
海浪看着我一脸的橘子,莫名其妙。我只是嘿嘿的笑,她瞪了我一眼,我伸了一只手掌,呈爪子状托着看着。海浪禁不住问了一声:“干嘛?”我得意的饿笑:“真大!”她脸唰的红了,只是那妆化的浓,只有我发现了。我弹了弹五根指头,问海浪:“她是不是还欠我们五千块钱呐?”海浪笑笑,回答说:“我看她是还不出来了。”她跺了跺脚,轻啐道:“真不知道你是真晕还是假晕?!”
天色渐暗,车厢内亮起了灯。我隔着玻璃看着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香蕉林,一大串一大串的香蕉榨弯了枝头,叫人看的高兴。其实我不能肯定它是香蕉,芭蕉和香蕉总是有区别的,只是我喜欢吃这东西。
火车一声嘶鸣,在一个不知名的站口停了下来。我开了窗,下面站满了卖香蕉的人,看她们仰着头不停的吆喝,不停的跟车上的乘客讨价还价。我托着下巴看着远处通红的夕阳,记得谁说过‘夕阳无限美’,我从没认真观察过夕阳如何个美法,今天有这闲暇,待我要好好的去欣赏它时,雾蒙蒙的一片又阻隔了我的视线。原来,是不远处冉冉飘升的炊烟。那是个古旧的村落,就因为每栋房顶上还耸着一个烟囱,屋里的老人孩子肯定做好了饭菜等候着卖完香蕉的家人归来。我觉得这一刻好美,舒服的吐了口气,眼眶中却不觉掉下两颗泪来,我想,我的父母亲也肯定等候着我这几年未归的游子,等候着我的归来。
辣妹儿将头探出窗外,轻轻问我:“想吃吗?”她的语气很温柔,促使我点了点头。她买了两大串上来,摘了一根,剥了皮,递到我嘴边。
“不怕他又咬你?”海浪一边笑。
她也笑,说:“香蕉不比橘子,他不规矩,这么长伸到喉咙里,噎死他。”
海浪说:“半死不活的时候,还得你给他做人工呼吸。”
“那样不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我插了一句。
她趁势将香蕉塞到了我嘴里,嗔道:“就怕你得了便宜,还要喊非礼。”
我大笑,嘴里嚼烂的香蕉喷了出来,砸了她一脸。
夜深了,渐渐犯困,迷迷糊糊中听得辣妹儿向海浪问我的名字。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两点多了,我脑袋清醒了些,四肢也上了口气,看看边上,海浪和辣妹儿睡的正香。我喝了杯水,有些尿意,便起身去厕所。
“喂,大哥,我这条领带漂亮吧?!”
“多少?”
“八百。”
厕所回来,见一边铺上一个光头男人跟另一个男的吹嘘,还有一女的跪在他们面前啜泣。那光头抚摸着脖子上的领带,轻问道:“大哥,我估计能分多少?”那男的一脸不耐烦,朝地上那女人的胸口踹了一脚。她依旧爬起来跪着,哭的不敢大声,只是捂着嘴撕心裂肺的抽。光头挠了挠后脑勺,又问了一遍。那男的漫不经心,淡淡的回了一句:“五十万吧!”光头兴奋的握了握拳头,忙爬起身半跪在床铺上,追问道:“什么时候给呀?”那男的看了看他,坐起身来,又朝那女的踹了一脚,这一脚看的出踹的很轻,心不在焉的。那光头耐不住了,禁不住扯了扯那男人的袖角,说:“大哥,我那份提一成出来给您喝茶,您现在就分了给我吧!”那男人点了根烟,说:“还怕我吞了你的饿那份?”光头忙赔笑:“我哪敢有哪个意思,只是这种活做久了,搞不好有钱也没命花。——我想洗手。”那男人猛的盯着他,两眼生光,光头一时局促,往后仰了仰,是害怕了。
地上跪着的女人还在抽,只是现在的抽搐较先前哭泣的抽动大不相同,她不时的吸着鼻子,嘴里溢出口水。我吃一惊,看她定是犯了毒瘾。她跪着抱住了那男人的腿,鼻涕唾液弄了他一裤子。那男人怒极,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不停的往床沿上撞。我站的久了,在这晃悠悠的车厢里又开始头晕了,胃里泛酸,一阵一阵的往上涌,我忙点了支烟,蹲在了地上。那女人开始叫了,含含糊糊的,就像她额头上冒出的血,染上皮肤,印了床沿,淌了地面,浸湿了蓬乱的红头发,蔓延开来。她躺在地上,身体仿佛比太平间里的尸体还要僵硬、沉重,悄无声息,只有那一双因血流入而不停眨动的眼睛告诉着旁观者她还没死,还有一口气在。
“大哥,你分了给我吧!”光头催促着。
“分什么?”
“钱呐,我的那份钱,我真的要洗手。”
“到了老爷子那再说。”
光头猛的从腰间拔出了一把枪,抵住了那男人的太阳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见识到枪,很兴奋,嘴上的烟不觉吸的作响,‘吧嗒’一声,我吓了一跳,心想枪声或许就是这样,扳机一扣,那男人的脑袋便要开花,跟烟花一样。光头低吼着:“你别逼我,钱!”那男人动也不动,嘴唇挑了挑,说:“你一开枪,也跑不掉。”光头大口大口的喘气,握枪的手不觉颤抖起来。那男人笑了,诡异而邪恶,说:“你这副德性,要被警察逮了不用严刑逼供,也就招了。我看你,死了算了,倒省的我劳心。”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传入了光头的耳里让他心惊肉跳。他咬紧了牙,腮帮子鼓的厉害,他一把抓起床上的被褥隔在了枪口的前面。他是下定了决心不要那五十万块钱了,他下定了决心要杀他。
第二章 混沌 (中节)
他快,那男人更快。
枪飞了,落在了地上。
那男人制住了光头,死死的勒紧了他脖子上那条价值八百元的领带。
光头终于断了气,留下的只有让人难忘的垂死挣扎,死不瞑目啊。
火车震的厉害,我的头都快炸了,手上的香烟燃尽了,烟蒂上还有一颗火种,我用力拧熄了,手掌中辣辣的烫仍清醒不了我的脑袋。一个趔趄出去,那男人在窗玻璃的反光中发现了我。一声枪响,几乎让我魂飞魄散。开枪了,他开枪了,一个杀人犯是绝不允许有事件目击者的,我在等脑浆涂地或是鲜血长流。片刻,车依旧轰隆隆的声音,我的头仍然胀的难受,没有脑浆涂地和鲜血长流。那地上躺着的女人爬起来了,一身的血,手上却多了一把枪,是她开的枪,她瞄准的是那男人,可惜血泪模糊的双眼让子弹打在了一边铁栏杆上。那男人同样吓了一跳。第二次枪响了,是那男人发出的,她没有叹息,因为她根本没有叹息的时间和余地。她死了。
我拼命的跑,脑中不停的嗡嗡作响,跌跌撞撞中全是海浪和辣妹儿的影象,是幻觉,他们的召唤,我的抗拒……
最终,我跳了车。从窗户口跳的。
面对赶尽杀绝,也只有置之死地。
天朦朦亮。
我醒了,脑袋醒了,除去了混沌和晕乎。我还活着,可眼睛没力气睁开,身体冻的僵硬,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横尸路边的悲哀。深吸了口气,清新的,悄无声息的,真舒服。舒服的又睡着了,幻想着这样的死法也不错。
呜——呜——呜——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火车鸣叫声,咔嚓喀嚓的往这边开来。吵吵的,赶走了清新,驱逐了舒服,我又醒了。声音越来越大,轰隆轰隆的压进,它太庞大了,它毫不畏惧我挡它的路
它要压扁我了,我的灵魂在逃蹿,可恨一副僵硬的躯体死死困住,臭皮囊。一声呼啸,它风驰电掣的过去了,渐行渐远,轰隆隆的声音逐渐模糊。我依然活着。
一线曙光温暖的洒在了我的右手上,它顺着手臂爬上了肩膀,又小心翼翼的覆盖了我的右眼,红红的光亮开启了眼睛的大门。我看着天边的朝阳,感觉身体在漂浮,在飞升,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朝向一个美丽的地方——是梦乡。
当我再次腥来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