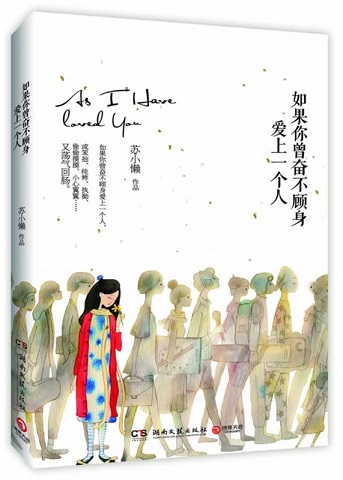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点永远在移动中,这楼里的人真正需要的是给别人一个位置较低的定性(以此让别人在自己面前永远没有优越感),而没人会真有永远盯着你七情六欲的好奇,祝响亮只是这一年度的一个花絮,会过去的。
比如在眼下的节骨眼上,更多人的视线和好奇又被牵引到了咸鱼翻身、火线上位的钟处身上。因为他携手虞大头之后的强势,日益关系到各个部门利益的重新分配。
3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猜测,钟处可能挤掉陈方明,捞到那个他盼了多少年的“副局”位置。
但也有人不这样认为。
卓立的语气里就透着对钟处的不以为然。他说,这年头,一个人捧住一个领导的大腿又算得了什么?除非那是省委领导的大腿。别的大腿虽有用,但也未必太管用,你想,现在的头儿门槛有多精,如果你群众基础差,得票太少,他是吃不消挺你的,现在的领导是很精的,谁会豁出去挑担子?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竞聘得票太低,粘了领导也白粘。
对此,程珊珊表示异议,她的鼻子里喷出了不屑,她说,卓立啊你真纯,群众投票之后,党委会还要再投票,后者占70%比重,你不捧70%的大腿,你还是回去捧小学数学课本好?
程珊珊的嗓门开始渐高,她说,再说,他(钟处)的票为什么一定就少?我看未必!这两年单位效益不好,人是越想越明白了,自己是否投一个人的票,得看看他可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一个人如果只是老好人,提拔他,那只是他自己的好事,关我们什么屁事?!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火爆强人,哪怕我气场与他再不对路,只要他能让单位效益好一点,让我们的饭碗牢靠一点,我都会投他一票,否则,我绝不投他的。
程珊珊含沙射影,我知道她平时就不太看得上陈方明,嫌他蔫,嫌他只顾自己,不为手下人请命。
程珊珊说到这些,脸上就好像在生气。我知道她和毛亚亚是大学同班同学,现在毛亚亚已经是副科长了,程珊珊对此是不服气的,她常嘀咕,人家是有人挺的!我和毛亚亚有啥比头,钟处会为手下人去争去要,哪像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有的人最好啥事也不管,啥事也别对他烦,那他还占着这个位置干嘛。她说,你们以为他会对谁好,屁,他只对他自己好,他就想着自己的乌纱帽。
程珊珊的眼角扫了我这边一眼,摆出一副“你去打小报告好了”的老娘架式。
这女人口无遮挡,我平时就嫌她叽歪。现在她的这番论调,又让我想起几年前毛亚亚分析李瑞汤丽娟PK的利益关系。我想,她们是女人,所以她们都靠直觉行事。
4
丁宁不知从哪儿听到了些什么,他的神色已从对钟处“夫人外交”的义愤中超脱出来。
有一天中午,他在我面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以为钟真的成红人了?屁!
他说,人家用他,是因为他会咬人! 他说,你知道吗,越狠的人越容易被别人利用得惨。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就闭口不说了。
他高深莫测的样子使我费解。 晚上我在家里上网的时候,不知怎么又想起了他的话。
咬人,咬什么人?莫非是老虞想借钟处去咬别的什么人吧?
这么一转念,竟使我自以为豁然开朗:
这半年来,由于副局长胡士忠将退,又由于局长老虞及厅里主要领导对副局长接班人选至今态度暧昧,这楼里的许多处长们于是急得像无头苍蝇开始了活动,于是悄然间树起了许多山头和团队,人一互相挤兑,压力就铺天盖地。据传,洪彤等处长心急火燎地掠过这楼里的人直接去找厅里的关系了。而在这些人中,老资历的常务副局长蔡副局长多年来一直与局长老虞你来我往地暗斗,眼下老蔡想力挺自己分管的机要处处长张战或社研处的陈方明上,据说老蔡将活动网络蔓延到了省里的某位头儿那里之外,还在拉这次不可能上的楼春、陈叔立等资历较浅的处长作盟友。他们的联盟又引起了别的对手的焦虑……这乱哄哄的一切显然让老虞不爽。
而要消除这番混乱,要么是老虞自己早点亮出人选答案(但这年头,这答案也未必真的全由他决定,对于副局长一级,他有权,但不是全权);要么是老虞强力猛挺某一位,让别人死心(但混到他这一步的人,不可能这么幼稚,因为一个人被钦点,剩下的就全成了灰心人,这可能使自己一下子树敌太多),但他都做不到,他只能像小学生拖作业一样用拖延来回避问题,在暧昧中调度别人的欲求,以他的经验,暧昧才是持久的硬道理。但暧昧又不是长远之策,尤其是这年头,你越暧昧下属们就越性急。他们真是欠揍。
但自己出面揍,又不是太妥。所以,放眼过去,钟处就是一个合适的人手,让他去咬吧。
因为钟会咬人。他的性格会咬人。像一条狗一样会咬人。
我想钟处去年还在嘲笑虞大头把陈方明、安重中当成了乖乖狗,而如今人家把他当作了一条咬人狗,他一乐颠,还不是同样找不到北了,以为别人用自己了,找不到北了。
这一阵,我也在学陈方明看了点历史书。
我发现各朝各代的职场人生虽千姿态百态,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人对于“用不用自己”的超级敏感。一旦上司抛过来一个 “用你”的温暖眼神,心里立马暖和得全忘了什么“归隐”、“散淡”、“对立”,统统见鬼去吧。
5
如果说这阵子钟处因为“被用”而温暖吠叫,那么,如今被搁在了冷宫架子上的陈方明则显得寂寥。
这就让人纳闷了,像陈方明这样的温和之人,他哪里得罪了虞大头呢?虞为什么这阵子让钟先奔着陈开咬呢?
“怎么会不得罪呢?”有一天夜里,综合处的“愤青”林伟新在网上和我聊天时说。
他说,你们的陈方明处长,你别看他谦和成那样,他的路子其实是很粗的,底气是很足的,你知道省委组织部长夏虹宁是他的战友吗,当年,正因为陈方明在安河市收集先进材料时发现了夏虹宁这个教师,才使夏成为全省树立的典型,并从那个地级市出来,慢慢提拔到组织部长这个位子上。单靠这一点,他就比这局里其他处长的背景要粗硬得多,更何况,夏现在还常到陈方明家去喝酒,你想想,这年头能到别人家去喝,而不是去饭店喝,这是啥关系啊。
我想,难怪老虞看着陈方明要不爽了!可能是犯酸,也可能是觉得你背后有人又怎么样,老子偏不买这些账又怎么样,老子偏看不惯你们攀到上面去的急相,你们别搞错了,我是这儿的主,给你们来个下马威你们又能如何?
那么,他为什么要让钟处先奔着陈方明开咬呢?
林伟新分析,首先因为他俩是竞争对手,钟处会起斗性;其次,长期与虞大头不和的蔡副局长分管陈方明,这次蔡力推自己分管的张战和陈方明两位下属,虞大头心态微妙……再次,陈的性格有点蔫,咬他,不至于强劲反弹,他会忍,从而不至使场面失控,正因此,杀一儆百,这个下马威才有效并可控。这不就是所谓的马善被人骑吗?
我这么一听,简直惊呆了。我想,原先我们还在抱怨钟处从社研处抢走了“乡村经济”,原来是我们吃错了醋,原来那是老虞的砝码!
这么想来我们真是书呆子一样,“乡村经济”这一块谁做得好谁做不好,真是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成了让人爽或者不爽的砝码。
我感到了自己的幼稚,几个月前我们还在像傻瓜一样地在乎这事,其实这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显然自作多情了。我们有什么好难受的,放在这样的格局里看,那些头儿脑袋里压根儿没有我们难受的空间。
树倒下来,谁会注意到一只蚂蚁的伤心。在这楼里,我丧失了难受的资格。至于我高不高兴,那更是缈远到高级阶段的诉求。
我明白这些,就像现在了悟了暧昧、和稀泥、霸道各有各的功用,但我还是恨它们,因为它们让人不爽。
6
星期四,有两位加拿大客人来我们单位洽谈一个项目。晚上虞局长和一些中层请他们吃饭,秘书处说我英语好,让我相帮做一下翻译。
我坐在老外旁边,给他们译这桌人东一句西一句对他们的寒喧,慢慢地就没我什么事了,因为老虞和中层们形成了他们自己兴高采烈的话题,而不知不觉中把陪两位老外说话的事留给了我,好在两位老外对这桌上的菜更感好奇,他们看到了整条活鱼还有鸽子,有些怕的样子,我一边和老外聊着,一边目击中层们围绕虞大头的争风。
机要处处长张战敬了老虞一杯酒,他说他认同厅里准备在我局推广中心制,他说这样可以资源共享。他还没说完,钟处就把酒对老虞说,厅里的头儿这回不知是怎么拍脑袋的,一会儿一个机构设置,一会儿又一个新主意,那么原来的设置呢,两套体系不是混了。张战又给老虞敬了一杯,表示对钟处观点的异议。接着钟处再反驳回来……该看虞大头点谁的头了,虞大头没具体点谁的头,他在两边的话锋中东倒一下西歪一下。桌上的人都喝多了,一帮人后来不知怎么说起虞大头对这桌上的谁干的活最放心这话题,钟处说肯定最放心楼春,楼春做的事虞局长是100%放心的,而我们做的只是80%放心。楼春急忙跳起来,说哪里哪里,虞局你说是不是,如果我是100%,那么钟处就是120%。楼春又去指一直坐在一边不太声响的陈方明,他说,噢,对了,是陈方明,你们都忘了,绝对是老陈,他150%。钟处说,老陈嘛 ,绝对是200%,我一直把他当偶像的噢。钟处拎起酒杯递过去说,来,老陈,我敬偶像一杯。陈方明有些不自在地瞥了虞大头一眼,他说,老钟,这阵子你干得那么多,我们该敬敬你辛苦了,老虞你说是不是,老钟这阵子真是好点子不断啊,老虞最喜欢的当然是他……
虞大头爽歪歪地坐在他们中间,他说,都喜欢,都喜欢,我都喜欢。
两位老外问我,他们在说啥,那么高兴。我说,他们在开玩笑。
我为自己的快速回答得意。因为他们确实像是在开玩笑,他们开玩笑的时候像幼儿园小朋友在过家家。
7
即使坐在热火朝天的酒桌上,我也能瞥见陈方明遏制不住的倦意和郁闷。
在许多瞬间,我能感觉得到他在心里想把一切看淡的意念,但更多时候,你依然能听到他那声溜到了嘴边的叹息。
我理解他的叹息,一个深呼吸也许能让自己的理智过关,但情感总是滞在后面,它骗不了自己,所以情感往往是过不了关的。
而我的纳闷在于:虞大头以前一直和陈方明好好的,不管怎么说,友好了那么多年,总是有点情份的,怎么说咬就咬了呢?
有一天我去传达室取报纸,没想到大妈黄珍芝在无意中解答了我的疑问。
当时是中午1点多,她可能闲得发慌,好不容易遇到我这么个进来看邮件并和她瞎扯了几句的人,于是几句话就点爆了她的谈性。
她说,男人之间好不好的,有时候比女人还赌气,连我们女人都看不懂他们的小心眼。她说,虞大头以前捧过陈方明又怎么了?我告诉你好了,当初虞大头还和蔡副局长是铁哥们呢,你别看他俩现在较劲较成了冤家对头,想当初,这院子里老蔡可是虞大头的大红人呢。
黄珍芝说,你得记着,人怎么可能永远只喜欢一个人呢?你指望喜欢你的那个人用情专一,但他怎么可能永远只喜欢你一个人呢?!这就像结婚了还会变心呢,讨了老婆还要包二奶呢,哪能就喜欢你一个?更何况男人有点臭权了,还有利益滚在里面,好好坏坏的,不全是感情。
我说,当然不全是感情,还有策略。
她说,不,是策划!什么都可以策划的,今天不喜欢你,明天可以策划得喜欢你;今天喜欢你,明天可以策划得不喜欢你。
我发现她像许多人一样,在单位的角落里愈呆就愈喜欢高屋建瓴地议论人生。
我夸她满嘴哲理,越来越像半仙、哲学家之类的了。她就往我胸前飞了一记老来俏的拳头。
她说,混了这大半辈子的哪有不成仙的。
她说,想当年,虞大头刚从交通厅空降到我们局里时,两眼一摸黑,谁都摸不透他的,几个老资格的副局长可能觉得自己的路被他堵了,对他爱理不理的,根本不买他的账,他的指令连党委会的门槛都出不了,没想到,这个时候蔡副局长却上位了,他粘上去对老虞示好。因为老蔡和前一任头儿关系不好,一直被边缘化,所以现在来了个新局长,对他而言反而是好事。老蔡主动上位,给老虞送去温暖和这局子里的底细,按这楼里当时的说法, “他成了老虞两眼一摸黑时的一盏明灯”,他俩好作了一团,老蔡出谋划策,虞大头就进了角色,镇住了这楼里的不少人精。
黄珍芝说,你知道老蔡那时候有多牛吗,私底下我们把他叫成了老二,他最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是该听老二的还是听老大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是老二大还是老大大。
黄珍芝说,我记得有一次老蔡和我们中心的几位老同志喝酒,喝高了,他就大着舌头告诉我们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说:那些副局那些处长们,我知道他们不爽,但他们不得不听我的,不得不听!虞大头也听我的,他能不听我的吗……
黄珍芝说,我当时还以为他拿住了虞大头的什么把柄呢,呵,说起这些事来,好像就在昨天,十多年前的事好像就在眼前,你说好不好笑,这日子快得也真是邪门了,你能想象那时候老蔡有多少强势吗,你能想象他的眼锋有多少锋利吗?
我说,即使现在他眼神里一天到晚也冷若冰霜的。
她说,那可不一样,现在是怨妇钻了牛角尖的眼光,恨恨的,板得很牢。你离他远点。
我问:他变了很多?
黄珍芝说,是的,那时候他虽也难缠,但那是牛,当时他傍着虞大头,看什么都不顺眼,什么事他都管,得罪了不少人。但事情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人人望他生畏时,没想到,这时老虞突然来了个变脸,反手一巴掌,把老蔡劈到一边去了,给冷落了,转手捧起了猪头胡士忠了。
黄珍芝说,也真是好笑,我们就眼看着老蔡变成了一怨妇,就耳听着他四处抱怨,“妈拉巴子的,我为了帮他(虞大头)理顺这楼里的人头,把这楼里的人都得罪光了,他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