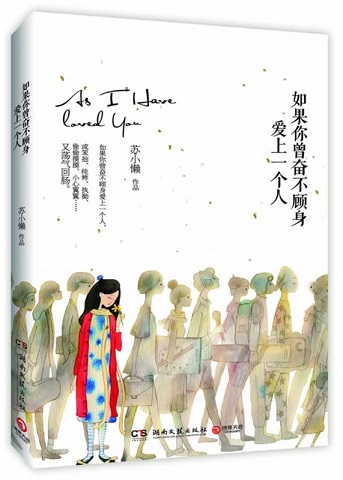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回到家,忍不住把这事倒给了老婆。她说,不管他怎么犯酸,你都初选上了,你不应该要求卓立,甚至你还要感谢他这种人品都来不及,如果他是个讲修养的人,会轮得到你上吗,正因为他是这种德性,所以生活在教训他。
我想,这也是,正因为他恶心,所以我得感谢他,否则哪有我的份。
我爸爸这几天从老家来省城看白内障,住在我家,他听说我初选上了,那个高兴劲,眼睛里都放着光。那神色,让我有点蔑视又让我有点怜悯。不就是个副科吗?但转念一想,老人如果真的这么高兴,我真的该为他拿下来。
17
关于我初选入围这事,陈方明没来找我谈过。虽然每天我们都打几个照面,但他压根没向我提起这事,好像压根没发生过。虽然我了解他的性格,但他的淡漠还是让我纳闷和难受。
科长祝响亮倒把我找去,谈了谈。他说,我们科室两个女的这回表现倒挺好,都上了,你更好,据说票数很高。卓立没上,倒有点意外,唉,他的票数怎会低得那么多?
我今天原本不想为难他,听他这一念叨,我的嘴巴就有点不听使唤,我说:是啊是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意外,别人可能觉得是意料之中,卓立肯定有很多优点,有人看他看到的多是优点,有人看到的则多是缺点,也可能是他把好的一面呈现给一些人,而把另一面流露给另一些人,所以别人对他的判断有分歧。
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祝科长你看人是不准的,说了你别生气,因为你内向,其实我也比较内向,我发现内向的人看人总是不太准,因为内向的人总等着别人来与自己交往,所以他们总觉得那些主动与自己来往的人是好人,但其实,主动的人往往更会掩饰自己。
我说,从更简单的道理来分析,内向的人看人不准,是因为他们很少与各种类型的人主动来往,他们坐等在那儿,所以他们对于人的判断,得到信息的渠道就少,他们的信息由此就一个指向,所以内向的人看人就不太准。
他连忙解释,我看人是准的,我这人其实是外向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生气,但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以后,还在想这问题。我想,看人不准,所以才会身边鸟人围绕。我在单位呆了十年,发现“头儿身边有亲密鸟人”这几乎是个普遍的现象。我曾经不可理解,但此刻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人当到了头儿,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内向的人,都坐等着别人来与自己主动交流,有粘功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而实在、厚道、清高的人多半不会主动去贴。头儿与单位各种类型的人交往少了,对于人的判断,他得到的信息自然就单一,再加上他坐在那个位子所需要的感觉,所喜欢听的好话,使他的判断力自然弱化,于是他就觉得谁与自己走近就是对自己好。慢慢地,身边就围上了几个鸟人,后者在他周围构造着那种令他爽歪歪的氛围,此时其他人即使想粘上去,不鸟都不行。
18
党委会还没开,答辩还没举行。我们初选上的这些人,接下来谁有戏呢?
很多事,人一旦介入,就会不知不觉沉浸其中,越想心里越起盼头,这真有点邪门,比如我,开始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戏,觉得能出口气就已经是赚了,但初选上了以后,我发现自己心态的变化,我竖起耳朵,每天都在不可歇制地留意着动静。
人事处通知:星期五答辩,每人抽一题,评委是党委会成员和处级领导,题目是由几位正副局长每人各出了几个。
丁宁在家里打电话给我。
我说,你胃怎么样?
他说,今天好点了,哎,透露给你一个信息,听我老乡说,这回初选上的人好多都在活动,你没去活动活动?
我说,没有。
他说,党办秘书屠小民是我老乡,他说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隔壁几个办公室一会儿闪过一个人影一会儿闪过一个人影,一包包东西送进去。
我心想,我算了吧,这年头别人谁稀罕你送的那点东西,你送进去了还要坐下来,还要厚着脸皮和他找话说,怎么说,说什么,都是个问题。
丁宁在电话那头说,嘿,听说,杨副局长对送礼的说,你出去吧,否则,我不会给你投票的。
天哪,这不就更难堪了,我简直无法想象这种场景如果落在我身上,我怎么应对。我对电话那头的丁宁说,送礼我就拉倒了吧,要送礼还得准备一块奉上自己的脸皮……
丁宁在电话那头打断我的话,他好意提醒,那么你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要打的,大家都在活动,人心不古啊,你不表示一下,人家说不定觉得你眼里没有他们?打个电话,哪怕用语言表示一下,意思到了,说明你知道他们的重要性了。
我感谢他在病中还记得来提醒我一下。我想,人生真是很奇怪,我们当初在综合处别扭成了乌鸡眼,而到了水很深的社研处,却俨然成了需要相互取暖的好友。
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天,我都在考虑,我怎么办,别人都在活动,都在猛贴热脸,如果我对头儿一声不吭,会不会真的显得自己太牛皮,太目中无人?
那么怎么表示呢?我比较了一下,觉得丁宁建议的打电话方式相对来说,会少点难堪,因为不面对面,中间隔了根电话线。
那么,我什么时候去打呢?我算了一下头儿们的作息,上班的时候他们在办公室,这时候打过去他们人在,但问题是,那时我也在办公室里,众目睽睽之下我怎么打这种电话?
19
下午的时候,人事处突然通知,“首席调研员”答辩提前到明天下午,因为后天星期五省厅领导要来单位视察。
我一下子变得急了,因为要打电话的话,也只有今天下午了。到哪里去打这个电话,我想不好,一趟趟上洗手室,洗手间很大,空旷无人,突然我决定了就在洗手间里打吧。
在洗手间,我照着单位通讯录,用手机一个个拨过去。我压着嗓门,大致说了这个意思,××老总,你好,我们平时也没机会合作,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次请你支持我。
我不知道自己的说法是不是有点直奔主题的傻劲。但如果不直奔主题,那么怎样表达才委婉?我一下子无法急中生智。我想,管他的,我的意思到了,他们知道我在求他们,也就够了。
他们在电话里有的客气,有的一下子严肃起来了,有的“哦”的一声,我不知什么意思,有的说“我了解我了解”,有的说“你搞错了这次我不参加评议”。
而虞大头一听我报了自家姓名,就说,这事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了,好了。我想,我还没说什么呢,他知道我想说什么?
他在那头说,年轻人要自信。
我一急,就结结巴巴地说,虞局长,不是我没自信,而是生怕自己不谦虚,我想,我只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尊敬。他说,那我知道了,知道了。
一圈电话打下来,有的人反应客气,有的人则让我感觉他在离我十万八千里的南极。
而有一些人的语态,则使我直觉他绝对不会投我的票,虽然他也算客气,比如秘书处的张战处长、群文处长贾阳柯、财务处长安重中、设备处长李明居、党务处洪彤处长,他们在电话那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不会投我的票的。坐在卫生间里,我安慰自己,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多大意见,而是因为在这楼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他们有自己要托举的人。而对于综合处的钟处,我没打,因为我知道打也没有用。
在这样的下午三点,我在单位的卫生间悄悄给单位的领导打电话,因为害怕别人听见,我拿着手机压着嗓门,打着打着,什么滋味都涌上来了,我的手心在出汗,耳朵异常敏感对方的每一声气息。
等到我关掉手机,我发现自己需要心理咨询。
20
晚上,我回到家里,对我爸说起这事,我说,难受,特别难受,真的要心理咨询了。
他瞅着我半天,也叹了一口气,他说,你这一代人可能太顺了,求人算什么,我们从来都是求人的,我们贺家人什么时候不求人,以前又不是没求过?想当初,我师范毕业时,你妈刚生下你,拖着两孩子在老家,家里无人照顾,我想分回老家,就去求系里的党支书,他那张脸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听了一句就调头走开去了,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俯身跟着,一边跟着,一边低声哀求他……
我爸对我说,其实你毕业分配的时候,也一样啊,我和你妈为了想让你留在省城找个单位,那么大的雪天,听到一点点线索,就亲戚家、老同学家一家家地拜访,我记得有一次从我一个老同学家里出来你妈眼泪涌出来的样子,你不要忘记了这事啊。人,不求人只是因为还没到底线,到底线了的时候,小人物哪会不求人?求人算什么,那些快下岗的,那些在找饭碗的,如果能有人求的话,谁都理解他们求人,没人会看低他们。我们贺家这一路过来,什么时候不求人啊?
给他这么一说,我也有点难过。我想他一定觉得我太娇了。
21
星期四下午面试。单位的头头脑脑坐在会议室里,我们在外面等,一个个进去,抽题,回答。
我们在外面等的时候,每个人的神色各异。林伟新脸上带着冷傲,他说,陪绑陪绑。杨青坐在一边抽烟。我看着他的安静,就在心里安慰自己:别紧张,紧张就是自作多情,谁不知道这是走过场,我走到这一步,已经可以了。
因为是竞聘“首席业务调研员“,所以我觉得题目可能会比较专业,这两天我翻了不少经济方面的专业书,作了准备。但,当我走进会议室抽出那张答辩纸时,我还是吃了一惊,我面对那些头们把题目念出来:
办公室坐着两位同事,他们都在忙着,一会儿之后,其中一位去上了厕所,他回来后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机没了。如果你是领导,丢手机的那位悄悄来向你反映这事,你怎么处理?
这题出乎我的想象,妈的,原来考破案,我一下子脑子短路,因为这题有点像脑筋急转弯,又有点像这两年公务员考试,比如,南极为什么没有熊,鳄鱼看到食物为什么流泪。
我听见虞大头在悄悄对钟处说,嘿,这题是我出的。
我想,他一定觉得处理这种事的技法很重要。
于是我说,如果直接把另一位找来,开门见山说这事,他跳起来不承认自己拿,这后面的事就有些难办,两位同事日后的关系紧张不说,如果一方死不认,那你怎么办,报警吧,事搞大了,丢了单位的脸,不处理吧,这事传来传去的,如果那位真的没拿,对他也不公平,而且他会想另一位怎么把自己想得这么坏,这如何是好?
虞大头说,你问我,我还问你呢。
他们都笑了。
我说,把另一位找来,不说他拿没拿,而说单位里最近许多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没人,东西要放好。看他的脸色有没有紧张,再判断……
钟处笑起来说,你还会相面啊。
我吱唔起来,说,要不,开门见山坦诚地告诉嫌疑人,说自己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希望他大气一点,协助自己处理这事,如果拿了,就以影响最小的方式还回去,这事他知你知我知,这事就到此为止;如果没拿,那么我们该一起把那位丢手机的同事找来,坦然地谈谈这事,这比在心里揣磨半天好,那样以后就没事,问题就解决了。
我看见好几个人在笑,陈方明也冲着我笑。我不知他们的意思。虞大头说:噢,你说的是用真诚感化他们,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说,要不把嫌疑人找来,把这道题改头换面一下,说自己看了一道题,是办公室丢钱包的事,出给他,查他,让他回答。
他们笑得我心里没底了。我说,手机现在也不贵啊,这事搞得那么烦,我干脆买一个送给那位丢手机的,当作当月业绩奖品,当众奖励给他,那位拿手机的看到这情境或许会触动,怀疑你们知道是谁拿的,只是为了维持场面上的和谐办公室,不来和他计较这事,他就收敛一点;而那位失手机的,一方面觉得领导站在自己一边,一方面觉得损失补回来了,再一方面觉得自己对另一位有德道优越感,他就不吵了,少给领导添乱了,办公室就和谐了。
说着,我自己也笑了,我嘟哝:给他买一只吧,买一只,算了。
20
我从会议室出来,程珊珊许惠琴问我气氛怎么那么好。她们说:你讲了些什么?
女人为什么焦虑(1)
1
经过星期四的这场答辩之后,党委会将于近期再作一次讨论,确定最后人选。
2
我原以为下周会有结果,但没想到突然延期了。
因为星期五省厅领导来我们单位考查的时候,李厅长派给了虞大头两个赴欧洲调研的名额。李厅长说,老虞啊,你们要出去看看,开开眼界,取取经,这次是随省经济考察团一起去,下周出发,时间蛮紧的。
虞大头连连感谢,说,那太好了,胡士忠、杨心泉都还没出去过呢,这真是个好机会。
结果,由于两位副局长临时出国,讨论“首席调研员”人选的党委会就只有延期,据说得等他们从欧洲回来以后再开。
我听到这消息,松了一口气,好像一个不安的小学生,下意识地希望成绩晚点公布,想把侥幸拖得长一点。
当然,我心里也明白:妈的,这事越拖这中间想玩猫腻的就会越多,看着好了,我们这10个人中间,这下不知有多少人要加紧活动了?
3
我和程珊珊、许惠琴坐在同一间大办公室里。
由于这次竞聘我们同时入围,所以最近这阵我们之间有些微妙,在场面上我们仨谁都没提起竞聘的事,倒是办公室里的“老滑头”严明等几个时不时调侃她们两个女的。他们已经把她们叫作“程首席”、“许首席”了。
程珊珊娇啧着,用手指点着严明说,去去去,等俺们真上了请你喝醋。
看着他们叽叽呱呱的,我想,这两个女人,她或者她,会是我的对手吗?
我猜她们心里可能也在这么揣测着我。但,一般来说,她们惦记得最多的肯定不是我,而是她们彼此,谁让她们都是女的,她们较劲的对象永远是对方,她们顾不上我。
作为这两个女人的旁观者,这些天,我瞅着她俩觉得逗趣:
两位“辣嫂”程珊珊和许惠琴,平时就常为一点点破事暗地里比个不停(比老公比孩子比奖金),这两天她俩攀比的意志更渗透了每个细节,比如,趁这会儿许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