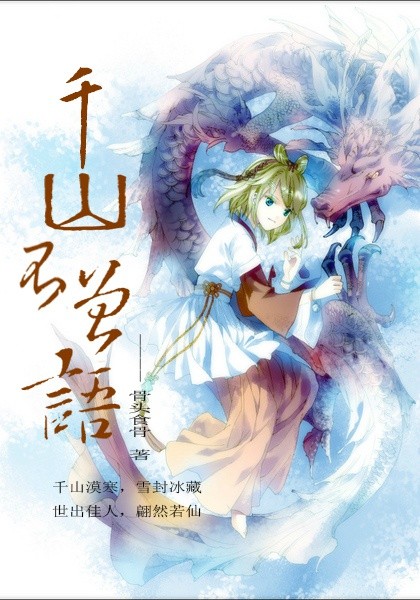万水千山走遍-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烈日下的所谓金字塔,已被小贩、游览车,大声播放的流行音乐和大呼小叫的
各国游客完全污染光了。
日神庙六十四公尺高的石阶上,有若电影院散场般的人群,并肩在登高。手中
提著他们的小型录音机,放著美国音乐。
我没有去爬,只是远远的坐著观望。米夏的红衬衫,在高高石阶的人群里依旧
鲜明。
那日的参观没有什么心得。好似游客涌去的地方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当米夏努力在登日神庙顶时,我借了一辆小贩的脚踏车,向著古代不知为何称为“
死亡大道”的宽大街道的废墟上慢慢的骑去。
本想在夜间 去一趟神庙废墟的,终因交通的问题,结果没有再回去。
我还是不羞耻的觉得城镇的人脸比神庙更引人。
至于马雅文化和废墟,计划中是留到宏都拉斯的“哥庞”才去看一看了。
吃抹布
第一次在街头看见路边的小摊子上在烘手掌大的玉米汉饼时,我非常喜欢,知
道那是墨西哥人的主食“搭哥”(TACO),急于尝尝它们。
卖东西的妇人在我张开的掌心中拍一下给了一张饼,然后在饼上放了些什么东
西混著的一滩馅,我将它们半卷起来,吃掉了,有酱汁滴滴嗒嗒的从手腕边流下来
。
“搭哥”的种类很多,外面那个饼等于是一张小型的春卷皮,淡土黄色的,它
们永远不变。
里面的馅放在一只只大锅里,煮来煮去,有的是肉,有的是香肠,有的看不清
楚,有的猜不出来。要换口味,便换里面的东西。
在城内,除非是游客区,那儿可以吃中国菜、意大利面食,还有丹麦甜点蛋饼
之外,也可以吃“搭哥”。
可是当我们坐车离城去小村落时,除了“搭哥”之外,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
。
在城外几百里的小镇上,当我吃了今生第几十个“搭哥”之后,那个味道和形
式,实在已像是一块抹布━━土黄色的抹布,抹过了残余食物的饭桌,然后半卷起
来,汤汤水水的用手抓著,将它们吞下去。
一个“搭哥”大约合几角到一元五美金,看地区和内容,当然吃一个胃口是倒
了,而肚子是不可能饱的。这已是不错了,比较起城内高级饭店的食物,大约是十
倍到十五倍价格的差距。虽然我们的经费充足,仍是坚持入境问俗,一路“搭哥”
到底。这对助手米夏便是叫苦连天,每吃必嚷∶“又是一块小抹布!”
在墨西哥的最后一日,我怕米夏太泄气,同意一起去吃一顿中国饭,不肯去豪
华的中国饭店,挑了一家冷清街角的,先点了两只春卷━━结果上来的那个所谓“
春天的卷子”的东西,竟然怎么看,怎么咬,都只是两只炸过了的“搭哥”。
吃在一般的墨西哥是贫乏而没有文化的。
它的好处是不必筷子与刀叉,用手便可解决一顿生计,倒也方便简单。至于卫
不卫生就不能多去想它了。
货物大同
在城内的游客区里,看见美丽而价格并不便宜的墨西哥人的“大氅”,那种西
班牙文叫做“蹦裘”(PONCHO)的衣物。
事实上它们只是一块厚料子,中间开一个洞套进颈子里,便是御寒的好东西了
。
我过去有过两三个“蹦裘”,都因朋友喜欢而送掉了。这次虽然看见了市场上
有极美丽的,总因在游客出没的地区,不甘心付高价去买它。
下决心坐长途车去城外的一个小镇,在理由上对米夏说的是请他下乡去拍照。
事实上我有自己的秘密,此行的目的对我,根本是去乡下找漂亮、便宜,而又绝对
乡土的“蹦裘”来穿。
坐公路车颠几百里去买衣服也只有最笨的人━━而且是女人,会做的事情,不
巧我就有这份决心和明白。
到了一个地图上也快找不到的城镇,看到了又是所谓景色如画的贫穷和脏乱。
我转来转去找市场━━资料书中所说的当地人的市集,找到了,怪大的一个广场。
他们在卖什么?在卖热水瓶、镜子、假皮的皮夹、搪瓷的锅、碗、盆、杯,完全尼
龙的衣服,塑胶拖鞋、原子笔、口红、指甲油、耳环、手镯、项链━━。
我到处问人家∶“你们不卖PONCGO?怎么不卖PON-CHO?”
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举起他们手中彩色的尼龙衣服向我叫喊∶“这个时髦?
这个漂亮?怎么,不要吗?”
水上花园
那是过去的一大片沼泽,而今部分已成了城镇,另外一小部分弯弯曲曲的水道
,仍然保存著,成了水上的花园。
本来也是要自己去划船的。星期天的旧货市场出来后计划去搭长途公车。我的
朋友约根算准我必然会在星期日早晨的市集里与当地人厮混。他去了,也果然找到
了我与米夏。
于是,我们没有转来转去在公车上颠,坐了一辆大轿车,不太开心的去履行一
场游客必做的节目。
一条条彩色缤纷的木船内放著一排排椅子,比碧潭的大船又要大了些。墨西哥
人真是太阳的儿女,他们用色的浓艳,连水中的倒影都要凝固了。
参考书上说是二十五块美金租一条船,划完两小时的水道。船家看见是大轿车
来的外国人,偏说是五十美金,我因不肯接受约根的任何招待,坚持报社付钱,就
因如此,自己跑去与人争价格,已经降到四十块美金了,当然可以再减。讲价也是
一种艺术,可惜我高尚的朋友十分窘迫,不愿再磨,浪费了报社的钱,上了一条花
船。
三个人坐在船中木头似的沉默无聊,我忍不住跑去船尾跟船家说话,这一搭上
交情,他手中撑的那只好长的篙跑到我手上来了。
用尽了气力撑长篙,花船在窄窄的水道里跟别的船乱撞,这时我的心情也好转
了,一路认真撑下去。
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水道,只因也有音乐船、卖鲜花、毡子和食物和小船一路
挤著,它也活泼起来。
虽是游客的节目,只因长篙在自己的手中,身分转变成了船家,那份生涯之感
便是很不同了。
那一天,我的朋友约根没有法子吃他昂贵的餐馆,被迫用手抓著碎肉和生菜往
玉米饼里卷著做“搭哥”吃。买了一大堆船边的小食。当然,船夫也是请了一同分
食的。
水上花园的节目,一直到我们回码头,我将粗绳索丢上岸,给船在铁环上扎好
一个漂亮俐落的水手结,才叫结束。自己动手参与的事情,即便是处理一条小船吧
,也是快乐得很的。奇怪的是同去的两位男士连试撑的兴趣都没有。
你们求什么
又是一个星期天,也是墨西哥的最后一日了。
我跟米夏说,今天是主日,我要去教堂。
来了墨西哥不去“爪达路沛大教堂”是很可惜的事情。据说一五三一年的时候
,圣母在那个地方显现三次,而今它已是一个一共建有新旧七座天主教堂的地方了
。
“爪达路沛的圣母”是天主教友必然知道的一位。我因心中挂念著所爱的亲友
,很喜欢去那儿静坐祷告一会儿,求神保佑我离远了的家人平安。
我们坐地下往城东北的方向去,出了车站,便跟著人群走了。汹汹涛涛的人群
啊,全都走向圣母。
新建大教堂是一座现代的巨大的建筑,里面因为太宽,神父用扩音机在做弥撒
。
外面的广场又是大得如同可以踢足球。广场外,一群男人戴著长羽毛,光著上
身,在跳他们古代祭大神的舞蹈。鼓声重沉沉的混著天主教扩音机的念经声,十分
奇异的一种文化的交杂。
外籍游客没有了,本地籍的人,不只是城内的,坐著不同型状的大巴士也来此
地祈求他们的天主。
在广场及几个教堂内走了一圈,只因周遭太吵太乱,静不下心坐下来祷告。那
场祭什么玉米神的舞蹈,鼓得人心神不宁,而人群,花花绿绿的人群,挤满了每一
个角落。
我走进神父用扩音机在讲话的新教堂里去。
看见一对乡下夫妇,两人的身边放著一个土土的网篮,想必是远路来的,因为
篮内卷著衣服。
这两个人木像一般的跑在几乎已经挤不进门的教堂外面,背著我,面向著里面
的圣母,直直的安静的跪著,动也不动,十几分钟过去了,我绕了一大圈又回来,
他们的姿势一如当初。
米夏偷偷上去拍这两人的背影,我看得突然眼泪盈眶。
那做丈夫的手,一直搭在他太太的肩上。做太太的那个,另一只手绕著先生的
腰。两个人,在圣母面前亦是永恒的夫妻。
一低头,擦掉了眼泪。
但愿圣母你还我失去的那一半,叫我们终生跪在你的面前,直到化成一双石像
,也是幸福的吧!
我独自走开去了,想去广场透透气,走不离人群,而眼睛一再的模糊起来。
那边石阶上,在许多行路的人里面,一个中年男人用膝盖爬行著慢慢移过来,
他的两只手高拉著裤管,每爬几步,脸上抽筋似的扭动著,我再低头去看他,他的
膝差哪里有一片完整的皮膏━━那儿是两只血球,他自己爬破的一瘫生肉,牛肉碎
饼似的两团。
虽然明知这是祈求圣母的一种方式,我还是吓了一大跳,哽住了,想跑开去,
可是完全不能动弹,只是定定的看住那个男人。
在那男人身后十几步的地方,爬著看上去是他的家人,全家人的膝盖都已磨烂
了。
一个白发的老娘在爬,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在爬,十几岁的妹妹在爬,一
个更小的妹妹已经忍痛不堪了,吊在哥哥的手臂里,可是她不站起来。
这一家人里面显然少了一个人,少了那个男子的妻子,老婆婆的女儿,一群孩
子的母亲━━。
她在哪里?是不是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是不是正在死去?而她的家人,在没
有另一条路可以救她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来祈求上天的奇迹?
看著这一个小队伍,看著这一群衣衫褴褛向圣母爬去的可怜人,看著他们的血
迹沾过的石头广场,我的眼泪迸了出来,终于跑了几步,用袖子压住了眼睛。
受到了极大的惊骇,坐在一个石阶上,硬不在声。
那些人扭曲的脸,血肉模糊的膝盖,受苦的心灵,祈求的方式,再再的使我愤
怒。
愚蠢的人啊!你们在求什么?
苍天?圣母马利亚,下来啊!看看这些可怜的人吧!他们在向你献活祭,向你
要求一个奇迹,而这奇迹,对于肉做的心并不过分,可是你,你在哪里?圣母啊,
你看见了什么?
黄昏了,教堂的大钟一起大声的敲打起来,广场上,那一小撮人,还在慢慢的
爬著。
我,仰望著彩霞满天的穹苍,而苍天不语。
这是一九八一年的墨西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宏都拉斯纪行
青鸟不到的地方
由墨西哥飞到宏都拉斯的航程不过短短两小时,我们已在宏国首都“得古西加
尔巴”(Telgucigalpa)的机场降落了。
下飞机便看见扛枪的军人,虽说不是生平第一次经验,可是仍然改不掉害怕制
服的毛病。对我看制服象征一种隐藏的权力,是个人所无能为力的。
排队查验护照时,一个军人与我默默的对峙著,凝神的瞪著彼此,结果我先笑
了,他这也笑了起来,踱上来谈了几句话,心表便放松了。
那是一个寂寞的海关,稀稀落落的旅客等著检查。
碰到一个美国人,是由此去边境,为萨尔瓦多涌进来的难民去工作的。
当这人问起我此行的目的时,我说吟是来做一次旅行,写些所闻所见而已。在
这样的人面前,总觉得自己活得有些自私。
我们是被锁在一扇玻璃门内的,查完一个,守门的军人查过验关条,就开门放
人。
当米夏与我被放出来时,蜂涌上来讨生意的人包围了我们。
有的要换美金,有的来抢箱子提,有的叫我们上计程车,更有人抱住脚要擦鞋
。
生活的艰难和挣扎,初入宏国的国门便看了个清楚。
我请米夏与行李在一起坐著,自己跑去换钱,同时找“旅客服务中心”,请他
们替我打电话给一家已在书上参考到的旅馆。
宏都拉斯的首府只有四五家世界连锁性的大旅馆,那儿设备自然豪华而周全。
可是本地人的客栈也是可以住的,当然,如果付的价格只是十元美金一个房间的话
,也不能期待有私人浴室和热水了。
此地的钱币叫做“连比拉”(Lempira)。这本是过去一个印地安人的
大酋长,十六世纪时在一场赴西班牙人的和谈中被杀。而今他的名字天天被宏都拉
斯人提起无数次━━成了钱币。
两个连比拉是一块美金。
计程车向我要了十二个连比拉由机场进城,我去找小巴士,可是那种车掌吊在
门外的巴士只能坐十二个人,已经客满了。于是我又回去跟计程司机讲价,讲到六
个大酋长,我们便上车了。
公元一五○三年,当哥伦布在宏都拉斯北部海岸登陆时,发现那儿水深,因此
给这片土地叫做“宏都拉斯”在西班牙语中,便是“深”的意思。
并不喜欢用落后或者先进这些字句来形容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毕竟各样的民族
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与先天不平等的立国条件。
虽然那么说,一路坐车,六公里的行程,所见的宏都拉斯仍是寂寞而哀愁的。
便是这座在印地安语中称为“银立”的三十万人的首都,看上去也是贫穷。
这是中美洲第二大面积的国家,十一万两千八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百分之四
十五被群山所吞噬,人口一直到如今还只三百万左右。
宏都拉斯出产蔗糖、咖啡、香蕉、棉花和一点金矿、锡矿,据说牛肉也开始出
口了。
我到的旅馆除了一张床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家具。走道上放著一只方桌子,
我将它搬了进房,做为日后写字地方。
米夏说兵床上有跳蚤,我去看了一看,毡子的确不够清洁,可是没有看见什么
虫,大半是他心理作用。当然,旅馆初看上去是有些骇人。
街上的餐馆昂贵得不合理,想到此地国民收入的比率,这样的价格又怎么生活
下去?
走在路上,沿途都是讨钱的人。
初来宏都拉斯的第一夜,喝了浴室中的自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