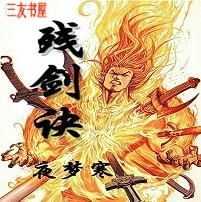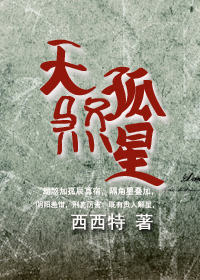残剑孤星-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痛过甚,怎会许久不肯回答你一句话,你就别再逼她了吧!”
韦松感激的点点头,道:“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原谅我,我太辜负她了—一”
马森培不解其中原故,一时接不上口,“子母剑”马梦真含笑上前,道:“世上没有解不开的误会,时间是最好的解释,譬如我们对韦少侠原也误会极深,但自从见了韦少侠石上留字,才觉得从前的事,竟是大错而特错!”
韦松惶惑地道;“在下急于追赶师妹,误抢渡舟,致将船只踏沉,还没向贤兄妹谢罪致歉呢!”
马森培爽朗笑道;“韦兄何须客套,实在说起来,咱们倒应该感谢韦兄,假如没有这场误会,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岂能解脱迷魂毒性,我和妹妹,更无缘结识慧心姑娘了。”
马梦真也道:“韦少侠赠药留宇,慧心姑娘正在林中,并未离开,那时凌鹏还想趁机对我们痛下毒手,全亏慧心姑娘识破,力创那狗贼,我和了尘大师乙真道长才没伤在他手中,后来我哥哥寻来了,大伙儿述及前情,了尘大师和乙真道长感激无比,千嘱万托,要我们向韦少侠代谢解毒大恩!”
韦松又喜又悲,问道:“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内毒都已经化解了么?”
马梦真道:“都清醒过来了,两位掌门人如梦初醒,对以前种种,愧愤不已,现在已经分返本派,决心号召江湖,同御万毒教。”
韦松长嘘一声,如释重负道:“但能如此,在下纵被冤屈,也就心安了。”
于是,又向马氏兄妹谢了援救大恩,再看视“袖手鬼医”艾长青,却见他呆呆坐在棺木上,正黯然垂泪。
这时候,茅屋已烧得只剩一堆灰烬,韦松苦口劝慰艾长青,又在屋前掘土营坟,帮他将棺木下葬,立碑为记,艾长青落棺入土,感怀前情,忍不住放声大哭。
掩葬刚毕,马森培悄悄将韦松引到一旁,低声问道:“此地之事了后,韦兄意欲何往?”
韦松道:“北天山神手前辈,为了桐柏山惨变,独自往湘北万毒教总坛寻仇,他老人家功力全失,这一去何异羊入虎口,在下之意,须得立即去追赶他老人家。”
马森培想了想,道:“艾老前辈和令师妹,韦兄又作何安排?”
韦松道:“自然是劝他们一同到洞庭湖去,贤兄妹如无他事,也请同往—一”
马森培尴尬笑道:“在下和舍妹极愿附骡同行,只是慧心姑娘,她——”
韦松道:“她怎么了?”
马森培叹道;“方才舍妹私下劝她,但她只是一味摇头垂泪,看情形,好像,好像—
一”
韦松道:“洞庭之约,是徐姑姑吩咐,她纵或恨我,难道连师父也不认了,我再去问问她。”
马森培忽然将他拦住,道:“在下猜她并不是不愿前往洞庭,而是与韦兄之间,尚有误会未能解开,假如你再去问她,她一定也是不肯回答的。”
韦松为难道:“这么说,该怎么办呢?”
马森培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如由在下陪她同往洞庭,途中得便,可以设法开导她,韦兄可与艾老前辈径赴湖北,届时咱们在洞庭会面,其中误会,也许就化解了。”
韦松道:“如有贤兄妹陪伴着她,在下就大大放心了,只是艾老前辈忧伤过度,途中也许不便兼程疾赶,在下又急于去追神手前辈,时间又无法耽延—一”
马森培忙道;“这个容易,我可以留下舍妹和韦兄同行,途中代为照料艾老前辈,不致妨碍韦兄行动。”
韦松怔了一怔,只好点了点头。
他的原意,是想请艾长青和马氏兄妹一起,不妨缓缓前行,自己则急追神手头陀,阻止他独往洞庭,不想马森培代他安排,竟是要马梦真陪伴艾长青和自己,他则偕同慧心,另作一起,前往洞庭。
这个安排,他不能说不妥当,但略一回味,却发现马森培之所以要这样做,表面理由正大堂皇,实则极可能另有私心。
私心是什么?当然是慧心师妹那绝世容颜和令人倾慕的精湛武技。
韦松乃是心性坦然的人,这一刹那,虽然略有领悟,但他暗想马森培兄妹号称“荆山双秀”,出身正道武林名门,有他伴着慧心,最起码不会让慧心与歹徒合污,如像这一次桐柏山事件,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至于马森培是不是会跟慧心两情相治,那是男女间发乎自然的事,他不想反对,也不能反对。
马森培却有心病,见他沉思不语,脸上立时臊红不胜,自解地低声道:“韦兄如认为不妥,有何意见,咱们不妨再作商议—一”
韦松坦然笑道:“不!马兄的意见已经很好了,咱们就这样办,劳动贤兄妹分别奔波,盛情心感,慧心师妹性子比较刚强,如有开罪失仪之处,马兄务必要多耽待,在下先行谢过。”
马森培红着脸道:“哪里话!哪里话!在下能与令师妹结伴同行,真是三生有幸。”
两人计议要当,重回草坪,艾长青仍在坟前饮泣,慧心还是坐在那块大石上,仰面凝望不语,马梦真却在坟边低声劝慰艾长青。
韦松举步走到石前,深深一揖,诚挚地说道;“愚兄亏负师妹太多,自觉无以自解,师妹责我恨我,愚兄一应承受,但洞庭之行,是徐姑姑亲自瞩令愚兄转致,还盼师妹能屈从一次,使愚兄于姑姑面前,有所覆命。”
慧心举目望天,默默不答,神情十分冷漠。
韦松道:“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果承师妹盛情,只恨图报无门,空自负疚难释,此后师妹要多多珍重。”
慧心才然不语,但两行清泪,却顺着粉颊,缓缓滴落襟前。
马森培上前低声道:“慧心姑娘,咱们动身吧!”
慧心缓缓站起身子,移动脚步,向山下行去,走了数丈,忽然顿了一顿,飞快地回过头来,满眶热泪扫了韦松一眼,慢慢一跌莲足,掠身疾奔而去。
马森培急急向韦松一拱手,道:“洞庭之滨,敬候韦兄侠驾。”说罢,匆匆跟着向山下飞掠追去。
韦松怅然目送他们一先一后,转过林于,内心有如刀割,长叹一声,垂头坐在那块大石上。
石上余温犹存,他低头感伤,忽然发现泥地上划着许多零乱的字迹。
那是慧心不久之前,用三刃剑尖无心刻划在泥土上,沿着大石,遍地都是“韦松,韦松,韦松—一”两字,重覆交二,层层累累,何止千百遍。
他痴痴凝视着那些零乱不堪的字迹,眼中一阵模糊,泪水已扑蔌蔌滚落了下来—一☆☆☆☆☆
夕阳衔山的时候,洞庭湖畔,金波万顷,景色如画。
熏风吹低了芦苇,闪出一角茅屋、小径、竹篱、木扉。红泥堆砌的院墙,寂寞的沐浴在落日余晖之中。
院子里没有人影,烟筒上不见炊烟,门扉半掩,随着微风一开一闪,发出低沉的“依呀”之声。
这时,小径上渐渐出现一条歪歪倒倒的人影,一身灰布大袍,满头如雪乱发,简跚向茅屋而来。
他走几步,又举起一只巨大的珠红葫芦,“咕喀”向喉咙里灌下一大口酒,抹抹嘴唇,又抹抹额头上汗珠。
从魁梧身形和衣着看来,这是一位昂藏的带发头陀,红润的面庞,被酒气和蒸蒸泽气笼罩着,又显见经过长途跋涉,才到了这临湖的幽静茅屋。
当他转过芦苇的刹那,目光一瞬这雅致幽静的茅屋,神色立现欣喜激动,几乎泽忘了途中劳累疲惫,一面加快步子,一面扬着酒葫芦,高声叫道:“东方老头儿在家么?酒肉和尚来啦!”
一连叫了几声,茅屋中毫无回应,而他蹦跚的身子,也渐渐行到竹篱外,微感一诧,喃喃说道:“奇怪,难道他们爹儿三个都打渔去了?”
他伸手推开篱门,踉跄跨了进去,才到屋边,一阵风过,那木扉“蓬”地一声敞了开去。
头陀皱皱眉头,道:“莺儿这丫头,越来越不仔细,人不在家,连门也忘了掩—一”
边说边迈进茅屋,一个不留神,迎面绊着一张竹椅,险些摔倒,踉跄前冲几步,竟触了一头蛛网,摸了满手灰尘。
头陀心头一阵凉,酒意消散了大半,游目回顾,才见这茅屋中满是积尘珠丝,桌椅散乱,竟是个久无人居的空屋。
他一颗心顿时向下疾沉,奔进卧室,又冲进厨房,急急乱奔一匝,最后颓然跌坐在一张积满尘土的椅上,惊骇莫名道:“这—一这是—一怎么一回事—一”
搬家了?东方老儿去世了?出了什么变故?
这一刹那间.许多可能发生的事故,都在他脑子里飞一一旋转,他猜测不透,性急起来,仰头又大大灌了两口酒。
酒人愁肠,烦闷更盛,昏昏沉沉中,他仿佛听到有一阵纷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遥遥向茅屋而来。
他恍然忖道:啊!对了,他们一定出了远门,现在才回来,否则,这茅屋地处荒僻,谁会找到这儿来?我和尚就坐在这儿,吓他们一跳。
片刻间,脚步声已到竹篱外,只听一个粗重的嗓音说道:“寻了几天,竟是这地方最好,不但偏僻,又临大湖,进退之路极佳,决不会被万毒教知觉,唯一缺点,是地方小了一些,不知道金师爷中意不中意?”
另一个声音接口道:“师爷嘱咐只求临近君山,地方隐密,虽然小一些,好在只是暂住,略加整修,也就够住了。”
粗重嗓音道:“既然如此,你们先看看屋里有没有人居住,我这就去接金师爷来亲自决定。”
另一个笑道:“有人没人,还不是一样,咱们看中了,少不得叫他立刻搬出去。”
粗重嗓音道:“余老二,不准蛮于,要是原有屋主,只许多给他们银两,叫他们暂时迁让几日,万万不可惹出事故来泄露了消息。”
几人商议一阵,其中两人疾步离去,留下的两个,跨进竹屋,高声道:“喂!屋里有人吗?”
头陀一直在屋中倾听,早辨出这些人口音全是北方人氏,心中一动,应声道:“进来!”
木门“呀”然而开,从院中大步进来两个锦衣大汉,其中一个豹头虎目,身形粗壮,另一个较显瘦削,却目光奕奕有神,两人都悬着满嵌珠宝的长刀,神态威猛。
那粗壮的一个探进头来。一见正中厅上,坐着个白发头陀,含笑拱手道:“敢问大师父,这茅屋主人在家么?”
头陀冷笑道: ”我和尚便是主人,二位有何贵干?”
两名锦衣人又望一眼,都有些诧讶之色,瘦削的一个笑道:“咱们倒未料到,这茅屋原来是间和尚庙,敢情有些霉气。”
粗壮的一个睁着眼,四下一望,哼道:“胡说,屋中一无神位,二无经卷钟拨,分明只是普通房屋,这和尚只怕也是霸占人家住宅的人物。”
头陀笑道:“说得是,但是我和尚既然先来一步,就是此屋主人,三位晚到片刻,只好屈居客位了。”
粗壮大汉怒目道:“不管你是不是此屋主人,咱们给你银子,赶快离开,这屋子咱们另有用处。”
头陀道:“两位的意思,是要收买和尚这栋茅屋?”
粗壮大汉接口道;“不错,就算你早来一步,撞上好买卖,白赚一笔银子。”
头陀微笑道:“两位打算出多少银子呢?”
大汉道:“你想卖多少?”
头陀伸出三只手指,粗壮大汉道:“三十两?”
头陀笑道:“三万两。”
粗壮大汉大吼一声,“呛”地拔出长刀,叱道:“反了,反了!咱们跟你客气,你倒当了福气,勒索巨款,这还了得!”
瘦削汉子一闪身挡住他,沉声道:“余老二,不耍乱来,依我看,这位大师父必有来历,别替庄主随意开罪了朋友。”
正说着,屋外一阵衣袂飘风之声,划过院落,疾掠而至,一个沙哑的声音接口道:“余腾,瞎了眼的东西,连威震武林的北天神手头陀都认不出来,还不赶快跪下向老前辈陪礼谢罪。”
随着人声,一个浑身儒衫,手提旱烟袋的瘦老头儿,伟然出现在门前。
头陀抬目一见那儒衫老人,早扬声哈哈大笑起来,道:“金老夫子,什么时候做了康一苇的师爷啦?”
儒衫老人抱拳当胸,含笑道:“大和尚,咱们是老交情,多年不见,您老一向可好?”
头陀笑道:“托福!托福!毕竟是老朋友,这笔买卖定然做成了,冲着您金豪金师爷一句话,减一万两,算二万两成交如何?”
金师爷苦笑道:“几十年来,您这玩世不恭的脾气还没改。”
回头叱道:“余腾,还不快些跪下叩头!〃
那粗壮大汉慌忙跪倒,“咚咚”在地上叩了两个响头,道:“小的有眼无珠,冒犯佛驾,大师父赦罪。”
神手头陀感慨地挥挥手,道:“快起来,别难为了人家孩子,金老夫子,坐下咱们详谈。”
金师爷叱退余腾等人,自寻一把椅子,在神手头陀对面坐下,目不转瞬注视他半晌,脸上渐渐流露出惊诧之色。
神手头陀笑问道:“敢情是看我和尚不如从前了?”
金师爷惊问道:“大师父目光霉而不明,难道已炼就‘返本还虚’的佛门至高境界?”
神手头陀神色微微一动,敞声笑道:“蹈光隐晦的境界,岂是那样容易炼就的,倒是金老夫子何时跟康一苇攀上交情,屈身做了他那‘傲啸山庄’的管事师爷?”
金师爷叹了一口气,道:“唉!说来真是一言难尽。”说着,掀起身上儒衫,登时一片灿烂光华,从襟底激射而出。
金师爷道:“大师父知道这东西来历么?”
神手头陀脸上微微掠过一丝惊诧之色,但随即隐去,淡淡一笑,道;“看样子,敢情是名闻天下的“七彩宝衣’?”
金师爷笑道:“不愧是老江湖,果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此宝原产大越国,是酋长哈都木护身之物,不但能御刀剑,水浸火烧,内家重掌,都难损伤分毫。哈都木仗此宝农,纵横大越国八十一寨,所向无敌,卒能统一各部,登上盟主宝座——”
神手头陀插口笑道:“你别跟和尚说故事,这东西怎会到你手上?单说这一段就行了。”
金师爷又是一声长叹,道:“关于金某得此至宝的经过,也不是三言两语说仅明白的,大师父总该记得二十年前,“宇内一君”康一苇和花月娘之间一段旧恨—一”
神手头陀蓦地一震,脱口道:“你说康一苇废掉那老淫妇武功的事?”
金师爷点点头,道:“正是,武林传言,但知花月娘迷恋康一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