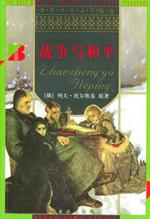日德青岛战争-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交通也不顺溜,强子领着人到处砸黄包车,那些拉洋车的黄包车夫都不敢出车了。殖民当局也忙了起来,他们不知哪来的风雨,巡捕房为了维持秩序,在街上见了不顺眼的人就抓。
冬生的人有预谋,他们又在暗处巡捕非但没抓到他们,反而把阿毛的人抓了不少。那些黄包车夫不敢出车,没了生活来源,便出来伺机枪劫。
一日傍晚,芳芳和丽娜从德华大学放学回家,她俩出来的较晚,路上人已稀少,几个车夫开始只是抢钱,另一个车夫见她俩相貌不错,便起了歹心,想把她俩绑架到窑子铺去卖了。于是便和其余的车夫把她俩绑了,堵上嘴推搡着从前海滩来到了圣功女子中学门前。事情凑巧阿毛在川江茶馆喝茶,被疤根盯上,带着几个兄弟去滋事斗殴。没想到阿毛的手下也不是吃素的,疤根几个人没得着便宜吃了亏。冬生得到消息便急匆匆地往那里赶。芳芳和丽娜不停地挣扎,那遮眼布在冬生迎面走来时掉了下来。芳芳见是冬生便打坠不走,两眼直直地盯着冬生,嗓子眼里拼命地呜呜着,冬生知道是绑架人的,停下脚步看仔细。那几个洋车夫做贼心虚,见冬生停下来,其中一个也不说话从腰里拔出刀子就朝冬生刺来。冬生哪里吃这一套,把身子往右侧一闪顺手牵羊把刀子夺了过来,借着惯性顺势在他的背上砸了一刀把,这家伙哎呦一声趴在了地上,其余的见状撒腿跑得无影无踪了。冬生给她俩解开了绳索,顾不得跟她俩说话,又急匆匆地往川江茶馆奔去。
芳芳和丽娜吓得不轻,两人都病了。芳芳发了两天烧说了两天的糊话,二把头见芳芳病的这样,坐卧不安,一直陪在女儿身边,。直到芳芳醒来才知道事情的原由,心想:我没置冬生死地,是老天有眼;放他一马,他却把我的女儿救了;阿弥陀佛,看起来人得多做好事,还真灵验了一报还一报的那句话。
芳芳躲过这一劫后,人突然变得稳重了,身上的孩子气消失了,动态语言成熟起来。这可真是女大十八变,变的教你难以相信。也可能情感触及了她的灵魂。
开始二把头以为女儿是大病初愈,或是大脑受了惊吓,过些日子就恢复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女儿显得更加恬静,更加稳重。除了在学校里学习,在家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房间里独思。
一天女佣拾掇芳芳的房间,二把头见女儿这些天像是在考试,书本都散放在写字桌上。他来到书桌前告诉女佣,书桌上的书本不要动,以勉弄乱了,女儿回来寻找答题费时间。他无形中随手拿起一本笔记本见是女儿写的日记,女儿记日记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女儿不会记日记。女孩子除了上学就是学习,不接触什么事情,哪来的那么多的心得与体会?只不过记些;今天天气晴朗,同学踩了她一脚,没上火,没发脾气之类的字语。他本不想翻看;无意中还是翻了翻,突然一段文字映入他的眼帘:
我知道你的名字——冬生,你不认得我,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没有感
觉只有印象,可这印象总是在我的脑海里徘徊挥之不去。我试尝着把你忘掉,
可总也忘不掉。阿毛的人来绑架我,老天爷派你来救我这是咱俩的缘分!我
不认为事情的凑巧或是节骨眼;我认定了这是缘分。回家后我的神不守舍精
神恍惚,可我不想唱也不想哭,我的心里只有你。《新约全书》上的那个“爱”
字天主送给了我,我把它偷偷地送给你吧——我爱你!生哥。
二把头看完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女儿的情感原来这般的随他,随她的妈妈。
他想起了他的从前。二把头年轻做瘪三混不下去时,常受到那时还不是他妻子,也不是他未婚妻的恩惠。他坐班房时,都是还不是他未婚妻的妻子,催着她的老爹花钱去班房里把他赎出来。其实妻子当时和他家并没有什么亲友裙带关系,只不过是街坊邻居。二把头也算是个有心的人,为了报答,索性夜间在妻子家的门外过夜,为的是给妻子一家守夜。后来他发迹了,便花重金把妻子娶了过来。其实他并没花钱,当他娶过妻子后,老丈人没过两年就死了,他反而白捡了老婆家的一片宅园。爱情有了财产是小事,遗憾的是老婆命短,生女儿时难产,女儿活了,老婆死了。这给二把头留下了终生的伤痛。凭着他的地位、财气、势力,多少富贵人家拿着自己的千金来给他补缺,都被他婉言了。有人花高价从妓院买来妓女巴结他,被他嗤之以鼻。认识他的人都怀疑他年纪轻轻怎么就拒绝了这人人喜爱的儿女情长?这使接触过他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有的朋友曾经诱惑过他:当太监的年老了都想娶媳妇成亲,你这年轻力壮的怎么就会败下阵来了呢?他只是笑笑,就是不动心。性情在他身上像是养的一只鸟,冷不丁地飞走了,永远的不再回来了,从此永远的没有了。
二把头欠妻子的恩惠到头来又转化成了爱。本想终生报答,没想到妻子不买他的账,永远地走了。这使他遗憾而悲怆,怀中的女儿是他的眼球谁也动不的,除了奶妈喂奶谁也看不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在他身边,简直是比母亲还母亲。女儿的动向时刻牵挂着他的神经;谁都动不得这根神经。
女儿的日记勾起了他对爱妻的温馨回忆,他把对妻子的爱转嫁到了女儿的身上。他知道女儿懂事了,要寻找自己的爱巢了。他更知道那爱的力量,像着了魔一样,九头牛也拉不回。他擦了一把泪才知道自己哭了,自言自语道:“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老了吗?我大概老了?”自己无法测定自己老了的相貌,孩子是测定自己老了的标尺;孩子长大了,父母必定老了。
第六章 荒岛落难 兄妹结义
一日放学后没雇着黄包车,芳芳和丽娜只得走回家。两人各抱着书本,丽娜用胳膊肘拐了芳芳一下,道:“哎!自从那次出事后,我爸爸叮嘱我一定要早回家,不能在外面贪玩,所以咱俩得走得快些!”她见芳芳不回答,停下来放大了声音,道:“哎,我说你在想什么哪?”
芳芳这才注意到丽娜在跟她说话,她似乎有些抱歉地微笑着回答:“噢,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
“真坏,再也不理你了,”她侧脸看着芳芳脸色的变化,见芳芳心不在焉,故意刺激芳芳道:“你是不是又在心里想那个泥腿子乡巴佬?”
芳芳脸上泛起了红晕,微笑着答道:“对呀!我在单想思啊!”
“他真的像你说得那么酷?那么可爱?”
芳芳收住了笑容停下来,道:“你不是故意在逗我吧?那天你真的没看清?”
“那天?”丽娜一时迷茫,霎时那天被绑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她苦笑道:“真假?事情真的会这么巧?既使是真的我当时被吓蒙了,哪里看得清他是谁呀!”
芳芳心想对啊,她对生哥从认识到现在为止,也只不过是隔着门缝看了个大体轮廓,并不真切。救她们那天,算是贴近了,又慌里慌张的顾不上细看。自己心爱的人,自己都没端相仔细,丽娜怎么会认得呢?我这不是在出难题吗?她宽微丽娜道:“我是街上剃头的挑担儿,一头有火,人家那边凉着呢,还不知是咋回事儿?他并不知道我,也不认得我。”
丽娜有些莫名其妙,咋了咋舌道:“你这不是单相思吗?一见钟情?”她说完像是略有所思,放慢拖长了音调又道:“假如真是他,人家救了咱俩,咱俩应该去感谢他才是,或是送点礼品什么的表达一下心意。”
丽娜的这个注意一下子使芳芳的心情敞亮起来,对啊!这是与生哥接触的理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嗳!你怎么不说话?什么时候带我去感谢人家呀?”
“我不知道……”芳芳仿佛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什么不知道呀?咱俩到码头去找他好了!”
芳芳摇摇头道:“他不在码头了,他走了。”
“为了你吗?”
“不,是替工友打抱不平,打伤监工……”
“哦——英雄,行侠仗义,就像救你救我一样,这种人啊人见人爱,我遇到了我也爱!”
芳芳听丽娜表扬赞美生哥,心里美滋滋得开心地笑了,道:“咱俩得想法找到他,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也好了却咱俩的心愿。”
“你说他现在能在哪里呢?”
芳芳知道冬生是刚来青岛港的,混迹于底层人群中。她只是猜想,对丽娜道:“我想他现在大概住在后海沿的贫民院里。”
“那咱俩到哪里去找他。”
“不行,那里太乱,他万一不住在那里呢?”
“哎,我有办法了,后海沿不敢去,咱俩就去他常走的路上等他,总有一天能见到他。”
“只好这样了……”
……
阿毛这些日子有些毷氉,他的无本买卖被冬生这帮子人一闹腾,简直把他气疯了,黑钱收不上来,他手下的那些兄弟被巡捕房抓去没有钱赎,关在巡捕房里德国人硬是不放人。有些兄弟见阿毛敌不过生哥,便偷偷的给疤根、强子当了眼线,有的干脆投了过来。
大把头开的福寿馆,近些日子从大连海运一批大烟膏到青岛港,这事被阿毛的眼线探得后报给了阿毛。阿毛正手头缺钱,都支不开锅了,这消息使他喜出望外,他立即安排了手下的兄弟们谋划越货。
疤根从眼线那里得到消息后,兴奋地对冬生说:“生哥,这可是到嘴的肉,咱们不吃阿毛那小子可就独吞了,他是不会感谢我们的,再说咱们的兄弟越聚越多,吃饭,发饷都成了问题。如果得手截了,咱们半年的经费足够了。到时候兄弟们都扯点布做件衣裳,买顶帽子,换换行头,像模像样地做人。”
“抢东西这事……”他自言自语道。冬生有些犹豫不决。
强子见冬生下不了决心,往前凑了凑,道:“生哥,东西是大把头的,阿毛要去抢,咱知道了不能睁眼让阿毛弄了去。再说大把头开大烟馆,开妓院尽毒害人,在青岛港上他是黑老大,弄得黑钱最多,他比德国人还黑,算是黑到家了。咱们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谁也怎么不着咱们!”
鸦片这买卖,自从林则徐禁烟以来,中国人都知道它是毒品,但出于高额利润,人们私下趋之若鹜,偷运贩卖。开大烟馆的比比皆是,历任官府也曾经下过禁令,由于无能力操办禁止,也只能喊而不禁,这些事情冬生是听人们讲过的。如果今天把这桩买卖做了,良心上也过得去。给大把头一个撞击也算是在替天行道了,也好让他大把头知道我冬生在青岛港上的存在。
那些老码头工友告诉冬生,干这活得有耐性,得到船的靠岸点去蹲守。因为帆船这东西不是火轮,它受风向,潮流的影响,行走时间和路线及不确定,何况从大连到青岛路途遥远。再说运输这些伤天害理的东西老天定是不佑,那船时刻都有被风刮翻的可能。偷运鸦片这活都是在风高夜黑时进行,他们得行踪诡秘,一旦岸上有了异样就不靠岸了,另选别的地点了。
冬生他们犯了难,胶州湾包括前海这么长的海岸线,半夜三更黑咕隆咚地去找一条小帆船,确实太难了。关键是偷运鸦片的及秘密,人家不能等你来劫货。你蹲错了点,到头来是白搭。
疤根把眼线秘密找来,冬生和他谈好了,他把靠岸地点摸准了,等事成后给他二百块光洋作为报酬。
几天后秘信报来,大把头与二把头商定,卸货的地点定在大码头上。在大码头卸货有两个原因:一是正置初旬夜里没有月亮,海潮水位低,大吨位货船靠不了岸,码头没有货船就没有活干,码头上就没有工人。尤其是夜里只要把电闸一拉,码头上漆黑一片,除了黑夜就是海风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处几艘等待大潮进港卸货的货船上的灯,在风中一眨一眨地放出微弱的光亮。二是便于大把头、二把头指挥。万一撒了消息,有人来抢或当局海关来没收,也有运走和藏匿的便利。再一个二把头早已买通了巡捕房,只要一接到信息巡捕出警快。
天黑了,他们十几个人分三路向大码头的岸边摸去。他们听眼线说好,只要看见海中有灯光发出信号,和码头上对信号,就向灯光靠拢。大约半夜时分他们来到了预定的地点,一个工友问冬生,码头上从来都是灯火通明,今夜怎么没灯?疤根抢着说:“这说明接货就在今夜里了,我们不会空等。”
这时在海面不远处有灯光晃动,码头上距他们很远的地方也有人亮灯对信号。冬生很兴奋,他们正欲偷偷靠近,发现在他们前面的货堆中有人潜伏。他们不知这些人是阿毛的还是二把头的?不敢贸然靠近,只是伏在那里等待。
那船像是靠了码头,有了动静。再过一会听到有打斗的声音,冬生便知是阿毛的人在动手抢货了。当他们悄悄靠近货物时两帮人只顾打斗,把货物丢在一边。货物是用大木箱封着的,两人抬着走不方便。强子道:“给他砸了,光拿鸦片走。”话音刚落突然码头上的灯全亮了,随着响起了警笛声,接下来的是人们四下里逃窜。
冬生那十几个人已跑了四五个,还剩下五六个被一个工友叫到了运鸦片的船上。这个工友过去在运输船上打过工,只会摇橹不会使帆,且摇橹的技术也不是太好,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这时巡捕也赶到了码头边上,巡捕在明处,冬生他们的船在暗处,巡捕看不见什么,只朝着海面放了几枪。
冬生他们的船慢慢地向胶州湾的入海口划去,由于他们不识胶州湾的海流,时至涨潮时分,那海水从胶州湾的入海口,冲着那条破船向胶州湾的纵深流去。在急湍的海流中,那条本来就破漏的渔船失去了控制,渔船顺着海流向着急流中的一个小岛冲去。
当小船将靠近岸边时,船底碰在了礁石上,船上的人惊呼起来。那船急速下沉,并没停下,而顺着海流从小岛的侧面流去。这时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喊话,“喂——你们在哪里?”冬生他们听到有人喊,知道自己有救了,迅速从沮丧,惊恐的情绪中回过神来,他们兴奋激动得大声拼命的连续不断地喊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黑暗中,顺着喊声那船靠了过来,几个人慌忙地爬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