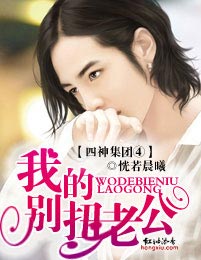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孩子确实长得敦敦实实,只这点她没说白。
她见了我,哭得呜呜的,我当着我岳母,给她敬个礼,说,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们至今相处很好。我为我能遇着她庆幸,从来没后悔过。
龙洪春已确定转业。副师长陈知建告诉我:他的婚事在部队、社会传为美谈,但转业还是受影响,不能进政法部门……
我原想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挂黑牌,敲锣游街。他历来烟酒不沾,从此又抽又喝,在我十岁时他得癌症死了。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叫我用功读书,将来出国留学。我说,成绩不好才留学呐!
我母亲是食品公司的职工。
父亲死后,我们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亲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们,小伙伴们叫我“特务儿”,我课余跟妈妈打猪草,人家骂我们是穷要饭的。我从小看够了一副副可怕的脸,除了家里人,我总是躲着别人,就是对家里人,我也很少说话。
妈妈总是一句话:别死气沉沉的,一个人是高是低,不在别人怎么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节,人家赏月,我在月光下等妈妈下夜班回家。妈妈看见我说:“小烈,你在看月光吗?”我说:“月光是别人家的,我不看。”妈妈抱着我唉声叹气直到我睡着了。
年龄越大,我越悲观。但我学习很努力。秋天,我爱一个人到林子里看书,或荡起小舟,到河心看书。父亲爱打鱼,家里还有条小渔舟。
我的家乡贵州湄潭风光很美,小城在湄江河的环抱中,有小台湾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曾迁到那里,琼瑶也写过湄潭。
河水清澈,落叶随水漂流,我感到我也是一片落叶。
我负伤住院时,文工团一位女演员送我一盘钢琴曲录音带,是外国的,我一听就想起了我悲苦的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大山、荒凉的河滩、落日残照下的原野……
妈妈曾经问我:“你长大干什么?”我说:“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妈妈吓坏了,很伤心地说:“你真没志气,为什么不在这让人看不起的地方作个让人人都看得起的人?”
读初中时,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同学当兵了,都是有门路的人家子弟。他们穿起军装回校告别时好神气呀!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刚想了个开头,我自己脸红了:你算什么?
我也有过一次意外的“走红”。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湄河发大水,一个小女孩落水,我衣服没脱,跳起水里追了很远很远,救起了她。她父母找到学校感谢我,县广播站也表扬我,学校叫我入了团,县委发了优秀共青团员的奖状。
妈妈见了盖大红印的奖状,抱着我哭了,说:“你真争气,可以后不要冒冒失失呀!”
1980年高考,我上了重点分数线,这时父亲的问题刚平反,说是“中右”,属人民内部矛盾。
我想报考军校。“妈妈,我想当军官,当将军!”妈妈说:“别说梦话,军事院校哪会要你?”她认为,爸爸虽然平反了,但在别人眼中我们还是低人一等。我填上了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她说,填了也白填。
结果我真接到了昆明陆院的录取通知,我高兴死了。从接到通知到送我起程,妈妈无数遍说:“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
我认为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的悲伤与冷漠,开始了我无边无涯的锦绣前程。
在军校里我的各科成绩都在全院居前列。我博览群书,立志当一个同时是政治家的将军。
假期,我穿了军装回家。妈妈看着我,总看不够似的,老说:“你真争气!”我说:“这算什么?你看我将来的吧!”
我自那时很狂。分到这个团,第一次见团长时你猜我想什么?“团长,不出十年,你这位置是我的!”
我分到炮排当排长。全排连我才六个人!我是学过营指挥的呀,怎么才给我五个兵!
我的心冷了一下。立刻想到书上一句话:“挫折就是奋起的机遇。”
我注意军人姿态,值班时很负责,口令一发出,全连肃然,战术演习,谁的动作马虎点我立刻纠正。果然营团首长很快注意到我了。
二十天后,我调任一排长,有了三十几个兵。五十天后,我得到团嘉奖,同时宣布调任团侦察排长。
这时,侦察排已在老山前线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因为历来侦察排长都是排长中尖子的尖子。我也很害怕,在学院我就知道,奇 …書∧ 網老山前线的侦察兵和越南特工队是怎么较量的!
我很想和团里说,我不行,我才20岁,在家时,还从没离开过妈妈十里远哩。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这时哪怕在人前皱一下眉头,我就从此被人看扁了!
连队领导和我的几位同学送我上火车。车一开,我悄悄地抹开了眼泪:在我面前本有千万条路,我怎么就单单选择了这一条呢?小火车跳,我的心更跳,好像是去赴杀场!这个侦察排长的任命呀,它不仅可能淹没我的将军梦,也许会把我的命都断送了!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一冬天给人家做香肠那双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节香肠想用茶缸煮给妹妹吃,妈妈说:“别这样,别作这种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对呀!决不能因我的畏怯让妈妈在人前抬不起头!我掏出笔记本,写了两句话:“为了我的妈妈,我要勇往直前!时刻想着,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剌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你妈的X,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逄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我的爱只在心里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天,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