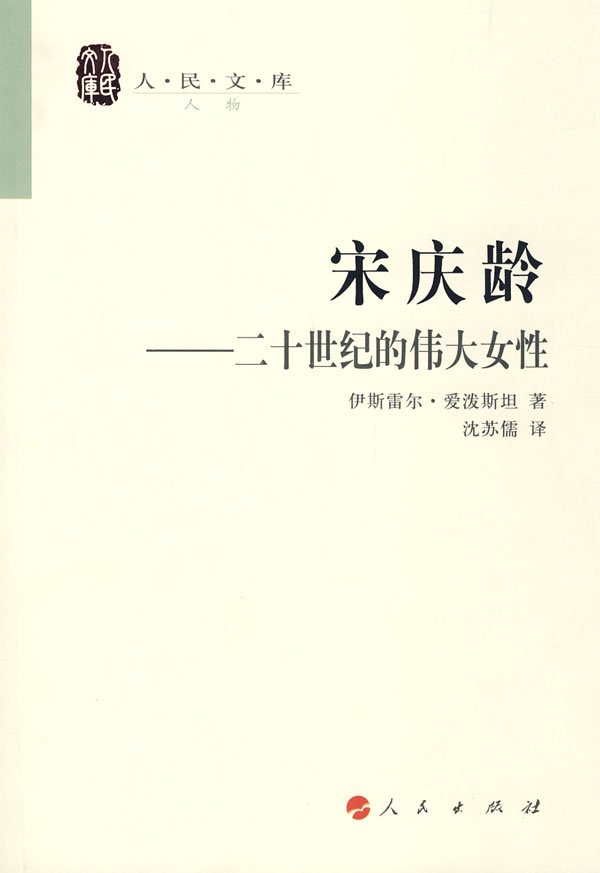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8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看来是故意回避谈别的事情。)
在同一页上,斯诺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错误——很有道理。”①
①《复始之旅》一书是斯诺离开中国多年、处于低潮时期写的,宋庆龄曾指出其中一些事实错误以及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并嘱路易·艾黎转告斯诺。
1970年末斯诺离开中国。1971年7月31日,他写信给路易·艾黎,谈到自从轰动一时的、出乎意料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一事发生之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现在随着更加轰动的美国总统访华的即将实现,主要的美国传播媒介都来向他紧急约稿(尽管它们仍想进行歪曲):“……化了一星期……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稿子,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人期望从尼克松的访问中得到什么》。我原来的标题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编辑中,他们设法做了点手脚,有一处压缩成周恩来谈话而‘毛听着’……在我那句‘中国从未放弃武力收回台湾’的话中,加上‘公开’一词。”他又带点嘲讽意味地接着说,“有一件事……使我大为得意。《生活》杂志在那张老大的《纽约时报》上为我那篇文章……登了整版的广告——也是这张报纸早些时候曾拒绝刊载重要的周总理访问记,深怕上斯诺的赤色宣传的当。现在美国却听不够了。关于乒乓(外交)的报道如此之多。”
在同一封信里,他对自己十年前访华后所写的《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作了自我批评式的评论:“……现在我重读这本老书,常常要惊叫起来……当时我对群众的无知和偏见过于迁就,以致对美国过于宽大了……现在,《纽约时报》也在发现中国是个好地方,但当时——在书评栏里除了抓赤色分子就没有篇幅登别的东西了……
“全世界现在看到毛主席是个伟人,他当然是。但我的任务是使人们看到他不是妖怪而是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在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传中,他的行径使人觉得是有威胁性的。”
斯诺又说,除了一些错误,他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但他不愿对此自吹自擂。“请告诉对我的批评家们……我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愿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纠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保持了一贯的谦虚态度。
但时间不允许了。在他写这封信后不到一年,癌症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1971年:关键的年份'
1971年,《年谱》上没有任何记载,但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在国内,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败仓皇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机毁人亡。这是9月13日的事。到11月,事情的内幕还没有完全公开,宋庆龄在11月11日给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的信上,赞扬他没有急于报道此事:
“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可不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这么说吧,这是一场噩梦——‘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①不管怎么样,勃鲁托斯还是L.P.(林彪英文拼音的缩写),都是他自己的阴谋的牺牲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出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①语出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凯撒》(据朱生豪译本)。勃鲁托斯是刺杀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以后自杀。——译者
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席位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窃踞了二十多年,现在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这反映出中国革命在它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改变了局面,而美国则支持蒋集团直到最后失败。
这样,中国尽管在国内遭到困难(一度有趋于危殆之势),在世界上的地位却不断上升。
宋庆龄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私人通讯中她写道:“(1971)对我们和对全世界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因为中国现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全世界人民从联合国的讲坛上听到了中国的声音。愿1972年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1年12月22日。
正由于形势有所好转,所以她在听到大弟(只比她小1岁)子文去世的消息时,还不至于太难过。宋子文是因为意外事故(在美国一家餐馆用餐时骨头卡住了咽喉)而死的,享年77岁。这位金融家、前国民党要人同她在政治上的争执和歧见大体上和霭龄、美龄差不多,但两人之间的个人情谊要深一些——他有时还支持她的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来是为了重新恢复同中国的接触,或者更明白一点说,是为了承认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二十多年来美国官方一直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结束了。也是在这一年,宋庆龄打破了持续五年的沉默,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月,在尼克松访问前夕,她发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①。文章的论点不是说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说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①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那末,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她接着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
在概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主要是在质量上——之后,她接着说: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必然是和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一军事集团联系起来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国的做法完全……是国际互助。”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文章最后说:“毛主席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
她为这一历史性的全面进展而感到自傲,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相对而言,挫折和困难犹如即将消失的乌云。
因患关节炎和尊麻疹,她没有参加官方对尼克松一行的招待会。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要我参加在尼克松访问期间的所有活动,但我在海外的朋友写信来说,他们在电视上没有见到我,感到失望。”
但她接着说:
“很多美国人去参观了我们在上海住过的房子……察看我丈夫书房里原有的藏书,甚至还有那些照片。”
她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显然是针对国外有人幻想新中国或她本人会改变根本观点):“他们会发现卡尔·马克思仍然好好地在那里。”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2年3月4日。
1972年之后,来华的美国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都有。有她在威斯里安上学时的朋友(来的常常是这些朋友的继承人或后代),有各个革命时期同她在政治上有关系的人,也有直到最近还对中国不友好、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新的发现者”的人。对这各种类型的人,她都欢迎,只有一种人她觉得难以接受——那些了解政治实情,而“在麦卡锡时代跑得同兔子一样快——毫无骨气”的人,“但现在他们却成了社会栋梁,所以我们必须欢迎!”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理查德·杨。
'痛悼挚友'
2月15日,一位同这些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此极度悲痛。
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①,她写东西通常是很快的,但在听到斯诺噩耗后她为了写给斯诺遗孀的唁电,通宵未睡。唁电写道:
①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们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对埃德加·斯诺的记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长青。”①
①《人民日报》,1972年2月1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34页。
洛易斯·惠勒·斯诺在她纪念斯诺的书中谈到这个唁电时说:“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①
①同注29。
在反动势力面前勇敢无畏——这是宋庆龄认为最优良的品质之一。三十六年前,主要通过她的推荐和帮助,斯诺访问了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一篇纪念斯诺的专文中,她称赞斯诺“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根据地的中国革命。”①
①《纪念埃德加·斯诺》,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6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斯诺最后著作之一的书名是:《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她满怀热情地回顾她同斯诺相识四十多年来的历程。斯诺作为一位年轻的记者,“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首先来到上海,然后又深入到中国的红色区域。他在这次采访中所写成的书(《西行漫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是最恰当的铭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他“曾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也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或称‘工合’运动的一位热情的发起人。”本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他备受政治迫害。“然而,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虽然当时埃德加·斯诺并不知道,正是他于1970年12月同毛主席所进行的长谈——当时中国人民的领袖谈到为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对话,导致了中美两国人民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来的大门的打开,而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毕生所致力的事业的一个目标……
“……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
在当时的一封信①里,宋庆龄写到斯诺的遗孀洛易斯遵照斯诺的遗嘱正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带到中国,并且称赞洛易斯“她多么能为别人着想!”——因为中国政府提出愿意负担她的路费,她就宁愿坐火车而不乘飞机以节约开支。护送斯诺骨灰来华的还有他的挚友、1936年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马海德是随同一个由毛泽东派去治疗斯诺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的。在北京,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前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美丽的未名湖畔,年轻时的斯诺曾在燕大教新闻学并鼓励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
斯诺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宋庆龄又悼念了另一位同她的过去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人,她的朋友、同志和经常的通信对象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撞车事故中不幸丧生,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马克斯,也受了重伤,但幸存下来。在一篇悼念文章①中,宋庆龄回顾了在战前危机四伏的上海,同格兰尼奇夫妇出版《中国呼声》的情形,以及在分离三十多年以后最近在北京重逢的景象——在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夏访华把道路开辟之后、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前,中国方面邀请第一批美国老朋友访华,格兰尼奇夫妇也在其中。
①《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9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他们重访中国的愿望终于在去年秋天实现了——这时格雷斯已74岁,马克斯(他们的朋友都叫他‘曼尼’)已75岁了!……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而且在他们退休以后还特别地把自己对中国的知识和了解转达给……青年人。
“……1971年10月5日周总理接见所有在京的美国人时,格雷斯·格兰尼奇就坐在总理的旁边。这次离开中国时,格雷斯和曼尼都满怀豪情,情绪高昂……
“很难以相信充满活力的格雷斯会这么突然逝世……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中国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这样认为。当她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成功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她为这些成就感到光荣和自豪。她对于能够给美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介绍最近在中国的经历,感到如愿以偿……”
影响更为广泛的是1972年9月何香凝的去世,享寿95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中国革命者中是同宋庆龄相识最早、相知最深的。这位伟大、英勇的中国女性亲身参加了孙中山同宋庆龄的婚礼、在孙中山弥留时同宋庆龄一起守护在他身边,她是国民党中极少几位能始终忠于孙中山思想的元老之一。几十年来,她同宋庆龄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