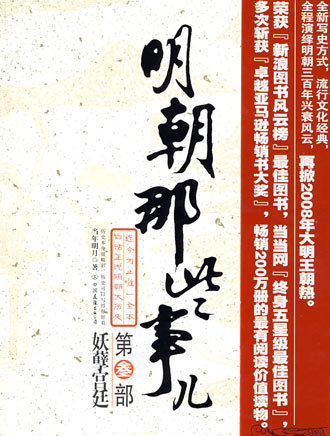阴间那些事儿-第2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花清羽……已经走了?!
我来不及多想,抱起才从怡宝和史文生,让两个村民小孩拽住我的衣角,我们快速往山洞外面跑去,白猫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跑的没了影。
这时洞窟开始大面积坍塌,石头大块大块落下来,砸在地上,生出一片烟尘,后面的洞口已经逐渐被落石堵上。我停下脚步焦急地说:“那只猫怎么办?”
话音刚落,碎石里突然伸出一只手,紧接着露出一张血肉模糊的脸,正是花图郎,他居然还没死!
黑暗中,他咬牙切齿,目光紧紧盯着我们,像是要把我们所有人的形象都深深印在脑子里。
第四十四章站在猫的角度看猫
花图郎盯着我,我吓呆了,他的眼神特别可怕,像狼一样。虽然此时此刻他全身都埋在石头里。无法动一下,但透出的那股恶毒和狠辣,还是让人胆寒心惊。
这时突然一块大石头从上面落下来。正砸在花图郎的脸上,瞬间把他埋在下面。
黑暗中,我冷汗直冒。只见石头堆松动。像是有什么要爬出来。我以为花图郎还没死,正要转身跑,就看到那只白猫从土里钻出来。嘴里还叼着东西。尽找向弟。
它一个纵跃跳过来,把嘴递向我,我摸出打火机照过去,它嘴里叼着的居然是迦楼罗鸟花花。
花花昏迷不醒,蔫头搭脑的,我轻轻伸出手把它接在掌心里。
史文生道:“这只鸟和你我都有缘法,不应该死在这里,我们赶紧走吧。”
我们几个人在洞里仓惶出逃,我不认路,幸亏史文生和白猫在黑暗中引路,我们跌跌撞撞,终于从洞里跑出来。此时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外面是接近黄昏的余晖,洞口风摇草动。远处嘉措母亲湖波光斑斓,像是恍然做了一场大梦。
洞口不远处站满了村民,他们一个个焦急万分,打着手电或是火把,谁也不敢进来。看到我们从洞里出来,众人惊呆了片刻。马上一片欢呼。
人群里出来几个孩子的家长,把失而复得的小孩抱在怀里,哇哇哭。
史文生在我的怀里,白猫依偎在我的脚边,花花塞在我的衣兜里,感觉自己就像个走江湖的马戏团。蔡玉成他们从人群里走出来,巴梭看我的样子目瞪口呆,他们刚要说什么,忽然“轰隆”一声巨响,所有人都震翻在地。村民们一个个高声叫着,蔡玉成更是扯着嗓子喊:“不好啦,地震啦!”
我趴在地上转头看,后面的山洞在剧烈的响声中,洞口已被一大堆乱石淹没。周围山动地摇,大地居然龟裂出几条裂纹,山石崩落,我眼睁睁看着远处的一座山体像突然融化了似的瘫软下来,霎时间,泥流、石块裹着乱七八糟的植物杂草,瀑布一般从山崖上倾斜而下。
村民们互相扶持,有人架起我,所有人跌跌撞撞一起往外跑,大地剧烈震动,每个人都像喝醉酒一样。周围是山崩石落,巨响震震,那场面就像打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十来分钟,坍塌震动停止,周围满目疮痍,所有的山体几乎都变了样子,尤其我们逃生的洞窟早已埋在乱石深处看不见了,放眼望去,面目全非。
众人停下来,面面相觑,所有人都愣了好几分钟,才回过神。蔡玉成脸色惨白,磕磕巴巴地说:“地震了吧?”
只见所有的村民都一起跪下来,面向嘉措母亲湖,开始跪拜磕头。村长跪在最前面,用当地土语不停地说着什么,那模样像是祭天,也像是诵经。
巴梭站在后面对我们说:“这是村里的一种仪式,他们认为这么大的波动,是母亲湖里的神发怒了。”
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刚才斗法,花图郎毕其功于一役,激荡了整个山洞,才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蔡玉成忽然一拍大腿:“坏了,老花还在洞里,他抱着史文生和我们走散了……”话还没说完,他才注意到我怀里抱着的史文生。他愣愣看着我:“老花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此时也很难细讲,苦笑一声:“他走了。”
“上哪了?”蔡玉成还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知道。”我说。花清羽这一世过完了,他走了,下一世是什么,在哪里,都是未知数。他就像上帝扔出的骰子,会随机落在这个地球的任何空间任何纬度里。不过万幸的是,他还留有这一世的记忆,他能记住我们这些人,能记住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能记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事。
不知下一次见到他,会是什么时候,会是什么情境。或许,我们再也没有相见的可能。
我们跟随村民回到村子,在村长家的房间里大家秉烛夜谈,所有人围坐一起,我把山洞里发生的一切讲述一遍。
听得过程中大家一言不发,全都听愣了,就跟听传说故事一样。
等我讲完,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冯良下意识用摄像机对准我脚边的那只白猫,疑惑地说:“你说这只猫会说话?”
蔡玉成道:“罗稻,你讲的这段经历太神乎其神了,这里毕竟关系到花清羽的生死安危,不是说我们不相信,只要你能让这只猫开口说句话,我们就更确凿了。”
我摸摸白猫的脑袋:“说两句吧。”
白猫伸着懒腰,喵喵叫了两声,突然开口说话:“玉成,你是为了你爷爷来的,我能帮到他。”
蔡玉成估计也就是随口这么一说,他根本不相信猫能说话。白猫这么一开口,他眼珠子瞪得比牛眼都圆,“啊”一声惊叫,整个人摔在地上,冯良把他扶起来,眼神还发直。
白猫喵喵叫着,说道:“罗稻说得都是真的,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劫数。”
冯良用摄像机拼命拍着,向导加多也瞪圆了眼,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动物能说人话。
巴梭还算镇定,双手合十,道:“白猫啊白猫,你就是上师吗?”
白猫学着人的模样坐起来,伸着小爪子说:“看看你的画。”
巴梭曾经临摹过上师修行洞窟砖墙上的莲花图,他把纸展开,上面是三朵诡异的莲花,一左一右分别是一大一小的人形,而中间那朵莲花造型奇诡。他颤抖着把纸拿起来,和眼前的白猫对比,我们都看出来,中间那朵莲花正是一只猫蹲坐在地上的剪影。
巴梭跪在地上,毕恭毕敬对着白猫磕头,再抬起时已泪流满面:“上师……”一句未了,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白猫叹口气:“巴梭,你是我生前最看重的心子,你最有慧根,可是现在竟然还如此不悟!还要修行啊。我即是宗磕玛珠,又不是宗磕玛珠,他已经死了,我就是现在的白猫。他的智慧记忆修为虽然有部分继承在我这里,但我们毕竟是两个物种,性存而身异。巴梭,你太眷恋上师这个名头这个相了。”
巴梭含泪磕头:“上师,没想到你会转世成一只猫。”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些功课要做。”白猫说:“很长时间以来因为科学带来的实证主义,世人都太看重数据和资料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进行量化。这些看法不是错,而是不够周延,我们要用一种更为开阔的生活标准或人生价值去看待这个世界。不是说转世成了猫,成了狗,成了猪马牛,就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业障。经由不同的体验才能领悟到不同的任务和功课。巴梭,真正的大境界是不要执着人的观念,要站在风的角度看风,站在云的角度看云,站在猫的角度看猫,这才是你要修的方向。”
巴梭重重磕了一个头。
蔡玉成磕磕巴巴地问:“那你和史文生,还有罗稻,你们仨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白猫说:“我生前转世曾有宏愿,分出身、口、意三幻法身,身为罗稻,口为我,意为史文生。罗稻为金刚身,我为传经口,史文生是智慧意。”
“可你们的年龄不一样啊,罗稻都快三十了,史文生才五岁,而你多大呢。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分出去的?”冯良提出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白猫笑了:“转世既然能跨越物种,必然也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转世轮回六道中,六道众生皆平等。六道的存在就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传统观念。你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转世这套系统用的是人类目前所不能理解的方式和机制进行的。”
“那才从怡宝又是什么人?”我问。
白猫说:“这个孩子与我与山寺有很深的缘法,我不可说破,你们要带他回寺里,自会有老喇嘛给出答案。”
我苦笑:“我完全没感觉到你与史文生和我之间有什么关系。”
“何必强求关系?”白猫笑:“我们三法身凑在一起已经是莫大的缘法了,完全出乎我生前的预料。我本想是分散身、口、意,永不相见的。”
这时,史文生走过来,抱住白猫,拍着它的小脑袋说:“就你多嘴,不愧是传经口。”
白猫喵喵叫,不说话了,开始舔爪子。
史文生看着我们说:“我有一事相求。”
第四十五章颠簸回寺
我们问他有什么要求。
“白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希望你们能和这家人商量。”史文生说。
讲完所有经历,众人跟我打趣,说我是上师转世什么的。我苦笑。对他们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没有上师的觉悟,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好在哪。该累一样累,该感冒一样感冒。
巴梭和这家人商量,要把带着才从怡宝回寺里。我瞅个机会问史文生:“我们是同一个人吗?”
史文生笑:“不是,你放心吧,你还是你自己。我也是史文生。不是上师宗磕玛珠,他已经死了。转世成谁就是谁,你不是别人的附庸,也不是顶着别人的灵魂,你就是你自己。”
这句话消散了我的心理阴影。我是上师的转世,这个听起来挺牛逼,但细细一想,会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我没有了,成为了别人,这里有一个自我认定的坍塌。我忽然有些明白,科学幻想上的克隆人战争,他们为什么要反抗人类,因为骨子里失去了自我认定,“我”消失了,根本就没有“我”,居然是别人复制出来的。这样的心理机制。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人立足于天地的根本,连“我”都没有了,你还活什么大劲。
我又问史文生:“在洞窟里,我看到金身喇嘛本来有能力制服花图郎,可为什么要放纵他用刀杀了花清羽?”
史文生半晌沉默。然后道:“人生而有因果,前世的因,后世的果。花清羽能舍身为上师挡刀,甘愿受死,看似一劫,实则一果。你不必追究了。天行道,不要用人的道德价值观来评断。”
他看看我:“罗稻,你资质平庸,徒有金刚身,是凶是福,现在还说不明白。希望你不要仗持这个能力,为非作歹便好。”
我听得都笑,就我这熊样还为非作歹呢。
经过协商,这家人决定让才从怡宝跟随我们回寺,同时他的父母也会跟着一起去。
我们在这里耽误了太长的时间,第二天一大早出发,村长非常热情,在村里找来了几头骡子,我们一人骑着一头。所有的村民都出来送我们。他们唱着当地的土歌,为我们奉上碰头礼。才从怡宝和他妈妈骑着一头骡子,小孩躲在妈妈的怀里,眼睛一眨一眨着,我怎么看他怎么别扭。
我们一行人从村里出来,骑着骡子,晃晃悠悠向着遥远的山寺进发。
这段旅程,说起来也有些伤感,回去的队伍里少了花清羽。我有种人生就像是一列旅途中的火车的感觉,我们在某一站上车,在车上认识了一些人,他们中有的人陪伴我们走到终点,更多的人是在半路下了车,从此不再相见。
空气很好,我抬起头看着蓝色天空,远处白雪皑皑的山脉。
花花已经恢复了神智,还很娇弱,这些天一直躲在我的衣兜里不出来,偶尔飞出来盘旋一圈又缩了回去,可能一直在养伤吧。这种神鸟,不能用普通的鸟类行为来定义,我从来没见过它进过食。
回来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很不寻常的事情。嘉措湖延绵的村庄,很多地方发生了地震,不少村子房屋坍塌,有不少大城市来的救助队正在村子里紧急救助,搭建了很多的临时救生棚,有序的组织村民发放救生物品。
我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那天从洞窟里跑出来的情景,地动山摇,山体崩塌,湖水倒流。难道这一切都是上师和花图郎斗法的结果?引起的地震,一直延绵到了这里。
我们在其中一个村子驻足,向当地人打听,这才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洞窟坍塌的时间惊人的吻合。我心中无比惊骇,斗法居然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后果。
每到一处受灾的地方,史文生就要队伍停下来,他带着白猫和巴梭,一起到村子里的祈福。一个大人一个孩子还有一只猫,形成了奇怪的队伍,他们安慰受灾的村民,为他们祈祷。尼泊尔是个有信仰的国家,老百姓们虽然遭遇到了这样的天灾,但心中有了信仰,便能很快地振作起来。
在路上我们见到了很多喇嘛,他们自愿加入救助站,成为志愿者。有的帮助工作人员来做震后工作,有的进入灾民家里用宗教方式进行心理疏导。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很多藏传佛教的祈天仪式,香火滚滚,天空湛蓝,整个地域都散发着浓浓的气息。
走了将近两天,我们终于回到山寺,此时回来,发现气氛大不相同。
山路的两侧,竟然站满了喇嘛和信徒,他们看到我们的骡队回来,谁都没有冒然上前,而是一片欢呼,挥动手臂上的哈达表示敬意,不停地向我们招手。
“他们知道上师的转世灵童回来了。”巴梭说。
不少游客和信徒拿着手机和摄像机对我们进行拍摄。此时队伍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史文生一个才从怡宝,这些人也搞不明白哪个才是,但他们知道,上师的灵童就在其中。
这时,有个颤巍巍的尼泊尔老人,拄着拐棍看我们的骡队过来,竟然放下拐棍,跪在地上,双手把白色的哈达举过头顶。他这个举动极具感染力,像是一片波浪,所有夹道的信徒们,一个接一个的跪下,全都双手把哈达捧到头顶。
这个场景,我这辈子都没看过,感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动。这一刻,我眼泪“哗”的夺眶而出,想止都止不住。
向导多加反应很快,他从骡子上跳下来,牵着自己的骡子默默走进人群,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配受到信徒们如此的大礼,他承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