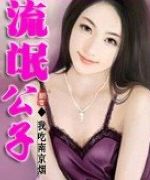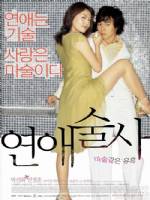小河静静流-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是在外边开会呵,学“理论”呵,取“革命”经呵,自我介绍吹嘘呵,……马不停蹄。要见到他不比见一个县官容易。
其实,即使找到了朱洪又怎么样呢?有其父才有其子。朱阿二夫妇若不是仗着他的权势,哪里敢这样放肆!
吵杂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上,方涛一家人吃过晚饭,早早关上门,以求得暂时的清净。
但门外很快响起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震耳。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谁呀?”方涛问。
“是我,代理队长。”声音颇为威严。
是朱阿二。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公事。”
方涛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朱阿二走进屋里,皮笑肉不笑地向方涛点了点头,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什么事?快说吧。”方涛说。
朱阿二看了看正在灶前洗碗的柳霞,说:
“今天我代表公社上级来,是为柳霞代课工资的事。”
“我的工资?”柳霞惊讶地回过头来说,“学校里不是已经发给我了吗?一月三十元。”
朱阿二泠泠一笑,说:
“一月三十元,想得倒美。拿着不觉得扎手?”
“你这话什么意思?”方涛问。
“什么意思?大有意思!”朱阿二清了清喉咙,说,“你俩都是知识分子,最近一定学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吧。学是为了用!为了坚决限止资产阶级法权,生产队作出规定:本队社员到学校代课所得工资,一律收回作为生产队收入。生产队给代课的人另记工分。柳霞是妇女,按生产队标准一天记八分工,去除星期天,一月二十六天,计二十个整工另八分。生产队分红每个工三角,柳霞可得六元二角四分。已经多领走的,限定三天内交回;不能交回的,生产队划入私人借款,至时另收利息。”
朱阿二说得飞快,但字字清楚,计算也颇为精确,显然是一篇经过充分准备的檄文。
柳霞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得“啪”地一声,她手里的洗碗布掉倒了地上。方涛的母亲正在里屋哄孩子睡觉,也闻言吃惊地跑了出来。
“你们这种做法有法律根据吗?”方涛问。
“根据?”朱阿二泠泠一笑,“限止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根据。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也不只是我们生产队的做法,全公社都一样!”
“那……”方涛的母亲呐呐地问,“那你家那位病哥哥的工资呢?”
“他是正式教员,病假不超过期限工资当然照发,生产队管不着。再说你儿子的工资,我们现在不是也没有扣吗?”
朱阿二说完,再不容方涛家人分辩,站起身,拔脚就走。
柳霞腿一软,跌坐到旁边的一只小桌椅上。桌椅“嗄吱”一声向后倾去,方涛慌忙走过去,把小桌椅和柳霞一块扶住。
“涛哥—;—;”柳霞无力地倒在方涛的身上,“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拿走了钱,还给一顶资产阶级帽子。我拿的代课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天哪!我是资产阶级?”
方涛什么也没有说。他能说什么呢?在朱阿二夫妻一类人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阶级的时候,柳霞被指为资产阶级受到盘剥,又有什么奇怪呢?方涛也很清楚,柳霞是聪明人,他懂得的,柳霞一定也懂得。
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柳霞翻起方涛的上衣襟,里面,正是她送给方涛的那件蓝色毛衣。柳霞紧紧抓着毛衣,手指颤抖着,眼睛里,泪水象雨珠沿着两颊“涮涮涮”往下掉……。
方涛家七拼八凑筹措了一笔钱,将合墙的另一半用高价从朱洪家买了下来,日子才算稍稍安生了一些。
但破屋越来越不经风雨了。晚上,西北风“哗哗”嘶叫着从砖瓦缝里往屋里钻,寒冷剌骨。海亮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未久就冻病了。起先高烧近四十度,随后又低烧不退,脸瘦得似乎只存下了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母亲也是三天两头感冒,脸色腊黄。柳霞忙忙碌碌,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候,人变得又黑又瘦,眼稍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皱纹。
方涛清醒起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特别是海亮的状况,最让方涛虑心忡忡。按说,孩子已经不算小了,他的教育也该提上日程。虽然倔强的孩子这两年很用功,看了不少小人书,认了不少字,但与城里的同龄孩子比起来,毕竟差了一截子。而且,方涛一走,柳霞和母亲两人一个没有时间照管他,一个没有精力照管他,任孩子拖着病弱的身子屋里屋外乱闯,也实在叫人放心不下。
方涛思来想去,感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北京时把海亮带走。
他讲了自己的打算。柳霞和母亲虽然舍不得孩子离开,但也不表示反对。孩子听说后更是欢天喜地,天天晚上缠着方涛打听北京的样子,又大又圆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分外活泼、精神。
但方涛却很快又动摇起来。愈近回京日期,动摇就愈厉害:一个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孩子,如何生存呢?就算有同事的接济,方涛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又如何带孩子呢?再说,他有带孩子的能力、经验和耐心吗?想起同屋郑叶妻子和孩子在北京时的狼狈处景,方涛的心就寒了。
方涛的犹豫未久就在神色和言行中表露了出来。
柳霞第一个摸到了方涛的心事。起先,她只是悄悄地叹息,几天后,终于主动开口说:
“算了,这次别带孩子去了。你是有工作的人,勉强带了去,也很难应乎。”
她停了停,补充说:
“再说,你从未带过孩子,毛手毛脚的,我也不放心。”
母亲也说:
“让孩子留在家里吧。我年岁是大了些,但也不是老得什么都不能干了。再说,孩子也懂些事了,在家有时也能帮着做点事呢。”
母亲说的是实话。海亮虽然小,但扫地、喂鸡喂鸭,都能帮着干。特别是喂鸡鸭,他还真有些着迷。他听妈妈说爹爹在北京很难吃到蛋,一心要把家里的鸡鸭喂好,说要让爹爹回来吃大鸡蛋、大鸭蛋。他的办法也真不少,草丛里挖蚯蚓呀,河边用竹篮子捞小鱼呀,把鸡鸭一只只养得肥肥的。方涛这次回来吃的蛋,主要就是海亮的劳动成果呢。每天,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鸭棚里找蛋。他总是一手抓着一个又大又白的鸭蛋,欢腾着给方涛看。
就这样,在离家的前一天,方涛决定还是把海亮留在家里。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次和海亮的离别。
整整一个上午,孩子总跟随着方涛进进出出,看方涛收拾东西、整理行装。他不说话,但目光愈来愈显得迷惘。他肯定在想:爹爹怎么尽顾自己啊?怎么不给亮亮洗洗脸,戴上小鸭舌帽,换件新衣服,穿上妈妈一星期前给做的小布鞋啊?其实,前一天方涛已经告诉过他这次不带他走了。但他不相信,总是笑嘻嘻地说:“爹爹说过带我去的,爹爹一定会带我去的。”但现在,他似乎已隐隐约约感觉到,爹爹这回真的不带他走了。
终于,吃过午饭,奶奶开口跟他说:
“亮亮,爹爹要上北京了,跟爹爹说声再会吧。”
“不,”孩子却执拗地说,“我要跟爹爹上北京去。”
方涛摇摇头,表示不能带他去。
孩子坚持着,眼泪汪汪,也不敢哭,只是拉着方涛的行李带,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愿望。
但是,方涛终究没有答应孩子。
柳霞也在一旁劝孩子:
“听话,亮亮。爹爹有工作,不好带你去。”
奶奶也劝他:
“这次别去了。以后,和奶奶妈妈一块跟爹爹去北京,更快活。”
方涛也说:
“明年,我带你去北京。”
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明年,方涛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这句话却起了作用,海亮终于一点点放开了抓行李带的手。
“好孩子,听话。别缠爹爹了,嗯?”奶奶顺势说。
海亮想了半天,低低地回答了一声“噢”,乖乖地转过身,向门外走去。
这时,方涛多么希望母亲能跟孩子说一声,象以往几次那样说一声:“亮亮,等会再出去玩吧,先送爹爹一阵。”
但她没有说,这一回竟没有说。
方涛也没有叫住他,不知为什么,连“再会”也没有跟孩子说一声。
孩子出门了,走远了,突然,方涛心头一沉,感到怅然若失……
第六章
方涛回到单位,惊悉许师傅已经去世。一星期前,许师傅不知是劳累过度还是心情过于冲动,心脏病突发不起。多好的一位老人,竟如此迅速地结束了一生,终未能合家团聚。
填补许师傅床位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新分配来的食堂炊事员,所里一个职工的儿子。他在北京已有女朋友,正等着找到房子结婚。方涛他们的宿舍,实际上也是他的觊觎目标之一。所以,小伙子虽说也是单身,与方涛他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宿舍里的气氛明显地比过去沉闷了。
郑叶的乡村女教师身体仍未复原,经常给郑叶写来一些催人泪下的长信,使得郑叶寝食不安。小陈现在一封信也没有。他白天黑夜都泡在外头,宿舍只是他不得已才回来合眼的地方。
方涛的爱人柳霞也不象过去那样冷静了,一封封信详细地叙述着家里的困难:小屋越来越不结实了,稍刮点风就摇晃。母亲感冒不断,心口老感发慌,走几步路都要喘气。柳霞自己腰疼、头晕。海亮还是低烧不退,查不清原因,柳霞也没有时间、精力和钱带他去城里的医院检查,只能从公社医务站拿点退烧药对付着。
一切都叫人挂心呵。
? 知道家里这个样子,方涛吃不下睡不好,健康情况也大不如从前了。
他总是感到精神恍惚,担心着家里可能会出事。他盼望着柳霞能经常给他来信,但又害怕她的每一封来信。每当他拆阅柳霞来信的时候,他的手总是微微颤抖,嘴里一遍遍祈愿着“万事顺利”。
七月,柳霞来了一封长信。她告诉方涛:海亮还是有低烧,但孩子也不顾身体,天天到后河洗衣石板上捞小虾小鱼喂鸡鸭,叨念着让爹爹回来吃大鲜蛋,带他上北京。母亲神志似已有些麻木,常常呆呆地坐着象木头人,管不了孩子。柳霞心力交瘁,仍强撑着天天下地。“涛哥,这日子可怎么过呵?”长信的结尾出现了这样无力的叹息。
方涛无法回答,他没有给柳霞写回信。
这以后,方涛差不多一个半月没有接到家里来信。
“柳霞,你生我的气了吗?”方涛在心里嘀咕着。
但突然,九月初,方涛接到一封字迹陌生的家乡来信。他急忙拆开,一慌,把信纸也撕破了。拼好信纸,上面只有一行字:
“方涛,望速返回。”
信的落款是柳妈。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方涛的心头。是和朱阿二家又闹纠纷了吗?是房屋倒塌了吗?是妈妈病倒了吗?是柳霞身体拖垮了吗?是海亮终天查出什么大病了吗?方涛心神不宁,眼皮跳动不止,设想着家里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乃至不幸。
天哪!他怎么能够想到,他又怎么能够相信,这不幸竟远远超出了他所有的设想:
海亮去世了,他心爱的亮亮溺水去世了!
当方涛回到家里,他的天真、活泼⒖砂的孩子,已经化为灰烬,危可地安息在房间小桌上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子里。……
八月二十九日,一个初秋的下午,四点来钟。方涛的母亲象往常一样,淘米、切菜,准备做晚饭。海亮见奶奶忙得不可开交,独个儿在门口玩了阵,又去后河洗衣石板上捞鱼虾去了。孩子就这么走了。母亲糊里糊涂以为他还在门口。她把米下了锅,点起火,坐在灶边望着火苗呆呆出神。突然,外面响起一位过路木匠的惊叫声:“谁家孩子落水了!”方涛的母亲一听,发疯似地奔出去。木匠和闻声赶来的人把落水的孩子—;—;海亮从河中救起。孩子已经昏迷,河水已经呛坏了他的肺脏,他口流血沫,再已没有醒来。……
海亮究竟是怎么落水的?据当时在离河不远干活的人说,出事前曾有一只汽油船驶过。河小船重,一定是河水涌上了石板,将体弱有病的孩子卷入了河中。汽油船“哒哒哒”响着驶走了,却留下孩子在河水中挣扎。……
方涛不忍心去弄清楚这些细节。他甚至不敢打听那几天母亲和柳霞的境况。她们曾多少回哭昏过去,又多少回在昏迷中哭醒,又有谁能够记得清楚?当他回家的时候,她俩的眼泪已经哭干,那两双简直难以分辨的干枯的、青黑色的眼珠深陷着,仿佛已失去了生命。
就是柳妈也哭肿了眼睛。她破例在方涛家住了一个多星期。
柳妈没有给方涛发电报。她说,城里车辆多,怕方涛精神上过于紧张出事。她也不希望方涛立即返回,不想让方涛看到母亲和爱人哭天怆地的凄惨情景。方涛因此也未能与海亮的遗体告别。这一点,柳妈提起来虽感到负疚,但并不懊恢。她对方涛说:“我不能让你一下子受那么多剌激。你是一家人的主心骨,你再出了事,这一家子怎么过?”
多亏柳妈和几位热心乡亲的帮助,在她们的全心劝慰和护理下,柳霞和方涛的母亲已初步经受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残酷命运的打击。当方涛回家,她俩都已从床上爬起来。柳霞已重新扛起锄头下地。她说:“和村里人一块劳动,心情要好受一些。”方涛母亲的情况要差一些。她是悲痛和自责交加,在精神的重负下整天佝偻着身子,颤颤巍巍,随时都象要摔倒。
海亮遇难三星期,按当地习俗,谓“三七”,是死者的一个重要祭日。
方涛的母亲早早就起来了。她没有话,一句话也没有。她只是来来回回忙碌着,显得分外干练、利索。吃过早饭,她就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叠专买的银灰色锡箔,折了满满一簸箕“元宝”。她一个人烧了饭,炒了鸡蛋,煮了小汤圆,又用方涛两天前从小镇上买回的粉丝做了一大碗汤。她的两臂也显得有了力气,独自一个把放着海亮骨灰盒的红漆小桌搬到北壁正中。她小心地把汤圆、鸡蛋、粉丝一样样端上红漆小桌。然后,从碗柜里面拿出海亮活着时用的一个小小的花边铁皮碗、一双小小的红筷,来到灶前,揭开锅盖,从大米、麦片饭里挖出一勺雪花白米,轻轻装进铁皮碗,转过身,恭恭敬敬把饭碗和筷子放到桌子的最前面。她做完这一切,从灶头油盐柜里取出蜡烛、长香,一枝枝小心翼翼燃上,靠桌子的右边放着。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