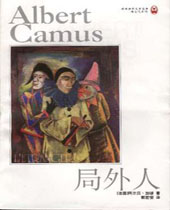鬼谷子的局-第1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田忌暗自吃惊,也是好奇心起,略顿一顿,抱拳问道,“请问庞将军,此是何阵?”
庞涓又是一声长笑,笑毕方道:“此阵名曰王八屎溺阵,专以活擒田大将军!”
原来,庞涓真也是个精怪,推知田忌善识阵势,灵机一动,想起在鬼谷中张仪串通苏秦戏弄他时所画的怪图,计上心来,依样摆出。至于屎溺这一灵感,完全出自他在寻找兵书时从树洞里摸到的那堆野猪屎。
这一个王八孵卵的阵图原是张仪的恶作剧,根本就是涂鸦之作,田忌哪里识得?庞涓当场说破阵名,连自己也忍俊不禁,像个顽皮孩子似的狂笑数声,拨马转回本阵。
田忌哪里肯受这般羞辱,脸色紫红,仗剑怒道:“庞涓竖子,你——看本将如何擒你!”转对鼓手,“击鼓!”
鼓声大震,齐军发声喊,势如潮水般掩杀过去。魏军武卒似乎经不住如此冲撞,纷纷退避。数万齐军卷入魏阵,如入无人之境。
田忌昂首挺枪,催动将士奋勇冲杀。数万大军眼看就要冲上河堤,忽见沿堤槐林中升起团团白雾,烽烟冲天。时下东南风正盛,风吹雾动,疾速飘来。见到白雾,正在溃退的魏人急从袖中摸出丝纱罩于头顶,脸朝下伏在地上。齐军正自纳闷,白雾已至,顷刻间就将整个河滩笼罩。田忌猛觉两眼刺疼,方知中计,急令退兵,已是迟了。一时间,兵士揉眼,战马悲鸣,数万大军整个成了盲人瞎马,在滩头乱冲乱撞。
白雾刚刚飘过,魏人鼓声大作,正在溃退的武卒转身杀来。齐兵已无招架之力,不战自乱。千乘战车、数千战马、数万步卒堆挤在宽仅二里许的河滩上,你拥我堵,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就在此时,又有一阵恶臭随风飘来。齐人尚未明白是何缘由,但见漫天屎溺从天而降,浇得他们一身一脸。这些屎溺均被魏卒搅成糨糊状,又臭又滑腻,一旦粘在手上,连枪也拿捏不稳。许多军士更因视物不清而撞入魏营,或遭斩杀,或缴械投降。
魏军将士却是杀声震天,越战越勇。田忌惊惧交加,顾不得眼睛刺疼,跳下战车夺路而走,未走几步,惨叫一声,跌入一个深坑。
坑中臭气冲天,净是屎溺。田忌长叹一声,举剑欲自戕,却被伏在坑沿的范梢伸钩打落。紧接着,魏军众卒齐伸钩手钩牢甲衣,将田忌拖上坑沿,不由分说,拿绳索绑了个结实。
看到一身屎溺、两眼迷离、被五花大绑起来的田忌,众军士兴高采烈,齐声喊道:“范将军活擒田忌喽!范将军活擒田忌喽!”
听到喊声,齐军越发惊乱,眼睛未受伤害的拼力护着迷眼的急朝济水退却。对岸齐军远远望到形势不利,迅即下水接应。一时间,济水两岸,齐军就如两大群戏水的鸭子一般扑扑通通跳入河中。
见齐兵下水,魏兵非但不追,反而设法将仍在岸上找不到北的散兵赶入河中。因河水不深,齐兵在水中一阵狂奔。逃有一程,看到魏人并不追赶,兵士们也自松弛下来,急不可待地泡入水中,或洗眼睛,或洗屎溺,或洗创伤。一时间,宽宽的水面上人影晃动,清清的河水里满是屎尿和血污。
众将士在水中一边洗涮,一边大骂魏人手段下作,胜之不武。他们或吵或嚷,或骂或咒,谁也没有注意从上游一泻而下的哗哗水声。等到有人看到滚滚扑来的洪峰时,一切都已迟了。在上游三十里处遭到截流两日的济水一朝决坝,势如奔牛,顷刻间就已涨满半槽。可怜数万齐兵再遭此劫,在一丈多深的大水中乱踢乱蹬。不消半炷香辰光,济水下游十几里长的河面上,但见浮尸具具,惨不忍睹。
洪水刚一退下,魏国武卒就急不可待地冲下河滩,涉过济水,全力追击溃敌。众人正在追得起劲,突然听到鸣金声。魏军退回,诸将不解,纷纷纵马驰至庞涓处,大声问道:“我等正欲活擒田辟疆,大将军为何鸣金?”
庞涓笑道:“大魏武卒是仁义之师,怎能赶尽杀绝呢?”
众将却是笑不起来,只将两眼不无疑惑地直视庞涓。
庞涓敛起笑容,对张猛道:“张将军,你领兵五千打扫战场,清点俘获!”转对参军,“传令各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偃旗息鼓,兵发朝歌!”
众将瞬间明白鸣金原委,无不振奋,齐声叫道:“末将得令!”
话音落处,三军将士调转马头,风驰电掣般朝宿胥口方向席卷而去。
三日之后,在魏都大梁的王宫正殿里,司徒朱威手捧两份战报,朗声奏道:“启奏陛下,大将军庞涓于黄池大捷,斩首一万一千五百,溺毙两万五千三百,生俘一万三千二百十人,活擒齐将田忌,走齐太子田辟疆,余众仓皇溃逃;朝歌大捷,斩首一万三千六百,俘敌六千一百五十,走赵相奉阳君,余众仓皇溃逃。秦、韩两国犯境之敌,皆闻风惊退!”
朱威刚一奏完,魏惠王就将拳头“咚”的一声猛砸于几案:“好!寡人胸中这口闷气,总算吐出来了。朱爱卿!”
“微臣在!”
“为大将军修筑彰功台,举国庆贺三日,大赦天下!”
“微臣领旨!”
旬日之后,庞涓凯旋,魏惠王效迎三十里,邀庞涓共登王辇,大梁民众夹道迎接,人山人海,直将庞涓簇拥至新近落成的庆功台前。
台前,鼓乐喧天。魏惠王端坐于台,庞涓偕三军众将行至台前,叩道:“末将叩见陛下,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魏惠王看着威风凛凛的庞涓,不无满意地抬手道:“爱卿平身!”
庞涓朗声道:“谢陛下!”
“大将军听旨!”
“末将在!”
“大将军力挽狂澜,力退强敌,功盖日月,赏黄金五百,锦缎百匹,奴仆五十名!”
“谢陛下隆恩!”
魏惠王审视一眼立功受赏名单:“其余将士,寡人准允大将军所请,转批相府,依军功大小,各有封赏!”
众将军叩首:“谢陛下隆恩!”
魏惠王再次颁旨:“上卿陈轸陷害忠良,草菅人命,其罪当诛。鉴于此贼已畏罪潜逃,为正法纪,准允司徒所奏,诛灭陈轸全家,凌迟其家宰戚光、护院丁三,没收陈轸所有家财,上交国库,府邸转赏大将军庞涓!”
庞涓叩道:“谢陛下隆恩!”
当夜,庞涓来到刑狱,走进那间关押过他和孙宾的死牢,看到戚光、丁三各戴枷锁,色如死灰。
庞涓扫一眼戚光,冷笑一声:“嘿,这不是戚爷吗?”
戚光平素仗着陈轸的势耀武扬威,此时沦入这步境地,知道生路已断。然而,奴才就是奴才,看到庞涓,明知求也无用,戚光仍是两膝一软,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自打耳光:“庞大将军,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庞涓冷冷地望着他,等他打得累了,这才说道:“再打呀,你是该死!”
戚光急了,向前爬几步,跪在庞涓脚下:“大将军,大人不记小人过,您大人大量,高抬贵手,饶过小人吧,小人愿为大将军做牛做马,以报再生之恩!”
庞涓阴阳怪气地长叹一声:“唉,真没想到啊,时过境迁,连戚爷也肯跪地求饶,啧啧啧!”转对白虎,“白兄弟,戚爷既然下跪了,庞某就不能不赏面子。凌迟那日,脖颈以上的三百刀不要刮了,留他一个圄囵脑袋,免得祭我阿大时,吓坏他老人家!”
戚光颓然倒地。
庞涓冷笑一声,一脚将他踢到墙角,目光望向丁三:“姓丁的,人家戚爷都下跪了,你为何不跪?”
因有戚光的前例,丁三知道求也无用,干脆充了汉子,硬住脖子叫道:“姓庞的,今日落你手里,丁爷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要杀就杀,何必废话?”
庞涓点点头,冷冷说道:“说出这句话,还算你有种!”转对白虎,“白兄弟,这是一条汉子,骨头硬,皮厚,将戚爷脖颈之上的三百刀转到他身上。三千六百刀外加三百刀,共是三千九百刀。记住,刮完之后再剜心,剜心时,他的心一定要跳,在下要他的心活祭先父!”
田辟疆领着残兵败将溃入齐境,不无狼狈地逃回临淄。
正在进膳的齐威王惊闻噩耗,将一口米饭噎在嗓眼里,憋得满脸紫红。辟疆急前一步,又是捶胸,又是敲背,见威王仍然缓不过气来,急得跪地大哭。
太医闻讯赶来,一阵急救,方使威王缓过气来,顺口吐道:“庞……涓……”
辟疆上前正欲搀扶威王,却被他一把推开。威王顾不上龙体安康,急急走回宫中。相国邹忌、上大夫田婴等几个朝中重臣早已闻讯赶到宫外,站在那儿候旨觐见。
威王果然宣召。几人叩见,威王神色诡秘地望着他们,大半日竟无一言出口。邹忌等无法起身,只得五体投地,两臀朝天,与威王对耗。
门外的光影移动尺许,威王终于长叹一声,颓然说道:“唉,寡人十多年的心血,就这般毁于一旦!”
听到此话,邹忌他们哪里还敢吭声,只将屁股翘得更高,大气也不敢出。
威王摆了摆手:“诸位爱卿,你们……起来吧。”
几人这才谢过恩,惶惶起身,缓步走至各自的几案前坐下,将目光一齐投向威王。
威王环视众臣一眼,再叹一声,缓缓说道:“今日惨败,过在寡人。”
邹忌奏道:“微臣以为,黄池之败,过不在陛下,过在田将军一人。田将军自恃天下名将,小胜数战后骄傲轻敌,方招此辱。”
威王又叹一声:“事已至此,过错在谁都是一样。诸位爱卿——”
众臣齐道:“微臣在!”
“你们议议,为今之计,如何方好?”
众臣面面相觑。
“陛下,”邹忌奏道,“微臣以为,既有开头,就该有个结束。我军虽败,国势却无大伤,仓廪仍然充盈,再征大军十万亦非难事。反观魏国,连年征战,早已油尽灯枯,仅凭庞涓一人之力,终是螳臂当车。依微臣之计,陛下可再发大军,另择良将,与魏一决雌雄!”
“陛下不可!”上大夫田婴急道,“纵观整个过程,庞涓设计精细,用兵奇诡,并在大胜之后,放我溃兵不追,转而长途袭赵,致使奉阳君猝不及防,险些遭擒。庞涓用兵能至此境,断非平庸之辈!”
齐威王长吸一气,重重点头:“爱卿所言甚是。今日观之,庞涓才是世间大宝,田忌不是此人对手。为今之计,爱卿可有良策?”
田婴接道:“回禀陛下,魏军新胜,士气正炽,我军士气一时却难恢复。依微臣之意,我当以退为进,示弱求和,恳请魏王放回田将军及被俘将士。魏王一向托大,陛下若肯示弱,他或会答应。”
齐威王转向辟疆:“上大夫要寡人示弱求人,疆儿意下如何?”
田辟疆应道:“儿臣以为,上大夫言之有理,请父王圣裁!”
齐威王不再说话,闭目有顷,以手按住几案,吃力地站起。内臣急走过去搀上,扶他走向宫殿一侧的偏门。众臣看到,赶忙起身跪下,叩送威王。辟疆注意到,威王一下子老了,每一步都显得沉重。
就在没入偏门时,威王回过头来,两眼望向田婴:“准卿所奏。具体如何,你办去吧。”
田婴叩道:“微臣领旨。”
齐威王诏命齐国上大夫田婴为特派使臣,出使魏国求和。田婴携带数箱金银珠玉和齐国边境十邑的版图、户籍等,马不停蹄地赶往大梁,在驿馆住下,稍事休息后,驱车拜访大将军府。
庞涓已于数日前搬入新府,也就是陈轸的上卿府。在戚光的苦心营造下,内里可谓是极尽奢华,里面亭台楼阁、堂榭厅室、塘池园林、花鸟虫鱼等应有尽有,庞涓要做的不过是将大门外面的上卿府匾额换为“大将军府”而已。
田婴赶到时,庞涓正在宗祠里祭奠亡父。田婴二话不说,当即从门人处讨来麻服穿上,要舍人引他前往宗祠。
祭坛上并排列着三只青铜托盘,左边盘中盛着戚光脑袋,右边盘中放着丁三心脏。两样祭品均是午时行刑时,由庞涓亲手割下来的。唯独中间一盘空无一物。
在田婴走进宗祠时,祠中仍是人影晃动,丧乐声声,祭礼已近尾声。
田婴素衣麻服,在坛前叩拜。
田婴祭拜已毕,庞涓过来与田婴见礼,邀他至几前坐下。田婴望着祭坛,指着中间的空盘:“请问大将军,中间一盘为何空置?”
庞涓应道:“上大夫有所不知,此盘是在下特意留给陈轸那厮的。前番在下忙于战事,被那厮走脱,下次他就没有这么走运了。”
田婴佯装不知,顺口问道:“听闻陈上卿与大将军有隙,看来不是谣传。”
“岂止是有隙?”庞涓咬牙道,“是杀父之仇!仲尼曰,‘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陈轸那厮无论跑到天涯海角,在下也必揪他回来,血祭先父!”略顿一顿,似有所悟地望着田婴,“上大夫此来寒舍,不会只为询问这个的吧?”
田婴点头:“此地不是说话之处,能否借大将军一寸光阴?”
庞涓起身,引田婴走至客厅,分宾主坐下,抱拳说道:“上大夫,此地可否说话?”
田婴亦抱拳还礼道:“在下此来,只有一事,就是祭拜令尊。”朝外击掌。
两名下人抬着一只礼箱走进厅中,摆好后退出。
田婴指着箱子:“些微薄礼,难成敬意,权为令尊置办祭品之用,望将军笑纳。”
庞涓上前打开,见金玉珠玑摆满一箱,遂合上箱盖,微微笑道:“庞涓谢上大夫大礼。”扭头冲身边的下人,“上茶!”
下人上过茶,田婴品一口,放下茶杯,望庞涓轻叹一声:“唉!”
庞涓问道:“上大夫为何叹气?”
田婴又叹一声,方才说道:“方才祭拜令尊时,在下看到中间那只空盘,心中颇多叹喟。”
“上大夫有何叹喟,可否说予在下听听?”
“大将军沉冤多年,今朝得雪,手刃杀父仇人,何其快哉!陈轸虽逃一死,其妻小及戚光、丁三却举族遭屠,何其悲哉!”
庞涓听出他的话外之音,缓缓说道:“上大夫有话请讲。”
“此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大将军为报父仇,手刃陈轸、戚光一族。今齐有将士数万惨遭屠戕,万千家庭破亡,如果齐人都如大将军般申冤复仇,魏国岂不血流成河了。”
庞涓哈哈笑道:“上大夫此言谬矣!陈轸乃大魏国贼,戚光、丁三之流乃民间恶瘤,庞涓除之,是为国除奸,为民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