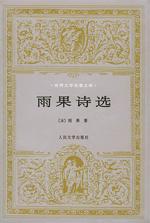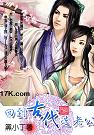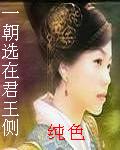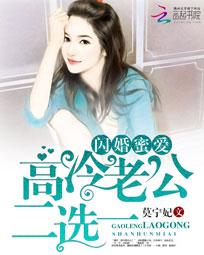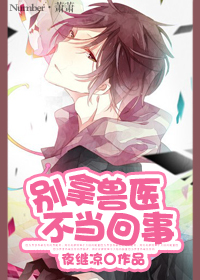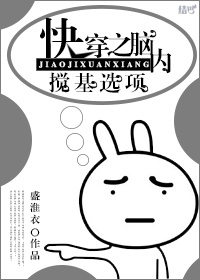钱理群文选-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
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
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历史发展
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
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
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
(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
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
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
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们“只
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
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们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
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
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们的精神避难所。
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
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
爱独处”,尽管他们现在不无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
们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
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
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
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
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
“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
图”两幅图画,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
尽了这一代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中学语文课本将朱自清描写充满“人生味”、生命
活力的南方景色的《绿》与《荷塘月色》编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它们象征
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两种人生境界,确实耐人寻味)。
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
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
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
“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
“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
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
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
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
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选自《名作重读》,钱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 月出版。)
谈“做梦”
——“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
(摘自《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著者:钱理群书号:7806033521 出版
商:山东画报出版社话说周氏兄弟,其实是在探讨鲁迅、周作人等先驱者关注过的
思想命题,以及他们探索中国的矛盾、困惑与收获。在本世纪很难找到像他们兄弟
俩这样了解中国的国情、民心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所处的困境,与他们当年有相
似处,又有新的问题,我们需要他们那样的胆识与远见。本书据钱理群在北大上课
的录音整理而成,集中了他20年来有关周氏兄弟研究的思考成果。由钱理群引领,
与周氏兄弟进行精神对话,实在是莫大的快事。汉林书城(。hanlin。)推荐)
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梦的现象,这种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由这个梦造成了一
种什么样的国民性?周作人在二三十年代已预感到,中国国民性出现了新问题。他
将其概括为“专制的狂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概念。它有两方面含义:一
方面是狂热的信念,或狂热的迷信。中国民族没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的狂热,但
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狂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一种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
主观精神和意志,并将其夸大到极端,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第二,迷信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的发明,将亿万
群众煽动起来形成强大的运动。他说:“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大,干劲大,一
张白纸正好画又新又美的图画。”他强调多数人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迷信多数。
第三,迷信权力。将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仿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
创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无知等等。无论“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
“文革”,年青人都是打先锋的,毛泽东说:“卑贱者战胜高贵者,年青的战胜老
年的,无知的战胜有知的,小人物战胜大人物,这是规律。”很少有像我们共和国
那样夸大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捧到极端。因为青年有热情,惟有青年能够献身,也
最容易被利用。这种“青年崇拜”实质上包藏着对青年的愚弄。
迷信主观精神意志的同时是反科学,反理性,在迷信群众运动的另一面是反专
家、反知识分子,在迷信多数的同时压制少数,在迷信权力的同时压制民主,在迷
信青春的同时反对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说的“专制”,而且
是群众专制,多数人专制。凡是持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都称为“花岗岩脑袋”,要把
他们“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拔白旗”运动不但在农村、工厂基层广泛
展开,在大学里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个重灾区,反专家、反教授、反知识,
“知识越多越蠢”。当时称这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为“革命的狂欢节”。这首先是
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前面说过的赛诗会的诗一句比一句激动人,显示了语言
的魔力。这种狂热的语言可以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人在
语言的迷恋中,丧失了自我,进入半睡眠状态。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
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
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
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的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批判会”
上,年青人运用语言的暴力强加于自己的老师,其实也在践踏作为自身存在基础、
理由的知识与科学理性。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
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一
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鼓动人们去迷信,并赋予“正
义感”和“合道德”性。这就使这类“狂信的专制”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
色彩。
在全民梦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
观地说,知识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澜者。比如说,亩产上万斤的粮食
上报是由省的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作证的,某大科学家亲口对毛泽东说:“根据科学
研究,在理论上亩产上万斤是可能的。”无数的诗人、作家都参加到“全民的狂欢
节”中,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本来知识分子应该在全民狂
热中起“清醒剂”作用,但却推波助澜,这恐怕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
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天风气之先”,而实际上是在赶时髦,为虎作
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这里也隐含着对于权力,对于“专制的狂信”的恐
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样的“赶潮流”
之风至今也没有停息,知识者仍有可能继续充当“推波助澜”者。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第一次见到摩罗,我是有些惊异的:这样一个文静的书生,怎么竟然以“恶魔”
自居,而且为文坛学界所认可?————这一回,为写这篇序,通读了他的大部分
文稿,又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引起了长远的思索与无尽的感慨。
我想起了世纪初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呼唤————“摩罗”的笔名显然是源
于此的。那时候,鲁迅正在惮精竭虑地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
的道路,“别立新宗”,即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
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
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但鲁
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他于是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
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
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
“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被惩罚、被改造,导
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到了摩罗这一代,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并要从前辈
那里寻求精神资源时,他们所面临的,竟是一片精神废墟。正像摩罗在好几篇文章
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他对被权势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充满
同情,但从他们受难的姿态中,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看到的却是渗入灵
魂的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
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被驯化,奴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
还没有引出必要的教训,以至他们中间少数觉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这是
真正的危机: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这样
的发现,使摩罗惊恐不已。而尤其让摩罗痛心的是,他竟然难以开口;因为一说出
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摩罗毕竟未
经“改造”,血性尚在,勇气犹存,他奋笔直书,陆续写下收入本集中的《由从势
者到求道者的位移》、《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等
文,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
我从他的这些文章里,重又听到了鲁迅当年的“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
安在?”的呼唤。
而对摩罗这一代来说,也许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于
是,又有了摩罗自称的那个“哭泣的黄昏”的“死亡体验”。“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
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
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
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哭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
末至9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
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
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
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
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
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耻辱”:
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致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
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
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就
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
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
苦难。”“描述耻辱”所指的是建立在自身“确定的体验”与“稳定的性格”基础
上,从自己内心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内容与方式。
摩罗,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方式,发言了。
作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他们已经认定要与一切奴役人的制度、
思想、观念作不妥协的反抗,他们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人
性的需要与历史的需要”,因此时刻准备着“战斗后的失败”,并且正在磨炼自己
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