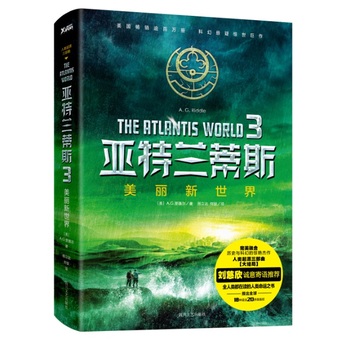阿坚:美人册-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刘晓庆、刘文彩,最后聊的力兄。她几次想让我谈你,我都转到你的优点上去了。对了,她这次所谓随团采访是她非要跟来,是自费。”
“我明天再来——我这骑车来回三十多公里呢。”
小来姑娘(12)
27
“她又没在吧?”吉一开门就问,“我昨晚饭后去她那儿,她正在跟几个邻居打麻将。桌上的钱都是十块一张的。我让那个邻居走,她还拦着,说玩得特来劲。我问她输了多少——她肯定输,那几个邻居都是老麻,肯定仨人抠她一个呢。我告她你明天来,她没说什么;我说你今儿来过,她也不说话。就是抽烟、出牌、递钱。那几个人都抽她的烟。”
“吉,这要有毒品她非去吸毒不可。”
“没那么严重。她有时的风格是有赌博的特点,不能愣劝;再说也该让她报复你几天了。你也不用天天往这儿跑了。呆会儿你写三张给她的条,签上今、明、后的日期,我一天去给你贴一张。她若看到你天天都来而不遇,锲而不舍,会动点儿心。”
“吉,那你贴时,小心她正上楼——那样,哥们儿可就一点儿戏没有了。算了吧,还是我每天来自己贴吧。不耗耗体力,我更难受。”
“那你活该吧。”吉一摊手。
“快给哥们儿削个萝卜,嗓子特难受。”
28
下午,有人敲我小屋门,敲了两遍“探戈”的点,我从没听过。我喊请进,门没动。
我一拉门:小来。
“真没想到是你;在这个门上,我从没听过你的敲门声;再说自己家门还用敲么?”趁着她笑,我把她横抱起来。
“我是怕万一打扰了你跟小琛小浅什么的。”
“我以为你出意外了呢。我正准备去急救中心和炮局找你呢。”见她笑到一半停下,“炮局就是总拘留所——在炮局胡同。”我把她放在床上,“快让我检查一下哪受伤了?”
她笑着搂我,一句也不解释。我发现她下眼睑有点儿颜色发深。她把我抱得很紧,使劲亲,好像三天没沾吃的了。
从下午四点到晚上11点她没怎么说话;从晚八点到11点我也话少。我们累了,双双眯了一觉。她睡得特甜却又不深,因为她半睡间还时而摸我一下。
“你该走了,都11点了。”她揪着我的胸脯。
“我今晚不走。”
“不。我嫌太挤。”她微笑着说。
“那我呆到12点吧。”
我俩静静躺着,好像在比谁能坚持沉默。
“是不是有时沉默特舒服?”
她点头。
她还不出声,我去搔她肋下。
她故意把胳膊张开。还顶着我的劲,以加强效果。
“死皮。”我捏起她肚子上的一层皮肤。
“别忘了,咱们是三年。”
她在空中画了一个“对勾”。
“三年之后我还想活。”
她闭上眼睛。
“万一我要喜欢你的时间持久呢?”我晃她。
她指指钟。
“万一钟都跑坏了,我对你的喜欢还没变?”
她还指钟,又加上了门。
“好吧,争取明天见。”我整理好衣服,拿起车钥匙,临出门又亲她,感觉到她的舌头比说话时还活泼。“今晚真好。”我推开门时说了这句话。
轻轻的一声“嘎噔”——屋里一下黑了。她拽灯绳的动作是她今晚最后一句哑语。
29
我除了上街吃饭,足不出户,就是出去吃饭,也大开着录音机;车钥匙扔在明显的位置上。
第四天晚饭回来,有张条。没抬头没落款。
“出租在等我,还有40分钟火车就开了。你要能追得上就来送我吧。”
录音机仍在响,只是磁带被谁翻过了面。
刚才那顿饭我喝了点儿酒,用了半个多小时。
我骑上车,到了西单路口。想了想,我向西拐,去了吉家。路上,红灯很多,仿佛那三个灯,只剩红的没坏。
30
五天后,小来来信:斯健,等检票时,我特怕你来,也特怕你来了就挽留我。刚一检完票,我站了半天,等着你出现,有几个人特像你,我都快喊了才发现不是。走上通道我多次回头。每一次都决心这是最后一次。你没有来。或者你来晚了。转告吉,没能跟他告别,还有小央,她是个好姑娘,好妻子;我不是也不会是。我喜欢吉说话,若能常跟他聊聊天,那真是舒服,他的知识比你丰富。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朋友。对不起,我一直没能习惯你们的萝卜。这信是在火车上写的,得回到成都再发。我也不知回成都将要怎样。爱我的穷诗人有,想娶我的阔佬也有;父母还让我赴美;报社还让我毕业后就来。我打算一进家就先关门睡两天。祝你健康!小来。
发信前,我犹豫一下,还是寄给你吧。又及。
我复信:
小来,在你的信封里没有倒出你家的门钥匙,我知道你不是忘了。这两天我搞来一些舒曼的磁带,天天听。并打算托人捎给你。我可以托自己捎给你么?我没有去车站追你。去了吉家,“吃萝卜,就热茶”。吉说那天你输了二百多块钱,他问了那边的邻居。我们仍然写,稿费零星,有时也抽骆驼以下的烟。我很想你,甚至有点儿悲观。我不希望你和力兄好。我写了二十多个小笑话,都是咱俩的小事。附在信后。我喜欢你,还没到三年呢。这一点你也别忘了。祝你好!斯健。
十天后,我再致小来信:
来,我的小屋已生火,比你住的那几天暖和多了。破的窗户,也糊了新纸。我用写大字的宣纸糊的,挡风却透阳光。对面房脊上的鸽影能映在窗纸上,纯是线条。几只刚断奶的耗子,身子也就栗子那么大,在地板上乱跑,不特怕人,那小眼睛也是婴儿的目光。它们的鼠娘,大概是你刚到京那天受的孕。吉和小央都问候你,还说那几个邻居要把赢你的钱退你。你对我的态度就好像给合唱起了一个头:我老婆和小琛现在都不爱搭理我了。所以我的身体不得不像出家的僧人那么好。也祝你健康。斯健。
小来姑娘(13)
31
约半月后力兄来信:
斯健:小来一周前两次自杀,未遂。第一次吃了200片安眠药;可能是,因为床头剩两个空瓶。被邻居发现后送医院急救。事隔两天,又服二百片,但第二天上午抢救后醒来,便割开手腕脉管,又被亲戚发现。她现已住进精神病院。谁都见不到她,除了小迈,我估计这和你有关,我觉得她不想真死。她从京回蓉后,我跟她聊过两次,没见异常,可见她隐忍之深。一有可能我争取见她。没想到你俩还真是爱得死去活来。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我就不说你什么了。
我即刻致信小迈:
朋友中只有你能接近小来,你们最要好。请你看在咱们过去感情的份上告诉我:需不需要我马上赴蓉?需要钱吗?我能够做什么?小来的病型是什么?她现在身体和精神到底怎样?你若能劝导小来抛弃厌世的念头,我会感激你一辈子。一年多未联系,不知你地址变否?
但愿你能收到此信。
32
十多天后,力兄复信:
斯健,我们已去医院探视过小来,现在基本正常,还跟我们开玩笑呢。她和我们都没提你。医生说她是严重的抑郁症。她答应我们不再自杀。在花园里散步时,她跟我说她不希望小迈知道她的事。大夫说她最多一个月就能出院了。但她表示想多住些日子。她说在家里休息不如在医院里。她的国内外亲戚来了不少,有的正在给她跑出国手续,她说无所谓。你若写信给她,不要说太多,别开玩笑。我会常去看她的,我也喜欢她。我最近没写诗,但还会写的。吉跟我的彻夜长谈,现在也让我感激。代我问他好。你的新作像历史白话文,大一时就读过。
我让力兄转信给小来:
来,我整理出一组新的诗,是你在京见我正写的《皇家猎场遗址》,大意讲:时间苍茫,朝代如水;再显赫的康乾盛世,再伟大的帝王,不过都是过眼云烟。所以,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力兄说我写的不是诗,是历史白话文,说他们读大一时就读过。在成都,我挤兑他的诗。我知道,他这不是报复。最近又出些散文随笔,容易换钱,写时也颇似休息,好玩。我身体越健康就越惦记你,怕你生病,怕你被人欺负,怕你抽烟过多。力兄善良而仗义,我挺感动。当面不好说,请你转告。祝好。健
33
又是周三了。今天倒是没什么西北风。
今儿骑得快了些,加上我小屋的钟可能快了,不到四点我就到了吉的楼下。我在楼下溜达到四点才上去敲门。
等了一会儿门才开。像每次一样,吉开门时在系着皮带,眼睛还没全亮起来。
我看看墙角:“心里美”还在网兜里系着。桌上是茶叶的纸盒铁盒,都是些名牌。
“又有新消息?”吉一边沏着茶,看完了水涨到杯沿儿,才把目光抬向我。
“没有。”我看看乌黑的茶叶在水中舒展开,“今儿是什么乌龙?”
“‘黄金桂’。你等会儿,我去洗萝卜——现在那个卖萝卜的‘眼镜’每天都挑几个好的给我留在网兜里,每天我都是中午下班去拿——”
“是不是跟每天取奶似的,特定时?吉,你说能不能造一种萝卜‘奶’,肯定价廉,省得人老得洗呀削皮呀怕糠呀。”我跟吉到了厨房,“贵人不吃贱萝卜,可喝萝卜‘奶’他们总不掉价吧。到那时,小来小琛她们,‘啪’一声打开易拉罐,就往嘴里倒萝卜汁——不,萝卜‘奶’,那多好玩。”
我俩回到屋里,吃口萝卜喝口茶。那种“嘎巴”咬下口萝卜的脆声和“嘘嘘”的喝茶声,充填着说话之间的沉默;萝卜声和茶声反而使沉默更加清晰。
“吉,咱们在小来那儿算完蛋了。”
“把那个‘们’去掉。”
“你不是也给她讲过人生之道吗?讲的总不是人死之道吧?我不相信她是为了区区爱情自杀——她不会干这种俗事。”
“斯健,你的意思她是:朝不闻道,夕死可矣。若真这样,她可比闻道而死的人还超脱呀。‘道’算什么东西,还得等到明早知道;这种等太无聊了,算了,不等了,今晚就死吧。等那个‘道’时的无聊程度可能比得到那个‘道’时的幸福程度厉害多了。”
“也是,知‘道’了再死,与不知‘道’而死,在这死之后有何不同呢?就算未来能研究出哪种不同,于那个死者又有什么用呢?”
吉给我续水,“越说越晕——你觉出来了么?现在萝卜不如十年前的好吃;个儿倒都不小;全是化肥催的。”
“没错,十年前的姑娘多纯朴啊。要自杀就为爱而死,那多豁亮。为‘我有迷魂招不得’而自杀这可真他妈的变态,都是那些现代艺术,对了,就跟化肥一样,把人给催得‘走向深刻’。‘深刻’那玩意儿哪能是个人就能担待呀。”
“怎么又绕回来了,别老惦着小来的事啦。”吉又喝了口茶,不咽,在嘴里来回漱,呼呼作响,好像要把嘴里的萝卜末一点不剩地“营养”到肚子里。“咕咚”一声之后,吉张开了嘴:“斯健,你也是替小来瞎操心,她不是被救过来了吗?不是快去美国了么?你放心,‘抑郁症’虽然行为极端,但并不难治——我查过精神病学。并且很多文学、艺术、哲学大师,都有这毛病——就跟天才的特点似的。”
“咱俩这辈子怎么也不会成为大师了。”我接道,“压根儿也不忧郁——先天素质不足。”
“我高中那会儿,就快到‘忧郁’的边上了。”吉也来了精神,“要是及时看看梵高的画、蒙克的画什么的,听听老柴的‘第六’、老贝的‘第五’什么的,估计也就忧郁成功了。可是——”吉正在想,但手势已经展开了。
“你老吃萝卜。”我一边指着。
“唉——结果,那种‘准忧郁’慢慢消失了。现在是彻底没了,再听谁的音乐,看谁的画,再碰上什么事也不会忧郁;最多就是忧伤吧,也不是,是不高兴;比如丢了钱失了恋什么的。斯健,你这几天是不是想学‘忧郁’了?”
“不至于,咱这种打萝卜嗝的人要是也忧郁,那么忧郁还有啥价值呢。”
“斯健,我给你讲,小来有忧郁的素质,又经历过生死关头,再加上你教给她的一些有用的‘俗’,她可能成就一番呢——对了,她还能去美国,父母有钱,不用为生计操心。我看你以后别给她写信了,各安天命吧。她吃她的美国苹果,你咀你的中国萝卜——来来,再吃两块,都给它吃了算了。”说着,吉把桌上的几块萝卜用手从中间一分,然后带头拿了一块。
萝卜皮已经一地了:一片儿一片儿的,像新鲜的树叶。窗外,杨树杈光秃秃的,一点儿不晃。
“那你重新给我沏一杯。”我端起杯给他看,“哥们儿这茶都没色儿了。”
小香姑娘(1)
离开小街,阿江骑着车刚拐进一条胡同,车速就慢下来,他望着前面两个也停下脚步看他的姑娘,〃小凤〃,他平淡的脸上鼓起笑纹,柔声地喊着,那话语像从笑纹发出的辐射物,以至传到五十米外的她俩那儿都散弱了。她俩不应不语,小凤只是嘻笑着,另一个冷眼观看阿江。阿江也是盯着另一个:鲜鲜亮亮的白腿白臂,脸粉眼黑,真丝短衣短裤中的身子骨小小巧巧;正面看上去的小胸在头顶的阳光下映出些许阴影,斜在那件米黄色的无领衫上。阿江骑到跟前才把眼光转向小凤。
小凤轻一跺脚,她是软底便鞋,没跺出什么声,只是脸借着震动换成怨情,道:〃等你两个多小时,真烦人,你不说你两点从来都在午觉么。我们俩正准备走呢这是小香,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她又转向小香说,〃小香,我不骗你吧,阿江真的有一米八,他不爱穿好衣服,所以个儿不显……〃
〃我年轻时个儿还高呢,〃他见小香笑唇一启,便望向她脸:白光中泛些粉晕,不是涂的脂粉,扁平鼻子和脸颊的过渡很均匀,眼睛眨得大大的,上下睫毛半真半假地很清晰,脸比鹅蛋疏略一些,唇较厚软,因为她张嘴时唇型变化挺大,声音倒清楚,〃你好,阿江,〃她平直的视线只是盯着阿江衬衣领下的第二个纽扣,〃小凤非拉我来,我做活的那家中午都睡觉了,我才出来的,下午还得洗泡的好多衣服呢。〃
〃别呀,再呆一会儿,你们先回我小屋,我去买冰激淋,〃他说着去拢小凤的肩往胡同里走着。小凤穿的平凡一些,梳两条长辫,用皮筋扎着,她脸黄白些,侧影的面部线条颇起伏的。阿江拍拍她的瘦肩,〃小凤,多吃点肉呀,你做活的那家是不是特抠、老让你喝剩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