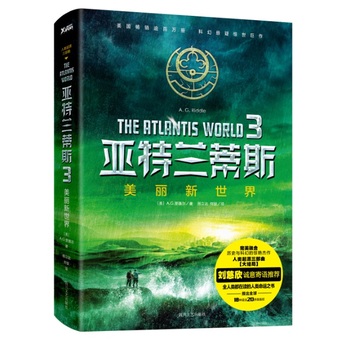阿坚:美人册-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把酒都推到施建跟前,“得了吧你,别装了,有本事你都喝了,我再去买几瓶;人家胡默是喜欢我才对我厉害,你是不喜欢我才对我好,你比他虚伪,可雷也虚。”黄的脸有点儿红,不太均匀,越靠近眼圈越红,“我爸千坏万坏,但他有一句话是真——成功的人有时必须低三下四。我想出国有啥不对的?我一个女孩儿不靠年轻靠什么?我后妈,怎么当上的讲师?不就是在我爸那儿舍得出年轻漂亮吗?其实有什么呀?要不她不还在小县城当教员吗?她其实不喜欢我爸。一样,我爸也就喜欢她几天。你们男人,那么坏,就不许女人坏一点儿吗?”她越说眼睛越红,抽泣得胸脯一抖一抖的。
丹琦姑娘(5)
施建抬了几次手,到半空又还原,又抬,刚要接近黄的肩正逢她晃头发,他一拐把手扣在自己耳朵上,挠一会儿才搭在黄的肩上,“黄,听我说,别哭,要不人进来以为我怎么你了呢。没关系,坏一点儿可以,但要把‘坏’用在刀刃上,争取用一点儿坏换一大块好;不能傻坏,那就白坏白吃亏了,说白了就是:牺牲年轻要牺牲得值得。”施建见黄抬头张开了眼睛,接着,“你不能瞎撞,瞎撞的姑娘你知叫什么么?叫傻——那种傻——瓜,别说好人,坏人也不待见,玩完就扔,懂吗?好了,都12点了,睡吧,你一哭倒挺像小孩儿的。”
黄从肩头找到施建的手,拽下来,两手抱着揉着。施建的手,骨节大,指长,皮皱,指甲盖梢是黑的;黄的手白乎乎的一团光,手背上四五个小坑是暗的。施建手腕一翻,把一只白手攥起,一边挪到黄的边上坐下。
“咱们躺会儿吧。”黄说,“可雷的话没错。”
施建把右臂伸到黄的颈下,“可雷说我不坏是不?男人差不多,可我没有护照,工作证还是好几年前的。”他的左手已抚起黄的脸来。
“你的手尽茧子,蹭人,轻点儿。”黄睁着大眼睛,半天一眨,瞳仁里有一个微型的脸,虽小而细全。“别摸脖子,痒痒。”
那双骨节很大的手已滑到胸口了,在中间的凹处,不动,轻轻颤着,“黄,你真年轻,好,你这衣服质地好,摸着就跟皮肤似的。”忽然施建的手就落在黄的左胸了,“行吗?”
黄的脸平平淡淡,“可雷说你原先特招姑娘,那天在长征饭馆我觉你就那么回事,现在我觉你挺好的,比可雷,也不是,比——别,别,我不喜欢。”
施建坐起,抽颗烟,“你睡吧,对,你还没洗呢,我去散步。”
“算了,不至于,你把大灯关了就行,开你的床头灯吧。”
施建枕臂躺着,那股光芒刚好照满他的脸:额头最高,离灯最近,光把皱纹擦了;瘦型脸;颧骨处也是两个光点;还有鼻头和鼻梁,比低平略高些,鼻孔隔一会儿射出两道蓝雾,像蓝光;眼睛长得一般,僵直,像控制着;嘴唇不断地动。
那边墙角传来水声,毛巾搓水声,关门声很轻,插门声,暖壶水进盆声,窸窸窣窣声,水被撩起又落下的声,共七八声……
“明早见,祝你睡个好觉。施建,你挺好的。”
“屁!”
四天以后,施建回家时见院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打量一会儿,在门口愣了一会,没进屋门就喊,“胡默来了吧,哥们刚吃完,你早来呀,咱——”
胡默坐在黄的床上,床头是各种女式衣服,有那件绿黄相间的无袖裙。“哥们,你丫可以呀,还假模假事儿地弄俩床干嘛——哦,你丫怎么又瘦了。”
“这几天没睡好,跟那画家似的。你今天把她领走吧,哥们这几夜跟熬鹰似的。”施建嘿嘿笑着。
“别装丫挺儿的了,我说你啥了?瞎解释什么呀?前天我就知她住你这儿,可雷打电话给我了;她在你这都住一礼拜了吧?你慢慢伺候吧,我给她留一个条就走,让她去找歌剧院一唱歌的。”
胡默写条,写了两张都揉了,第三张写好就站起,“走了,她要不好好学我就不管了。告诉你,陈力回四川前说这女的下眼睑大,是铤险之人。他懂相学的,你可留点神儿。”
“呆会儿再走,就算我把她怎么了你就不愿在我这儿多呆了?可雷安排她住这儿的,说实话,我也——算了,甭废话了,我反正也挺喜欢她的——行行,我不说了。咱俩喝点儿啤酒去,哥们请客,昨儿收了三十块稿费,就是你说我写得最臭的那首诗发了。”
“我今儿有事,改日吧。留着钱你补养身子吧。”胡默走了。开车锁的声响了半天,钥匙乱响,开了,屁股很重地打在座上。
施建追出门,“胡默——”他回到屋,愣了会儿,捡起地上两个揉皱的条,展开,是地点人名,好几个错别字被涂得很乱,像几团小乱麻,那处纸也被写漏了。
晚上,施建和黄在辽阳春饭馆,只有砂锅白肉和溜肝尖、鲜蘑油菜摆着。“这是我最爱吃的三个菜,”施建夹第一片肝尖在黄的碟里,“真是,你请我五六顿了吧,你今天也别加菜也别掏钱,你别管。你不是老想听我念诗吗,听我这首:
多少次望着她房间的灯光
我的目光打不开那个小窗
那个小窗总是关得很严
她知不知道窗外有春天——怎么样?”
“酸臭。”黄摇摇头,轻快地夹了一个蘑菇。
“我要的就是你这回答,酸臭吧,它换了三十块钱呢。又硬又香的东西人家不给你发呀。这几年写的东西,几乎发不了,稿都不退,可我抄些七八年前的玩意儿,有时倒能换回钱了。你那天不是问我怎么挣钱吗,卖酸臭呗。”
“你这么活累不累?”黄问。
“比你轻省,我牺牲一些虚伪的酸臭,得些钱,你牺牲的可是真东西呀。”施建说。
黄放下筷子,“其实,感情甚至——怎么说呢——睡觉都可以虚伪一下,换些必需的,反正心里明白就行;男人的虚伪可能是话,女人的虚伪可能是——反正你明白是啥,女人还有什么呢——服装店老板说我要表现好就长工资,他比可雷和你坏多了,连虚伪都不用。”
丹琦姑娘(6)
“你从哪儿学得这些道理,看不出来。”施建向她举杯。
黄只拿筷子敲了一下施建的杯:“施建,告你,我15岁就懂人事了。”
两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黄说:“胡默今天来没说什吗?光留下条子?”
“他说让我留神你;他看见你住我这儿,不是特高兴,可能觉得咱们已经那什么了。你说我冤不冤,都没地儿申。”
“这几天你睡得不是挺好吗?”黄笑。
“可不,我在心里把自个阉了,习惯了。你倒好,真把我当太监了。”
饭后回屋,各自躺下,一个睡着了,一个写到半夜也睡了。
“谭吉,你丫好久没来了,忙什么呢?”施建对刚落座的高个儿方脸人问。
“这不,我带来了,出了本小说,这几天正各处跑发行呢。”谭吉递上一本书,书名是《自由的忧伤》,忽道,“哥们,你丫的桃花又开了?哟,还这么多化妆品哪,挺高级的嘛,跟我原先老婆的差不多。”他又去盯床头那些花衣服。
“别提了,这姑娘是可雷存这儿的,准备让胡默取走的,光让我守着,比守活寡可难多了。”施建从半躺坐了起来。
“哪儿的?”吉问。
“17岁,南方的,想出国,也想学唱歌。对了,吉,让她搬你那儿住去吧,你那西屋不是空着嘛!”
“搬我那儿去?”
“要是一般的姑娘,我努努力也就成了。这姑娘,跟可雷不错,可雷怕老婆就想把她介绍出去;胡默最喜欢她,又拿架子,他见黄丹琦住我这儿极不高兴——本来是应住他那儿,还不如住你那儿去吧,别让哥们活受罪了。”
“现在她在哪儿?见见再说。合着你想把包袱扔给我,让胡默恨我。你忘了,上学时不就因为二班那女的他说我虚伪吗。”吉说。
“就在西单十字的商店卖衣服呢,呆会儿给她打电话,咱仨位一起吃晚饭。我现在就去打。”
施建来到公用电话处。拨通后,“是小黄吗,是啊,告你呀,我这来了一个作家,刚出了一本书——你别急,人特好,他住两室一厅——什么?你不想换地儿——先见见再说,五点来辽阳春饭馆吧……”
吉和施建在辽阳春点了酒菜,正吃着,吉一直盯着门,“嘿,是她吧?挺‘beau’的嘛。”
施建扬起手,“这儿哪。”拉出另一把椅子,“坐吧,怎么晚了半小时?迟到者买单。这是谭吉,写小说的,我们同学。哟,化这么好的妆见作家呀,是比陪我时漂亮。对,这是小黄。”
“刚听施建说你了,好!好姑娘志在四方。”吉的表情开始丰富,“我正打算写一个外省姑娘在北京折腾又去东京折腾的小说。”
“是吗?”黄丹琦开口了,“日本没意思,还是亚洲;为何不写去美国的事呢?我看看你的小说好么——都带来啦,我看看——这名子太好了,自由的忧伤,没有不忧伤的自由;我来北京快两个月了,挺自由的,就是什么都不顺。”
施建接道:“黄,谭吉号称中文系一才,认得的名人多,还有美国人要帮他翻译这本小说呢。”
“我也懂英语,高中时比赛我得第二呢。我想起来了,可雷跟我提过有一写小说的朋友,就是你吧。”黄看着吉,白脸,剑眉,眼睛中等却很黑,寸头。“你比施建年轻吧?”
“我心里老啊、白发苍苍。你真年轻啊,是应该出国闯闯,不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到国外可能老外觉你不漂亮;我认识俩长得丑的姑娘,一到美国来信说美国人特喜欢她们,说她们是东方美女。”吉说。
施建看着黄丹琦,她正给吉斟酒夹菜。施建问:“黄,你想嫁外国人么?吉说他以后也要去外国,比如地中海或佛罗里达的岛上写书。”说完用杯子挡着嘴。
“真的?”黄的眼又加了些亮,“我知道佛罗里达,到时我一定去看你,不过我喜欢加利福尼亚,海滩,长长的——我爸去过,带回好多照片。谭吉,来,咱俩干一杯。”
他俩的杯子碰时,施建的杯子也突然撞上来,“噢,把我一人剩在国内?黄,到时我去美国探亲你们,你也总得给我支个行军床吧,否则我就满世界嚷嚷你跟我一块住过抛弃了我。”
吉笑着跟黄说:“就这么定了,到时我给施建出来回机票,你管他食宿——顺便让他给你当保姆;我告你吧,女明星都雇男保姆,最好是黑人;施建不白不黑,就算混血吧。”
黄笑喘着点着施建脑门儿,“就你这样还算混血哪?山东和山西的混血吧——笑死我了,我得去趟洗手间。”
吉摇摇头,“算了,你留着吧,这姑娘咱伺候不起,怎么跟电影里下来的似的,我还以为她是挺单纯老实的姑娘呢。不过她长得挺迷人,才17岁呀。怪不得胡默喜欢。”
黄回来,嘴唇重新画过,一张嘴就冒红光,“谭吉,施建说你那儿有空房,住施建这儿不方便也让人说闲话,那天‘街道’就来问,我只好说是女朋友,人家还让我去办暂住证。麻烦。你英文肯定好,咱俩可以练口语。”
吉给施建使眼色,施建只笑不言。吉说:“黄小姐,我女朋友老来找我,你去住怕——”
“我又不跟你住一屋,就跟我住施建那儿一样,我也不是他的女朋友呀。”
丹琦姑娘(7)
“反正,黄,”施建开口,“别在我那儿住了,你虽不是我的女朋友,可你吓得我的女朋友都不来了。这几天有姑娘来找我,一看小床和你的衣服——你还故意把内衣都摆在明处,人家就不搭理我了。”
“别骗人了,”黄说,“你想撵我,谭吉那儿也不能住,好,我不麻烦你们,今晚我就搬走,不就是睡服装店老板那儿吗——是不是我陪你睡,你就不撵我了!”黄瞪着施建。
“好吧,”吉说,“就住我那儿去吧。”表情各占一半在脸上,左边无奈,右边像笑。
第二天,施建打电话,“胡默,别小心眼了,黄搬走了——你猜——不是——不是——哦,你怎么猜出来的——怎么着?下午来我这喝啤酒吧——什么?——再说?——你丫随便吧。”
不到四点胡默来了。施建躺着,眯着眼,又打一哈欠,“我以为你不来了呢。来也晚了。正好你帮我把那床支起来吧——人去床空哟。”
“你让她搬谭吉那儿去干吗?真操蛋。”胡说。
“这你又着急了吧,还不如你早些把她领走。上学时,你记得不?你跟那女的摆架子可是吉不摆,结果——你以为吉愿意带黄呢。”
胡默接道:“得了吧,我最腻味因为一姑娘跟你和吉这样的缠在一起了,你们太不懂游戏规则。你们别老把她往我头上安。可雷把她塞给你,你再推给吉,不像话,再说,她住你这儿就住你这儿吧,你丫赖了吧唧的,也太伤害不了她,吉呢,他倒不见得喜欢跟女孩子睡,他总爱逗女孩子,把人家逗得疯疯颠,他就满足了——‘纯粹’地玩弄感情。我觉黄丹琦挺可怜的,第一次见她时,她说她那家怎么龌龊、她怎么挨打怎么不服、怎么硬跑出来,那天她都哭了。当然她也虚荣、势利、骚——其实她还不懂骚。稍微帮她一把,没准儿就能出息呢。本来我上午刚写完给你的信,说她啥时来我这儿住都行,结果你来电话了。歌剧院那人打来电话,黄丹琦一次没去学过歌。”
胡默就坐在黄的小床上,空空的,只剩旧褥旧单,往后一靠,冲天花板说:“她也真能屈就,这破屋破床都能睡——”
“还有我这破人是不是。胡默,别提她了。我告你吧,每天都有不少姑娘学坏,也有不少学好。这也是伦理生态的平衡。你联系德国那事怎么着了?像你这样不随和的趁早去国外吧。”
胡默不答,隔会儿却问:“吉那儿不住着一个姑娘么?”
“早走了。你不信拉倒,吉不喜欢黄。”
“我知道;他不就想逗着玩么,也好,这回写东西有好素材了。走吧,喝啤酒去。”
两天以后的下午,胡同的老太太喊:“施建,电话。”
“噢,是吉呀,玩得好么——什么,让我过去——什么,黄丹琦——救过来了——操,怎么搞的——人没事吧——你有事?一夜没睡——行,好样的,你瞎逗人家来着吧——没有?——好好,等我过去再说。”
施建乘地铁去西郊吉家。
吉开门,一脸虚白,眼也发红半睁,“小点声,她正在那屋睡呢。”进了大屋,吉关上门,“你丫来了就好,哥们儿弄不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