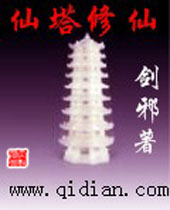洛丽塔-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于1935年。参加演出(我注意到我在前一段里的笔误,但请不要改正它吧,克拉伦斯)《被谋杀的剧作家》。贱人奎因。犯下谋杀奎尔蒂的罪。噢,我的洛丽塔,我只有这几句台词!
离婚手续延误了我的行期,又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在地球上笼罩,此后在萄萄牙又度过了一个患肺炎的倦怠冬天,这才终于抵达了美国。在纽约我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命运提供给我的一件轻松工作:它的要务是开动脑筋编写化妆品广告。我喜欢它散漫的特性和伪文学性的外表,只要没有更好的事做,就去干这活。另外,我受纽约一所战时大学的敦促,着手完成专为英美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费了我几年的工夫,每天工作量很少,在十五小时以内。当我回首这些日子的时候,我看见它们整齐地分裂成宽裕的光亮和狭窄的阴影:光亮是属于在宏大的图书馆进行研究所得的慰藉,阴影则是属于我那些恼人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说得不少了。到现在为止,了解了我,读者能很容易想象到,当我急于瞥见一个在中央公园里嬉闹的性感少女时(啊,通常离得很远),我会是多么烦困和燥热;而当那些除过臭的职业女郎,被某间办公室里某快乐汉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会怎样被击退。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一次我病倒了,险些要命,这使我在疗养院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是又住进了医院。
需要体力的户外活动,好象对我很有裨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医生,一个很有魅力爱讽刺的家伙,留着浓浓的褐色胡子,他有个哥哥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赴加拿大北极地区。
我被委派作它的〃医药反应记录员〃。我与两位年轻植物学者和一位老木工偶尔分享到(从未很成功)我们的一位名为阿尼塔.绚翰逊的营养学家的厚顾——他不久就飞回国了,我很高兴这样说;关于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所知甚少。根据投入的气象学家的人数判断,我们可能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磁极,一直追到了它的巢穴(在威尔士王子岛的什么地方,我想。)有一小组,与加拿大人在麦尔维尔海峡的皮尔方位会合建立了一座气象台。另一小组,也同样误入歧途,收集起浮游生物。第三组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起肺结核病来。伯特,一位电影摄影家——一个不可靠的小伙子,我曾经和他一起奉命分担一大堆仆人的工作(他,精神也有点毛病)——坚持认为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的是考查天气改良对北极狐皮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宿在花岗岩后寒武纪世界中,住的是预先建造的小木屋。我们的供应充足——《读者文摘》,冰激凌搅拌器,药物卫生纸,圣诞节的纸帽。我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了,也许正因为缺乏幻想,日子空虚。周围都是萎靡的植物,比如矮柳灌木丛和青苔,我猜想,它们又被狂吼的大风渗透吹净了;在完全透明的天空下(然而,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靠天空显现)坐在一块大鹅卵石上,我奇异地感觉到肉体疏远了我自己的灵魂。没有诱惑物使我发疯。那些脏乎乎又红光满面的爱斯基摩小姑娘,一身鱼腥味,满头乌黑吓人的头发,豚鼠一样的脸,对我激起的欲望甚至比约翰逊医生还少。在极地周围,性感少女是不会出现的。
我把分析冰河堆积物、椭圆形冰丘、小妖精、俄国城堡的工资交给了我的长辈,一度曾试图草记下我愿意认为是〃反应〃的东西(比如,我注意到在深夜太阳底下梦见的事物易于高度着色,我也认为有必要就许多重要问题测验一下我的各类同伴,比如怀乡病、对无名动物的恐惧、幻食症、梦遗、爱好、收音机频道的选择、表情的变化等等。所有人对此都厌腻透顶,于是我只好立刻彻底扔掉了这一项目,不过,在二十个月冷劳动(一位植物学家这样命名)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虚构了一份精心伪造且非常富有情趣的报告,读者可以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的《成人精神物理学年鉴》上读到它,同时在《极地探险》杂志为那次远征所发的专号上也有刊登;总之,那次远征与维多利亚岛上的铜翅蝴蝶之类并无真正关系,这是我后来从我和蔼的大夫那儿获悉的;它真实的本质是被喻为〃秘而不宣〃的,所以仅让我加上一句,无论它是什么,目的是极好地达到了。
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失常(如果是忧郁症或一种不堪忍受的压迫感,用这残酷的字眼很适宜)又发作了一次,读者一定会为我感到遗撼。我又彻底恢复了我在先前那所极其昂贵的疗养院治病时发现的一件事。我发现戏弄精神病医生真是乐趣无穷:狡猾地引他们误入歧途;永远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玩这花样的门道;为他们编造复杂的梦境,纯古典式的(这使他们,梦境勒索者自己也做梦,并尖叫着醒来);用虚构的〃原始场景〃愚弄他们;永远也不让他们瞥见一点点一个人真正的性欲状态。通过贿赂一名护士,我得以接近一些档案,欢欣地发现一些卡片上说我是〃潜伏性同性恋〃以及〃完全没有性能力〃。这场游戏真是太棒了,它的结果——就我而言——是使我在痊愈以后(睡觉很香,胃口象女学生),还整整多呆了一个月。而后我又加了一星期,只为了一位强壮的新来者,他是个被免了职的(当然,也是精神出了问题的)大名人,出名是因为他很有窍门令病人相信他们能化想象力为具体现实;跟他较量我可得了不少乐趣。
签字出来后,我想在新英格兰乡下或某个沉睡的小镇(榆树林、白色教堂)找一处地方,整整一夏天都能靠收集来的一箱笔记专心致志于我的研究工作,并且还可以在附近湖泊里洗澡。我的工作又提起了我的兴趣——我指的是我的学术努力;而对叔叔逝后留下的香水事业绝少过问,我的利润分享已被削减到最小数。
他从前的一位雇员,是某显赫家族的后裔,建议我到他的穷亲戚麦库先生家住上数月,麦库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妻子想把他们已故姨妈住过的二楼出租出去。他说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还是婴儿,一个十二岁了,有座美丽的花园,不远处还有个湖,我说,听起来相当不错。
我和他们通了信,他们满意我的良好习惯;于是,在火车上过了充满幻想的一夜,想象着我将施予那象迷一样的性感少女的全部细节,用法国方式训练她,用亨伯特方式抚爱她。我提着那只贵重的提包从车上下来,玩具般的小车站上无人接候,打电话去也没人接;最后,一位心神不安、浑身湿透了的麦库出现在绿紫色的拉姆斯代尔唯一一家旅店门口,带来消息,说他的房子刚刚烧毁了——很可能,起因于整夜在我心头蔓延的熊熊大火。他说,他家人乘飞机去他的农场了,小汽车也正用着;不过他妻子有位朋友,一个高贵的人,住在草坪街342号的黑兹夫人,愿意留我宿下。住在黑兹夫人对面的一位妇人把她的轿车借给了麦库,一辆非常漂亮的老式方顶轿车,司机是个快乐的黑人。现在,我到这里来的唯一意义已经彻底丧失,上边说的安排听起来就很荒谬。是啊,他的住宅会完全修复的,那又怎么样?他不是充分保证了吗?我气愤、失望、感到无聊,但作为有礼的欧洲人,我不能拒绝被那辆丧车送到草坪街去,不然,我觉得麦库就会想出更绝妙的方法抛掉我。看着他急匆匆地跑走了,我的司机摇摇头轻轻地笑起来。汽车开动时,我对自己发誓,任何情况下也绝不梦想呆在拉姆斯代尔,我要在当天就飞到百慕大或巴哈马或布勒兹。五光十色的海岸上可能遇到的鲜香过去一直在我脊骨上缓缓流动,而麦库的表亲实际上已经用他原本好心好意、但现在却是完全无意义的建议,强硬地扭转了我一系列的思绪。
说到强硬的转弯:当我们驶上草坪街时差点撞上一条爱管闲事的乡下狗(就是那种睡着懒觉等小汽车的)。不远处,黑兹住宅,一副自构架的惨状出现了,又脏又旧,与其说白色,不如说是灰色——那种地方,你知道,得在浴盆水龙头上加一条橡皮管以代替莲蓬喷头。我塞些小费给司机,希望他能立刻悄悄地按原路把我带回旅店,让我拿上行李;但他却只是穿向马路的另一边,朝一位站在阳台上招呼他的老太太驶去。我还能怎么办?我按了门铃。
一名黑女仆把我领进去——丢下我自己坐在席垫上,她又跑回厨房,好象有什么不该糊的东西糊了。
前厅装饰着门铃,装饰着一位有墨西哥商人血缘的白眼睛呆傻家伙,他正是这班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中一个虽琐碎但还可爱的人,另外还装饰着凡.高的《阿尔风景》。右边一扇门半掩着,能瞥见里面是卧室,角柜里摆着更多的墨西哥废品,一只镶条纹的沙发立在墙边,走廊尽头有楼梯,正当我站在那儿擦着额角(只在这时我才发觉屋外是多么热),四处寻视,看见了一只放在橡木箱上的灰色旧网球,黑兹夫人的女低音突然从上边降落,她靠在栏杆上优美地问道:〃是亨伯特先生吗?〃接着,一丝烟灰也跟着落了下来。之后,那妇人自己——凉鞋、栗色宽松裤、银黄色衬衣、近似方形的脸,就以这样的秩序——款款走下楼,她的食指仍然弹着烟卷。
我觉得我最好直截了当地描述她,可以清晰易解。可怜的妇人三十五六了,她的额头很有光泽,眉毛剔过,五官端正但不动人,或许能形容为玛雷娜的一次不稳固分解。她拍着铜褐色的卷发,领我走进客厅,我们聊了一会麦库的火灾,以及在拉姆斯代尔居住的特权。她那特别大的海绿色眼睛非常有意思地在你周身上下移动,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你的目光。她的笑只是一条眉毛挑逗地猛跳一下;一边说着,时面在沙发里伸展一下身体,时而朝三个烟灰缸和身旁的炉围(那上面放着一只褐色苹果核)冲击,而后又落座,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下。很显然她是那类妇女,她们经过修饰的谈吐颇能代表一家图书俱乐部或桥牌俱乐部或任何古板聚会的风格,却永远不能反映她们的灵魂;一批毫无幽默感的妇人;在内心深处对客厅交谈的所有主题完全漠然,但对这种谈话的形式却甚为讲究。透过太阳光下的玻璃纸,她的失意一目了然。我非常明白无论多么偶然我成了她的房客,对于我,她会有步骤、有头有尾地做完能对宿客做的一切;我于是就又会陷入一张肮脏交易的网,这些我知道得很。
但我住下来是毫无问题的。对那种每张椅子上都堆着邋遢杂志的家务事,以及在所谓〃实用的现代家俱〃喜剧与老朽的摇椅、患佝偻病的台灯桌上摆着摇摇欲坠的台灯的悲剧之间发生的可怕的杂交现象,我不能感到快乐。我被领上楼,向左——进入〃我的〃房间。我透过绝对抵触的心情审视它;但我确实在〃我〃的床上方辨认出勒内。普里耐的〃克莱采奏鸣曲〃。她管那间佣人的屋子叫〃小工作室〃!当我试图慎重地考虑我狡黠的女主人对我的食宿收取那么低的价钱,是多么荒唐且更显不吉利,我对自己坚定地说,还是让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但是,旧时代的彬彬有礼强迫我继续这场痛苦的考验。
我们穿过楼梯顶端的走廊,来到住宅的右半部(〃我和洛的房间〃在那儿——洛被推测为那位女仆);当投宿者情人,一个非常苛刻的人,被准许预先查看了唯一的一间浴室后,便根本不能隐瞒他的颤栗了,那是个很小的长方形,就在我和〃洛的〃卧室之间,有一团柔软、湿德源的东西悬在用途不明的马桶上方(桶里有一根头发弯成的问号);不出所料桶里还有橡皮蛇似的一团发卷,以及桶的附属品——一个紫红色棉垫羞答答罩在马桶盖上。
〃我看出你没什么太好的印象,〃妇人说着,让她的手在〃我的袖上停留片刻:她把一种冰凉的大胆——我所谓〃均衡的泛滥——和一种羞怯、一种忧伤结合起来,后者决定了她遣词造句的脱俗,就象一位教授作〃演讲〃时的语调那么不同自然。〃这个家称不上干净,我承认,〃注定要失败的可怜人继续道:〃但我向你保证(她看着我的嘴唇),你会非常舒服的,非常舒服,千真万确,让我带你去花园吧(最后一宇更响亮,带着一种迷人的震颤)〃。
我没奈何又跟她下了楼;而后穿过大厅末端的厨房,来到住宅的右半部——这部分也是用饭间和走廊的所在(〃我〃房下的那个左半边没什么,只有个汽车间。)厨房里,那个脏乎乎的年轻女黑仆,一边从通向后门廊的门把上取下她黑得发亮的提包,一边说:〃我这就走了,黑兹夫人。〃可以,露易丝,〃黑兹夫人叹口气答道,〃星期五我会和你解决的。〃
我们又走过一间很小的食品室,进到用饭间,它和我们已经称赞过的走廊是平行的。我看见地板上有双白袜子。黑兹夫人吐噜了一句道歉的话,立刻弯下身,随手把它扔进边柜里,我们草草地检查了中间摆着一只果盘的红木餐桌,果盘里只有一个还发着亮光的李子核。我在兜里摸索着火车时刻表,偷偷掏出来,以最快的速度找出了一趟车。穿过用饭间,我仍跟在黑兹夫人身后,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绿叶——〃游廊,〃我的指引者唱道,然后,未经半点提示,一排蓝色的海浪便从我心底涌起,在太阳沐浴的一块草垫上,半裸着,跪着,以膝盖为轴转过身,我的〃里维埃拉〃之恋正透过墨镜向我窥视。
那是…个同样的孩子——同样的少女,同样蜂蜜样的肩膀,同样象绸子一样柔嫩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一条圆点花纹头巾系在她胸间,她的胸躲开了我苍老而贪婪的双眼,却躲不开我年轻回忆的注视,那对青春期的乳房我曾经在…个不朽的日子抚摸过。仿佛我是神语中小公主们(失踪了,遭绑架了,被发现时穿着吉普赛人的破衣烂衫,她赤裸的身体在衣服下对着国王和他的猎犬微笑)的保护人,我发现了她胁上一个微小的沉褐色黑痣。带着敬畏和喜悦(国王乞求享受,喇叭嘟嘟响着,保护人酩酊大醉),我又看见她可爱的绷紧的小腹。我的嘴刚刚还停在上面;还有那不成熟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