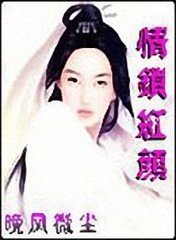机关红颜-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入土为安弃滚滚红尘而去
备极哀荣留万千遗憾在心
横批是:
老天杀人!
《机关红颜》42(1)
徐有福补了乔正年科长的缺,作为副县级后备干部被补报到市委组织部。不久,市里的任职文件下发,徐有福任副局长。因这次提拔干部各部门和县里竞争很激烈,局里另两位科长没能按原来的设想推荐到外部门或县里使用,经过一番争取,一个任了局里的纪检组长,一个任工会主席。
局里的领导班子由七人组成:局长,方副局长,张副局长,王副局长,徐有福副局长,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市政府设立会计核算中心,取消了市级各部门内设的小金库,每个局不再设财务科,只设一个报账员,在会计核算中心统一报账。
局里的财务科取消后,许小娇调到统计科任科长;吴小娇接徐有福任扶贫科科长;刘芒果“归队”,任业务三科科长;赵勤奋任宣传科科长;业务一科、二科原来的两个副科长“拾阶而上”,担任科长。
在局长分工里,徐有福副局长分管统计科、扶贫科、宣传科。
徐有福任副主任科员时,大家称呼他直呼其名:徐有福。那时赵勤奋总是差遣他:“徐有福,你过来一下!”“徐有福,去将这个材料打印一下!”“徐有福,怎么搞的?到处找不着你!”赵勤奋总是用居高临下有时甚至是盛气凌人的口气命令他,语气斩截。那时局长称呼他也有几种方式。“徐有福,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局长以这种口吻说话时,说明他不太高兴。徐有福一边往局长办公室跑一边还在寻思:自己又办错什么事了?“有福,到我这儿来一下。”局长以这种口气说话时,说明他比较高兴。徐有福往局长办公室走时,也便没有多少诚恐诚惶。
徐有福担任科长后,赵勤奋对他的称呼有两种。一种是如果县上的下级部门来了,到办公室请示某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好是徐有福职权范围内的事,赵勤奋就会和蔼地对来人说:“这个事情请你们去请示徐科长。”然后以手指着徐有福说,“这位就是徐科长。”若徐有福不在办公室,过一会儿徐有福回到办公室时,赵勤奋就会对他说:“有福,刚才县里的同志找你,我将你的手机号码留给他们了,他们下午上班后再来。”赵勤奋当面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直呼“徐有福”了。有时徐有福不在办公室,赵勤奋与许小娇、吴小娇议论起徐有福,还会说“徐有福如何如何”,可若徐有福突然进门,他马上会说:“哟,徐科长驾到,”或者表示亲切:“有福回来了。”此时若徐有福、赵勤奋、许小娇、吴小娇几个扎堆说话,哪怕说很长时间,赵勤奋也不会提一次“徐有福”,不是称“徐科长”,便是亲昵地称作“有福”。有福如何,有福怎样,语气十分亲热。而且往往以疑问句居多——有福你说是不是这样?
局长对徐有福的称呼也在变化。若碰上科里其他人,局长会说,叫徐科长来一下;或者叫有福来一下。局长无论用哪种称呼,语气一般是温和的,而不是疾言厉色的。
徐有福任副局长后,他的名字似乎从此被人们遗忘了。比他职位低的人都称呼他为“徐局长”,赵勤奋更是将“徐局长”一天到晚挂在嘴上。赵勤奋在“徐局长”面前表现出了完全的自我雌伏和自我奴媚。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认为,动物相争,认输称臣者往往会表现出如下姿态:一、将自己的身体缩小以使对方息怒;二、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朝向进攻者以此承认自己的失败;三、做幼崽乞食状以向强者认输;四、请求胜利者允许替其整饬毛发以表示臣服——原来赵勤奋这一系列行为和举动,是为徐有福“整饬毛发以表示臣服”呢!
局里其他的副局长也客气地称呼徐有福为“徐局长”,包括老资格的张副局长和王副局长也这样称呼他。你若冷不丁问局里的同志,张副局长与王副局长叫什么名字,还真有人会想不起来,因为很多年轻同志从调进局里工作那一天起,就一直称呼张副局长为“张局长”,王副局长为“王局长”。张副局长的名字叫张启高,王副局长的名字叫王宏礼。包括徐有福,若冷不丁听到有人叫“张启高”或“王宏礼”,也得想一想才能与两位副局长对上号。而现在,徐有福也成为与张局长、王局长一样的人!一些新调进局里的年轻同志若冷不丁听到“徐有福”三个字,也许也得想一想才能与“徐局长”对上号呢!
徐有福从此成为徐局长。只有老局长有时会慈祥地向他招招手说:“有福,你来一下。”
徐有福的名字“丢失”了,尊严却找到了。
人生,不就是一个寻找“尊严”的过程吗?
国与国之间也一样,往往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干戈,就是因为牵涉到同样的问题。
人从一生下来,就在不屈不挠地寻找尊严。上学时要考一个好分数,上大学时考一所好大学,工作后找一个好单位,进单位后一直由干事到科长,科长到局长,直至市长、省长。
如果你能干到一个市长、市委书记,那你的名字除了你爸你妈你妻子,再很少有人随便直呼其名。即使在背后,人们也不会轻易称呼你的名字。比如市委书记袁亦民。人们当面当然是叫他袁书记。即使几个人在背后一个毫不相干的场合说话,也会口口声声称袁书记。甲:袁书记上午的话讲得有水平;乙:袁书记不仅有水平,讲话还有针对性;丙:袁书记真是一个有水平的领导干部(相当于说:这个女人真漂亮)。此时若不合时宜进来一个“丁”,大大咧咧地说:袁亦民老得头上都不长毛了;袁亦民快退休了;袁亦民是个没文化的老粗干部。“丁”说第一句话时,甲、乙、丙会面面相觑;“丁”说第二句话时,甲、乙、丙会同时向周围张望(不会有人以为我们在背后议论袁书记吧);“丁”说第三句话时,闭着眼睛打了个喷嚏,待他睁开眼抬起头时,甲、乙、丙早不见了。
《机关红颜》42(2)
即使在背后,也没人敢将一个市委书记的名字随便呼来唤去。
而徐有福离这一步,还很遥远!
可徐有福已尝到了甜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当将母乳叼在嘴里吸入第一口甘甜的汁液后,他就再也不愿丢开了。如果你用塑料奶嘴装一瓶牛奶塞进他的小嘴里,他就会抗议似的哇哇直哭。当了副局长以后的徐有福,如同这个小孩子叼住了母乳,而那个副主任科员则是仿制的塑料奶嘴,徐有福再也不愿噙它了。
徐有福从此可以参加市里召开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可以看到上面发到这个级别的文件;可以在下面呈报上来的文件上签:“准办”、“暂缓”、“退回”等等字样。还可以写上“我意请某某同志牵头,去解决此问题”、“此议不妥,应调查研究后重新拿出符合实际且操作性较强的方案”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下县里转一圈,县里同志会说,请徐有福局长检查指导;请徐局长作指示等等。出席饭局,如果没有职位更高的领导,即使他最后一个到,最中间那个位子也总是给他留着。而过去,若他迟到后,别人便会不耐烦地扫视他,然后随便加一把椅子,插在服务员上菜的地方。结果不是上菜时不小心将汤汁洒他身上了,就是因太拥挤将左邻右舍的筷子碰掉了,从而招来讨厌的目光。
而且每上来一道菜,摆在自己眼前却不能动筷子,早有人殷勤地转到“正席”那儿去了。待别人吃过后再转回来,只剩下一些残汤剩菜了。
那时候的徐有福,在人生早已排好的队列里,是一个插队者,不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逃难者,伸出碗去别人给你施舍一勺粥就不错了,怎可奢望坐上宴会的正席!
而现在的徐有福,终于由一个缩头缩脑的插队者,变为正式队列中的一员,虽然还没有排到最前边。
即使在与白玉做爱时,他也能感觉到这个级别和职位带给他的好处。过去他只是一个“徐有福”时,趴在这位总经理上面,总觉得有点儿“不对称”,或者说他们无法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白总的腰长,他的腰短。而现在成为“徐局长”后,他在心理上已觉得与白总的“腰”一般长了。两个腰一般长的人做爱,就像推着一辆过去农业学大寨时拉土的那种平板车,由于手推的柄一般长,即使上坡的时候,也可同时着力,鼓一鼓气就推上去了。可若两边长短不一,你再鼓气,也无法将那车土推上去。
如果有一天徐有福成为徐市长,那就是他的腰长,白总的腰短了。做爱时白总会完全按他的要求来。白总的腰会一再屈就他的腰。而无论他怎样做,做得到位不到位,白总都会说:徐市长,我太爱你了!我太舒服了!我想咬你一口!
《机关红颜》43(1)
省上的对口主管部门要召开一个“统计工作研讨会”,要求市局来一个主管副局长和统计科长。
徐有福和许小娇去参加会议。
本来他们准备坐飞机去。临走的前一天,许小娇突然对徐有福讲,她想坐汽车去。
坐汽车也有几种坐法。坐单位的桑塔纳,当然也可以。局长主动对徐有福说,有福,你这次开会,带局里车去吧。可徐有福却不想带单位的车。那几天局长正在市里的一所医院推拿按摩,每天要去两次,晚上八点还有一次,局里的车跑来跑去接送。局里就这一辆车,若自己将车带走,局长按摩时就没有车接送,没有车接送局长就得“打的”,“打的”总没有坐自己的车舒服。桑塔纳车宽敞,坐套洗得干干净净,而本市的“的士”大都是奥拓,夏利都很少见。奥拓车那样小,将局长塞进奥拓车里,就像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塞进一个狭小的衣柜里,不是这儿碰着就是那儿碰着了。碰着心里就会不痛快。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意见往往是因一些小事而起。若将局长脚夹了或者胳膊碰疼了,局长就会在心里埋怨:这个徐有福!要不是他将车带走……而为这样一件事情惹局长不高兴,徐有福觉得没有一点必要。若按赵勤奋那个蠢货的说法,这才是典型的因小失大!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若带局里车去,局里的司机也得去。徐有福与许小娇去开会,不想再多一个“第三者”。虽然徐有福并不是想和许小娇怎么样,但他总觉得多一个司机有点儿别扭。就像两个人正打乒乓球,突然过来一个人夺过你的球拍打一下,再夺过他的球拍打一下,弄得双方都不舒服。或者一男一女两个好朋友正在谈文学,当时在一间干净雅致的房子里,停电了,俩人点一支蜡烛谈,即所谓“秉烛夜谈”。而且谈的是《红楼梦》,从晴雯撕扇麝月洗澡金钏投井一直到宝玉哭灵。双方都为对方的观点和新颖的见解而吸引,并互相被对方所触动,迸溅出更新颖的见解来。正说得入港,进来一个热衷于谈论大款发迹史的人,坐在俩人对面大谈某某十年前还是个流浪汉,现在却成了市里有名的亿万富翁;过去骑一辆除了铃不响浑身都响的破自行车,现在却开着市里惟一的一辆奔驰。某某开了三个大酒店,把酒店里有点儿姿色的女孩都睡遍了,等等。宛若佛头着粪,大煞风景,此时两个谈《红楼梦》的人会大倒胃口,只好缄口不言。而这人若再拿一个手电筒,好奇地将这个脸上照一照,再将那个脸上照一照,那简直会让人有一种羞辱的感觉。如果带一个司机去,也许就是这个拿手电筒的人——徐有福无法与许小娇在幽暗的烛光下谈《红楼梦》。
当然这个原因徐有福只能在心里想,他不会给任何人讲出来。
再就是开白玉的帕萨特去。与许小娇开会,徐有福不愿开白玉的车。白玉的车跟着自己,就仿佛白玉也跟着自己。如果你和你太太出门旅游,你愿不愿意让一个死皮赖脸缠着你的情人或小姐跟着你?当然许小娇不是徐有福的太太,可在徐有福的心目中,这个小蹄子却比他的太太重要一万倍!
许小娇说,若嫌他的赛欧小,就开她老公的奥迪去。开许小娇老公的车,徐有福也有点儿不愿意,好像许小娇老公一直跟着他们。若许小娇老公拿个手电筒在他们这个脸上照一下,那个脸上照一下,那比司机照来照去还令人尴尬,简直尴尬死了。
那就只能开赛欧去了,小是小一点儿,不过只有两个人。况且小和大永远是相对的。徐有福对许小娇说,你说紫雪市大还是中国大?如果我说紫雪市比中国大,你肯定说我不是弱智就是脑子进水了。而我以为也许紫雪市就是比中国大!比如我的一个同学在紫雪市,但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你说紫雪市大不大?可有一天,我却突然在上海东方明珠塔三百五十米高的太空舱碰到同学了。我刚由上海到北京,在北京动物园看海豚表演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走进来坐在我身边。看完表演一扭头,哈,又碰上那同学了!你说中国小不小?这就是紫雪大而中国小。
徐有福说这番话时,许小娇已开着那辆赛欧驶出了紫雪城。她扭头冲徐有福嫣然一笑说:“我发现你越来越会说话了!你如果一直和我这样说话,也许有一天,我会喜欢你的。”
“不会是四十年后再喜欢我吧?像赵勤奋以前给你说的那样,到那时我耳聋了怎么办?你说得再好听,我也听不见了。”徐有福有点伤感地叹了口气,随即他扭头瞥瞥许小娇,又补充一句:“不过我宁肯失聪,也不愿失明!”
“我现在都有点儿纳闷,那时你怎么像个闷葫芦似的,笨得像块石头,看着人都替你急。”许小娇说这个“人”的时候,有点儿撒娇的味道,仿佛他俩是一对十分亲密的朋友。
许小娇的脸特别白,却一点儿也不干涩,有一种诱人的水气。就像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富士苹果咬开第一口的那种感觉。
徐有福在心里想:这个小蹄子即使是个妖精,他也心甘情愿做个唐僧,跟上她迷迷糊糊到这儿,到那儿。哪怕最后将他捆起来吊到房梁上,他也会晃悠晃悠觉得舒服极了。
省里的统计工作研讨会在郊区的一个宾馆召开。这个宾馆隶属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