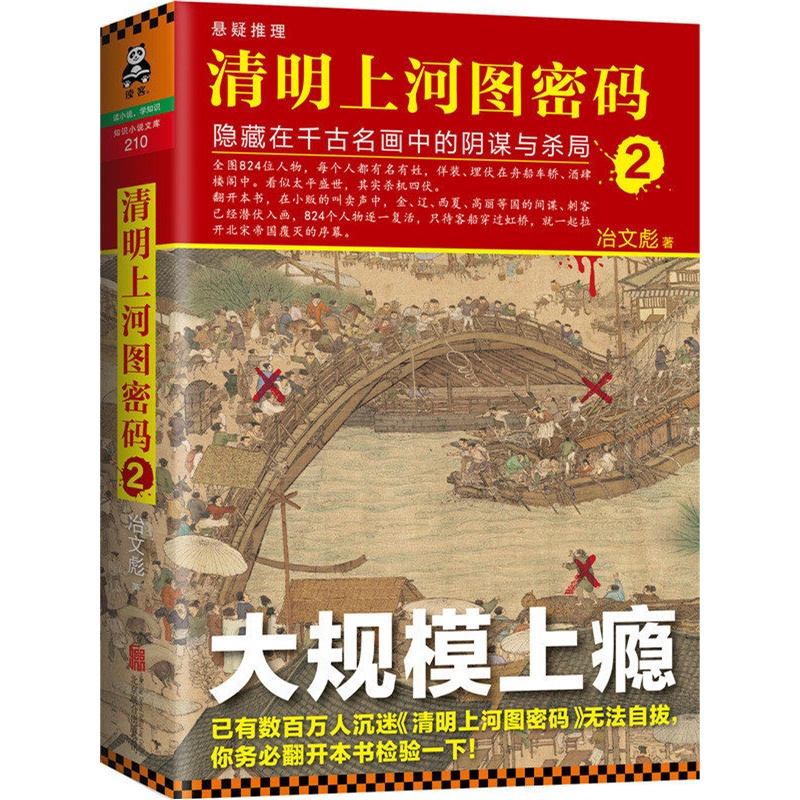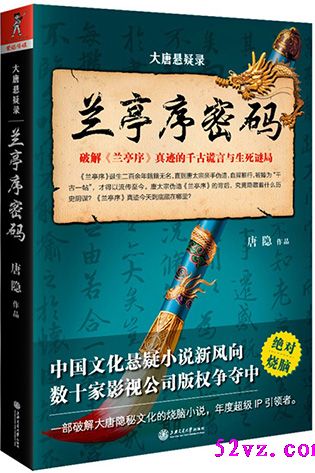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第6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楷也笑道:“正要找人去给你说这事,那鲁膀子果然有鬼。”
“哈哈,他招了?”
“逃了。”
“嗯?没逮到?”
“都是你提前透了风,他心里有鬼,还有不逃的?”
“哈哈,我不吃你开封府的饭,替你找出真凶,雪了冤案,已经是大功德了。至于捉不捉得到凶手,那是你们自家的差事。”
“我看你是有意透风,让他逃走,又逗我们跑腿。不过还是要多谢你。我今日还有许多事要办,改日再喝酒。”
赵不弃笑着道别,驱马出了城。
来到烂柯寺,他下了马,将马拴在寺门边的木柱上。一回头,见寺里那个爱吟诗弄句的小和尚弈心走了出来。
赵不弃很喜爱这个小和尚,一向不叫他的僧名,只戏称他为唐朝诗僧拾得:“小拾得,最近有什么好诗没有,吟两首来听听?”
弈心双手合十,低眉道:“诗心爱秋霜,春风随花无。”
赵不弃笑着随口对了句:“和尚敲木鱼,秃头对月明。”
弈心听了,也笑起来。白净的脸配着雪白的牙,笑容异常淳朴悦目。
赵不弃这才道:“小拾得,我今天来是要问一件事。就是正月十五,美人变丑女那件怪事。那天你在寺里吗?”
弈心收住笑:“清早奉师命,进城捎书忙。”
“进城送信去了?那天寺里只有你师父一人?”
弈心点了点头。
“今天你师父可在?我进去瞧瞧。”
“松绿禅房静,窗明师心空。”
“你师父在坐禅?”赵不弃抬腿进了寺门,弈心跟在后面。
寺里面十分清寂,四下里也清扫得极为整洁,不见片叶棵草。庭中央佛堂前那株老梅树新叶鲜绿,迎空舒展,相比于花开时,另有一番蓬蓬生机。
赵不弃照何涣所言,先走到右廊,墙上那些壁画他以前也曾看过。他站在那里面朝壁画,左眼余光正好扫到梅树和佛堂。当时阿慈和冷缃站在梅树下,自然也能看到。他又走到左廊,和右边一样,看壁画时,眼睛余光也能看到梅树和佛堂。
何涣和朱阁在这边欣赏壁画时,阿慈和冷缃绕着梅树追逐嬉闹,虽然当时梅树开满了花,但花枝间仍有间隙,就算人在梅树那边,也照样看得见。阿慈独自走进佛堂,据何涣讲,她并没有往左右两边走,而是直接在佛像前跪拜。这边廊基高出地面一尺,因此从这里望去,就算阿慈跪在蒲团上,也照样看得清清楚楚。
唯一遮挡了视线的是梅树后面那个香炉。
当时冷缃的裙子被香炉角勾住,阿慈过去蹲下身子帮她理开,只有这一小会儿,何涣他们在这边看不到阿慈。
难道那香炉有古怪?
赵不弃走下左廊,来到梅树后面的香炉跟前。那香炉原是一只大铁箱,大约有五尺长,三尺宽,四尺高,底下是四只五寸高的铁脚。顶上的箱盖被卸掉了,常年日晒雨淋,箱子外壁厚厚一层铁锈。箱子里积满了香灰,离顶沿只有五寸左右。香灰里满是细竹香杆残烬,中央插着三炷香,已经燃了一半,因没有风,香烟袅袅直上。
赵不弃从梅树上折了一根细长枝,插进香灰之中。香灰积压得太久,有些紧实,他双手用力,才将梅枝插了下去,一直插到底,近四尺深,看来是装满的。
这铁香炉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再说阿慈是进了佛堂之后才变的身。
赵不弃又走进佛堂,佛堂很小,只有门两边各一扇花格窗,光线有些昏暗。迈过门槛进去后,走两步地上便是三个蒲团,阿慈当时跪在中间这个蒲团上。蒲团前方是一张香案,底下空着,藏了人一眼就能看到。香案后则是一尊佛像。
赵不弃望向两边,左右贴墙各有一张长木台子,上面各供着一排一尺多高的罗汉,木台下面都空着。
赵不弃又绕到佛像左侧,不像其他大些的寺庙,这间佛堂并没有后门,佛像紧贴着后墙。
要换身,那个丑女必定要预先藏在这里,不过,她只要走到中间蒲团位置,何涣在外面就能看见。就算何涣没有发现,阿慈若猛地见一个人从暗处走过来,也会吃惊,甚至惊叫。但据何涣说,阿慈进门后并没有任何异常,只是跪在蒲团上,而且刚跪下才拜了一拜就昏倒了。何涣看到后,立即奔了过来,双眼一直望着阿慈,并没有见到其他人影。
最要紧的是:阿慈去了哪里?
何涣和朱阁夫妻,还有乌鹭住持发现阿慈变身后,立即搜了佛堂,并没有找到阿慈,何况这小小佛堂也没有地方能藏人。
赵不弃低头盯着那只蒲团,难道在底下?他忙弯腰挪开蒲团,下面是大青石方砖,接缝严密,看不到撬开移动的迹象,不可能有地窖。他又查看了其他两个蒲团和香案下面,都一样,不会有秘道。就算有秘道,也难在何涣眼底换人。
这桩怪事果然有趣,非常之有趣。
赵不弃不由得又笑起来。
最近京城凶案频发,案牍堆积,葛鲜的案子轮号待审,至少要等几天。
但他的岳丈郑居中听到消息,当天就使人催问,开封府推官第二天一早便提前审问。审问时,对葛鲜也十分客气。葛鲜只讲了一条:事发那天中午他去了柳风院,当晚并没有回家。柳风院的柳妈妈三人是见证。
推官便遣了个小吏去柳风院查问,小吏回来禀告属实,推官便释放了葛鲜。
葛鲜回到鱼儿巷,邻居见到,都来问讯,葛鲜勉强应付着,走到自家门前,门虚掩着,他犹豫了片刻,才推门进去,一眼就看到父亲的尸体,摆放在堂屋地上,下面铺了张席子,上面蒙着块布单。
他站在院子里,不敢进去,呆立了半晌,似乎听到父亲慈声唤自己的名字,眼泪顿时涌了出来,哽咽了一阵,才忽然哭出声,腿一软,跪倒在地上。
他一边哭,一边跪爬到父亲尸体旁,手触到父亲尸身,已经僵冷,心里越发痛楚,放声号啕起来,哭得连肝脏都快扯出。
母亲死得早,父亲一人辛苦将他抚养成人,从没有跟他说过一句重话,事事都以他为先。唯一不足是家境穷寒,让他时常有些自惭。但想着只要勤力读书,总会赢得富贵,改换门庭。而今终于一步登天,父亲却……和枢密院郑居中的小女定亲后,父亲却让他重重尝到穷贱之耻。
那夜,他本想杀掉丁旦,却被丁旦躲开。他从没动过武,就算继续追杀,也未必杀得掉丁旦。而且,就算杀了丁旦,他自己也难逃罪责。
他慌望向父亲,父亲也惊慌无比,他心中忽然闪出前日在岳父郑居中家的遭遇——那天郑居中邀他父子去府上赴宴。父亲特地选了件最好的衣裳穿戴齐整,可到了郑府,一看门吏都衣着鲜明,顿时衬得他们父子如同乞丐一般。父亲从没进过这等贵邸,抬腿要进门,险些被高门槛绊倒。进了门,晕头晕脑,连脚都不会使唤了。等见了郑居中,舌头打结,说出些不着三四的浑话。他在一边,羞得恨不得死掉。等茶端上来,那茶盏乌黑幽亮,盏壁上一丝丝细白毫纹,他知道那是兔毫盏,他家全部家产也抵不上这只茶盏。然而父亲才喝了一口,猛地呛了一下,手一颤,那只茶盏跌到地上,顿时摔碎了。郑居中虽然并没介意,立即命人又上了一盏,他却羞恨无比,恨不得杀了父亲……他看了一眼惊慌缩到墙边的丁旦,丁旦眼珠不住乱转,正在急想对策,再不能耽搁!他又望了父亲一眼,父亲伸出那双枯瘦老手,似是要来阻拦,那张面孔苍老而卑懦,一刹那,他的心底忽然闪出一个急念。
杀掉父亲,嫁祸给丁旦!
他悲唤一声:“爹,恕孩儿不孝——”
说着,他心一横,一刀刺向父亲……
父亲本已年老,又全无防备,那刀深刺进了胸口。他握着刀柄,见父亲瞪着自己,满眼惊异,他顿时呆住。见父亲仰面倒下,他才惊慌起来,扑通跪倒在父亲身侧,又慌又怕,却哭不出来,只有连声叫着:“爹!爹!”
父亲大口喘息着,目光虽然仍有些惊异,但很快似乎就明白过来,望着他,竟没有怨责,反倒涌出慈爱赞许之意。
他越发内疚,哽咽起来:“爹,我……”
半晌,父亲拼力说道:“鲜儿……好……好好珍惜前……”
父亲也许要说“前程”,“程”字还没出口,就咳了起来,咳出几大口血来,血喷了葛鲜一身。父亲又喘息了一阵,随后双眼一翻,面部僵住,再不动了,只有嘴还一直张着。
他轻轻摇了摇父亲,低声唤道:“爹……爹!”
父亲纹丝不动,他这才意识到父亲死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慌乱、悔疚、惧怕、悲痛一起涌来,全身却像化了石一般,顿时僵住。
这时,跌倒在墙边的丁旦发出些悉率声,葛鲜听到,茫然扭头,见丁旦满眼惊惧,身子往后缩着,缩到墙根想爬起来,但看到葛鲜的目光,他顿时停住,不敢再动。
葛鲜也才想起自己的初衷,他又低头看了看父亲,伸手将插在父亲胸口的那把刀拔了出来,而后站起身,扭头又看了一眼丁旦,丁旦立时打了个哆嗦,慌忙把身子拼命往后挤。葛鲜并不理他,抓起桌上那锭银铤,转身回到自己房中,脱下溅了血的衣服,换了件干净的,将那把刀卷进血衣中。
随后,他急步走到后院,轻轻开了后门,先听了听,外面毫无动静,这才悄悄出去,带好门,穿过后巷来到汴河北街。夜已经很深,家家户户都闭着门,只有一些酒坊还开着,并没有谁看到他。
快到虹桥时,他捡了块石头包在血衣里,上桥后,将血衣和刀丢进河里,而后快步进了城,来到柳风院。柳风院是个小妓馆,只有三间房一个小院。老娘柳妈妈和一个小丫头护侍着柳艾艾。葛鲜只因她家价低,所以才偶尔来坐坐。自从中了礼部省试头名后,开始顾惜身份,便不再来了,尤其是被枢密院郑居中相中女婿后,就更不肯沾足这种地方。
那柳妈妈开门见是葛鲜,惊喜之余,又有些为难,低声道:“葛公子?许久不见啦,今晚怎么得工夫想起我家艾艾了?不过啊,真真不巧,今晚已经有位恩客,唉,早知道葛公子——”
葛鲜忙打断她:“我只是来借住一宿,不见艾艾也成。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妈妈。”
“那快请进!”柳妈妈把葛鲜让到侧房,忙着要去张罗酒菜。
葛鲜忙止住她,从怀里取出那锭银铤:“我遭无赖陷害,平白惹上些冤枉,恐怕会上公堂。求妈妈替我做个见证,就说我从今天中午就来了这里。”
那天葛鲜一直在家,岳丈郑居中说要看看他的诗文,他便在书房里点检整理,整天没有出门,邻居也没有见到过他。
柳妈妈眼睛转了几圈,问道:“只要这句话?”
“嗯。不过艾艾和丫头也得说好,不要错乱了。”
“那好。只要葛公子往后不要把我们娘俩随意丢在脑后就成。”
“妈妈放心,我葛鲜不是负义忘恩之人。”
当晚他就想好,先脱罪,暂不提丁旦,过几天等机会合适,再设法将罪责引到丁旦身上,彻底断绝后患。从此安然踏上青云路……然而,此刻望着地上父亲的尸体,他心底生出无限痛悔,如同一只铁爪要将他的心揪扯出来。
他不知道哭了多久,眼泪已经哭干,嗓子也已哭哑,膝盖一阵阵酸痛。他扶着门框站起身,慢慢挪到椅子边费力坐下。喉咙干渴,他茫然伸手,抓起桌上的茶盏,盏里还有冷茶,他便一口喝尽。
放下杯子,垂头呆坐了片刻,忽觉喉咙干涩,身子发麻,气促心燥,他抬头望了一眼桌上的空杯,猛然想起:茶水有毒!
父亲那晚想要毒死丁旦,丁旦却没有喝这茶。他刺死父亲,从后门出去,丁旦恐怕随后也逃走了。第二天官府来查案,并没有将桌上的毒茶倒掉,这三杯毒茶一直摆在这里……毒性发作,一阵痉挛,葛鲜一头栽倒在地上,浑身抽搐,扭作一团,呼吸渐渐窒塞,他扭头望向父亲的尸体,使尽最后气力,嘶叫了一声:爹……赵不弃在烂柯寺追查阿慈变身的踪迹,但时隔已经快两个月,院子、佛堂都没有找出什么可疑之处。
他又绕到侧边去看,右边是一间厨房、一间杂物间和一间茅厕,并没有什么。左边一排有四间房子,乌鹭师徒各住一间,另有两间是客房。赵不弃透过窗缝一间间望过去,其中一间客房里,有个老僧正在床上闭目坐禅,没见过,可能是游方寄住的和尚。乌鹭则在自己房中坐禅,另两间则空着。至于后院,是一小片松柏林,三张石桌,清扫得干干净净,清幽无人。
赵不弃见找不出什么,就转身回到前院,小和尚弈心一直跟着他,见他要走,便合十问道:“袖风飒然至,问君何所得?”
“逐云飘兮去,片尘不沾身。”赵不弃随口答了句,笑着离开了。
他先骑了马沿汴河北街走到蓝婆家附近,见那个换了便服的道士张太羽正在门前蹲下身子给儿子穿鞋,小儿乖乖站着,蓝婆则端着个木盆出来倒水。看那情形,一家三代似乎十分和乐。赵不弃又望向斜对面,前几天那个武夫模样的大鼻头竟然仍蹲在大树根,不时往蓝婆家偷觑。
他竟还没有追到丁旦?
看那模样,十分疲顿,也怪可怜的,赵不弃笑着摇摇头,心想:阿慈变身那天,还有朱阁、冷缃夫妇同行,他们也许会记得些什么。但这对夫妇他并不认识,何涣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里。蓝婆应该知道,不过又不好再去惊扰她。
他一扭头看到旁边汪家茶食店,便驱马过去,见店里小伙计正好走出来,便下马问道:“小哥,向你打问件事。常去对面蓝婆家的朱阁夫妇,你可知道?”
“怎么不知道?朱阁家也在这东郊,他爹是打渔的。”
“他家在哪里?”
“他家原先在大河湾那边,不过是个穷寒小户。朱阁才考上府学,又撞上好运,投奔到小小蔡家做了门客,得赏了城里一院宅子,听说是在第二甜水巷。”
“小小蔡?可是蔡太师的长孙蔡行?”
“可不是?”
“多谢!”
赵不弃上马向城里行去,到了第二甜水巷,一打问,朱阁果然住在这里,街北头那个朱漆门楼的宅子就是。
赵不弃行到那门前,下了马抬手叩门,一个男仆开了门。赵不弃想,蔡行如今是殿中监,查视执政,天子面前宠信直逼其祖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