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正在迷情中-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受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木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第二十六复谈话
吕月月:我没想到你今天还来找我,你要的是故事,故事讲完了,我还以为就再也找不见你了呢。
海岩:你是木是认为人和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吕月月:不全是也差不多吧。
海岩:那你利用我什么呢?你并不谋求我的剧本发表后共分稿费,可你还是认真负责地讲完了整个儿故事。
吕月月:……怎么说呢,这两年我很寂寞,人一寂寞就会怀念,我常常会想起潘小伟,我想假使我后来跟他去了国外我们会生活得怎么样呢,也许是我自己撕碎了一个本来已经属于我的美丽的未来。现在我对未来一无幻想,但回忆比谁都多。
也许你听了觉得笑话,我闷极了的时候常常用潘小伟的姓呼我自己的BP机,有时候看着BP机上显示出6C这两个字母,就像吸了鸦片一样觉得身上的血能流快一点。自我从公安局辞职后,我就在所有熟人朋友中消失了。两年来我没对任何人诉说过一句往事一句委屈和一句忏悔。
海岩,也算是你让我好好地宣泄了一下。可现在故事讲完了,你满足了,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海岩:其实我倒愿意分给你稿费,哪怕把稿费全部给你,要是你允许我发表的话。
吕月月:别收买我了。我想我现在的收入供自己喝粥是没问题了,还不致于要拿自己的痛苦卖钱花。
海岩:你从公安局出来是不是一直干夜总会?夜总会的收入恐怕比当警察高多了,你是不是觉得因祸得福呢?
()
吕月月:刚辞职我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积蓄,我妈也没有。所以,我没工作就无法生活。
海岩:像你这样条件的年轻女孩,大学文化,外形又好,恐怕不会找不到事干吧。
吕月月:我先是到人才市场去,最初有一家报社要我,条件谈得很好,可后来突然不要了,说是领导不批,我估计他们是到我们处里调查我去了。从公安机关不明不白辞职的人,人家也不能不慎重。后来又有一家大公司要我去当女秘书,也可以算是公关小姐,许愿说以后能分我房子,一切都谈好了,也面试了,结果后来也没再跟我联系。请岂:你没去问问吗?
吕月月:没有,我清楚问也没用。
那时候对我来讲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妈身体弱,年龄大,没户口,更找不到工作。我辞职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她毕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比较敏感,因此断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编了一套谎话给她,我告诉她是因为工作失误造成损失和上级闹翻与同事不和等等等等。我妈看得出我那阵情绪极度低落,所以她也不想刨根问底埋怨我。
海岩:她相信你的话吗?
吕月月:那时候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所以她也没心情多加怀疑。说实在的那些天我出门联系工作连公共汽车地铁都不敢坐,再大的太阳再远的路,我也只能借邻居的自行车骑着走,再渴也不敢喝一口冷饮。我妈托了很多人,只要是工作,哪怕工资就二三百,我也干。后来她一个同学给联系了一家公司,是个体的还是民办的我说不清。那种公司不很正规但工资较高,而且不要档案,不用政审外调,说好每月工资一千,干好了还加,但工作比较辛苦,要经常陪着经理到广州上海黑龙江海南岛去公关宣传推销应酬。其实我并不怕辛苦并不怕出差在外,只要能挣钱能让我和我妈在北京继续活下去我什么都干得了。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突然冒出来,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打乱了。
海岩:什么事?吕目目:我怀孕了。
海岩:啊!怀孕了?是潘小伟的吗?
吕月月:是他的。我生理反应越来越大,我和我妈开始都以为是生了什么病,于是妈托熟人关系带我去医院,医生检查完,告诉我妈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妊娠反应,只要回去注意休息注意安服加强营养别吃刺激东西就行了。
我妈几乎惊呆了,她事前一点也没想到,可她似乎在刹那间就明白了一切。她拉着我回家,让我歇着不让我干活儿,我问她医生说什么来着,我这算什么病要紧不要紧?她不答,搬了个凳子坐在我面前,她的面色是慈祥的,平平静静地问我:
“月月,你肚子里有孩子了,你能告诉妈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愣了,我没想到我的身上居然还留下了潘小伟的一块血肉,我哇一声哭出来,不知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
我妈问:“是那个姓潘的吗?”
我承认说是。
妈问:“你是因为这事辞职的吗?”
我说是。
又问:“是因为这事和薛宇分手的吗?”
我说是,我不爱薛宇。
妈眼睛盯着我:“那你爱姓潘的吗?”
我泪如雨下,我说妈妈,妈妈,我爱他,我从没这样爱过一个人啊!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沉默了一会儿她才问:“后来他抛下你跑了,是吗?”
我摇头,“他死了。”
我妈明白了,她伸出双手抱住我,紧紧抱住我,不停地叹着,“我苦命的孩子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令我惊讶也令我感动的是,我妈没有给我一声斥责,她明白我把多大的痛苦吞在肚子里一直没说!她想分担这痛苦淡化这痛苦,可眼下她又不能不马上问我:
“月月,你打算要这孩子吗?”
我没有回答。妈斟酌试探商量着说:
“月月,你刚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多不容易呀,要孩子你就没法工作了。”
我流泪我没有回答,妈说:“我可以不要你养活,可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要说养活孩子了。”
我知道妈说的是对的,是现实。而且我才二十二岁,完全没想到也没准备好这么小会有一个孩子!
()
但我又想我怎么能再犹豫,难道今后我还会再爱上谁吗!还会再和谁恋爱结婚再生孩子吗!不会的,绝不会的,我注定要和我妈一样独身到老,只不过要比她孤寡得更早。所以我咬着牙把心一横,我说:“我要这孩子,哪怕我上街讨饭,也要这个孩子!”
我失去太多了只想要一个孩子,我一无所求了总得有个寄托。我一无所爱了但总要对得起潘小伟曾经那样地爱我!
我妈不再说什么,第二天她去买了两张硬座火车票,带着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东北,回到我们的老家密山县。那儿还有我家的一间;日房,和我父母的几个故人。
在我上大学离开老家时,我曾告别了那里的一切,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落魄归乡。
那些熟脸的同学、朋友和邻居们看见这个当年闹过一阵风流传说的漂亮的女学生一无所有地回来了,挺着不清不白的肚子,招摇过市。也许只有我自己,才不觉得羞耻。
几个月后,在密山县一个再简陋不过的肮脏的小医院里,我生下了我的儿子。
医院里不能住,分娩的当天我母亲就扶着我回到家里。我的儿子从一降生便自知生不逢时,所以极为克制极为忧郁,从不无所顾忌地哭喊。那时候只有我妈守着我们母子,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困苦无助的日子。
我给儿子起名叫吕念伟。他和潘小伟一样漂亮。他们父子俩确实太像了,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坐月子的时候营养跟不上,身体恢复得一直很慢。都说女人坐月子会发胖,可我从来没胖起来过。大概有三个月我没找工作,一时也找不到合适我身体的工作。
虽然有不少当地开公司的大款凑上来帮忙,请我去当秘书当助理并表示绝不会累着我,可他们太热情太无私了我看着害怕,因此不识抬举—一谢绝。那时候我妈又回到小学去当教书匠了,有点收入,我也被我们那儿两个厂子请去拍照片做产品广告,一次三百,一次五百,挣了八百块钱。我想这些钱给我儿子买瓶奶粉买块尿布也够了,犯不着再找个火坑自己往里跳。
海岩:你什么时候又回北京了?
吕月月:我在老家一共呆了一年。本来我妈已经帮我联系了一个中学让我去代课,后来通知我不行了。据说学校是愿意的,可教育局有说法,认为一个未婚而孕显然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的人怎能为人师表。我们那地方太小了,张家长李家短哪里有喜哪里有丧恨不得全城都知道。人们见了我免不了侧目而视然后窃窃私语,我上街买菜也得躲躲闪闪掩面而行。我想来想去觉得要想隐名埋姓重新做人就只有回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去。
我妈不愿意我走,她说月月我太了解你了,你是个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经不住诱惑。北京那个地方,机会虽然多,但陷阱也多,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我决心要走。我对妈说现在不同了,因为我已有了儿子,我要带他一起走,我今后所作所为,都会想到 我的儿子。
实际上我妈一生的期盼就是我能过得更好,她也不愿意我永远窝在这边远的地方,于是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揣在我的怀里,又给我做了炸酱面打卤面为我送行。
上火车时她抱住我痛哭,她说她预感到我这一去就再不会回来了,她将见不到我见不到孩子一个人留在这边远的小城里孤独地老去。她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使我一直心酸到现在,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拼命挣钱,好把我妈接出来共享天伦,好让我儿子受最好的教育出人头地。
就我样我带了我的愿望和誓言,带了我的还在邂褓里的儿子,又回到北京来了。
北京没有我一个亲朋,但 有我的思念,我的梦想。
开始一个月真不容易,我在朝阳区麦子店那边找了一间农民房,有七平方米,很破,每月租金五十元。那时候夏天还没有过去,酷暑难当。房东家旁边有个水塘,一到晚上水气蒸腾,蚊虫成片。我那小屋白天在暴日下无遮无挡,晚上闷热异常,还得挂上蚊帐。我带着孩子,一天到晚怕他热出病来,就是那样的生活我也熬过来了。我在一个酒楼里找到了一份额位的工作,后来那酒楼里的一位小姐又介绍我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子夜总会比干酒楼挣钱多。
海岩:后来你就搬到丰台这边来了?
吕月月:对,这儿条件好,也没人知道。
海岩:你儿子呢?
吕月月:我把他托给这儿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了,我每天上午到老太太家去,和儿子在一起玩玩儿。
海岩:我原来还以为你每天上午都忙着出去在别处另打一份工呢。前次有好几天都见不着你。
吕月月:前些天孩子闹病。扬岂:和你过去的同事,像伍队长、薛宇什么的,还有来往吗?
吕月月:没来往。前一阵在街上碰见了刘保华,他见到我挺惊讶,问我在哪儿发财呢,我说在皇族夜总会当服务员,他直犯愣,觉得我居然干这活儿真有点不可思议。
海岩:
吕月月,我也觉得你在夜总会那种地方陆人家喝酒,总不是个事情。
吕月月:现在不让陪酒了,公安局总来查。客人少了,小费也少了,再下去恐怕我连“面的”也打不起了。钱对我来讲比别人更重要。
海岩,你知道我在原来那家酒楼当领位时,领到第一份工资以后去了哪里吗?
()
海岩:去哪儿了?
吕月月:我去亚洲大酒店了。我在酒店一楼的那间“香港酒廊”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是坐在靠窗子那儿,坐在我和潘小伟第一次相对而坐的地方,也是要了一杯咖啡。
海岩:你是想追寻什么,还是仅仅出于怀念?
吕月月:怀念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种忏悔,欲哭无泪,只能。
海岩:对谁忏悔,潘小伟吗?
吕月月:潘小伟,伍队长,薛宇,我的组织,我妈,我对不起一切人,因为我的幼稚,还有盲动。
坐在这个酒廊的窗前,看着面前一杯浓浓的咖啡。这咖啡和茶几上的所有东西就像一幅静物画一样,使人清醒。这时候我才隐约看清自己灵魂和性格上的怯懦和浅薄,那么容易被诱惑,又那么容易失望。也许我从十六岁时被卷进那个丑闻开始,就造就了保护自己的本能,果断地,冷酷地,不假思索不假犹豫地保护自己,而不考虑是否伤害了别人。
于是潘小伟和我就成了一对冤家对头,他同样耽于幻想易于失望,是一个喜怒哀乐着于心形于色的人。当幻想滋润他时,他就青春勃勃充满动力;当幻想破灭时,就心灵枯萎、灰心绝望。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幻想。我们不幸地忽视了这样一个认识:人如同树木~样也要枝枝 权权地成长, 而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固定的雕像了,因此既不能容纳对方的缺点,又使自己变得神经过敏,总是全身心地期待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的生命。 于是,当对 方给我们一点点爱意或者无情,温暖或者冰冷时,都能逼使我们求生或者求死,陷入疯狂!
于是,就有了这个孩子式的游戏和它的荒唐的结局。
海岩:月月,现在你能够这样检讨反思,就等于有了重新开始的基础,这就是人的成熟的过程。关于整个故事的结局,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吕月月:没有了。说不定我又办了一件傻事,没准你会失信发表这个故事,甚至把它直接卖给公安局, 让他们知道当年 我和潘小伟私奔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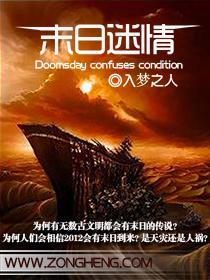






![[hp]嘘,这是个秘密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58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