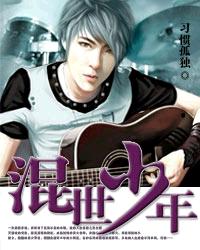混世和光-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想到这我真感到无比恐怖。
这是无边无际的日子,这是仿佛融化在了宇宙天地间的日子。不管身处何地,我都觉得自己像驾一叶方舟飘浮于茫茫的大海之上。孤独,无助,没有生命感,总担心被浪涛吞没。
我似乎绝望了。食堂,岳麓山,山上的小房间,山脚的林荫道,爱晚亭的溪流落叶,仿佛都在向我指出一种无法避免的绝望。它们以各自的特质把它们对绝望的理解强加给我。它们实在欺人太甚了。但我实际上又知道它们这样做其实很公道,公道得甚至找不出一点瑕疵。
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绝望,我是曾想到过的。我由不得不去这样推想,很久以后,我会不会有同样的感慨?不过我马上就知道这很可笑,因为绝望不光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现实状态,如果绝望是真的,那就不会有未来。也就是说我给现在的心情定性为绝望有些过分,也许由于某种自虐情绪过于强烈,我想用绝望来进行自我打击,以毒攻毒,便可以使自己对这样宁静的生活不至于太敏感。这方面我有过成功的经验,而且屡试不爽。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想法太奇怪了,差不多跟神经病没什么不同。实际上就是这样,无论从医学的角度还是精神的角度说,我已经是一个神经病人了。居然喜欢自己对自己进行精神迫害,如果说这还不算神经病,那什么样的人才算呢,难道非得要自杀了才算吗?可依我的理解,自杀绝对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跟神经病完全两码事,如果我有那样的勇敢,那一切痛苦早就在我身上结束了。
神经病人最糟糕的不是糊涂,而是自以为很清醒,好比醉酒的人总声称自己没醉。这是他永远解不了的结,永远冲不过去的精神关卡。
张学友用那杆标枪把我的自尊心扎得像一只霉烂透了的马蜂窝,他从这件事上最大限度地获取了他本来连一丁点都不该获取的快乐,终于心满意足了,就不再提那碴了。我的心虽然惨不忍睹,却也终于得以松了口气。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也就松了这么一口气,接着却被憋得更加难受。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贱骨头,别人把女孩送上门来,我故做清高,可事情过去了,我却又想了起来。这真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念。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晚上睡梦中的时候我是绝对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的,而失控的心灵会梦见什么人和事呢?显然,只会梦见女孩子,或者是初中时暗恋的一个女同学,或者是哪天路上碰到的一位绝代佳人。梦到深处,那件最敏感最神密的武器自然就抬举了起来,疯狂地朝梦中的佳人和被褥射击着。我无数次地想消除这种现象,非但一次也没有成功过,还越来越严重。最后我只能放弃,任凭这种现象充斥在我的睡梦中,任凭它将我一个个完整的睡眠撕扯得四分五裂。其次,即使在我清醒的时候,也常常被一张美丽的面孔或苗条的身影惹动情思,拔乱情弦。当然,这时候的想念不会像睡梦时那样不着边际,甚至连一点幻想的味道都没有,是非常现实而具体的。这样看来,似乎又不能说我那次放弃追女孩的机会是可笑的愚蠢的,也许我真的做得很对,因为毫无疑问那是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而我现在需要的是真真切切的感情慰藉。
是的,该找个女朋友了。这是在文学和食堂都不能给予我快乐的情况下唯一可能得到的快乐的办法。当然,也必须看到以我目前的条件,要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不太可能,也就是说这个心愿即使实现了,能有多见效也很值得怀疑,但肯定聊胜于无。对我来说,现在能做到聊胜于无,已算得上一件很了不得的事。这个心愿就迅速地膨胀强烈起来。虽然上次那件事一直让我心里隐隐做痛,悔恨不已,不过一想到自己是真的想做成这种事,那种痛实际就渐渐麻木了。
食堂里是有好几个女孩子的。因为她们长相平平,出身低微,我进食堂这么久几乎从没正眼瞧过她们。我甚至傲慢地觉得她们的容貌根本对不起我的一个正眼。但现在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看法。她们不是艺术品,我也不是鉴赏家。都是一只锅里的料,汤汤水水混在一起,谁也别说是谁坏了这汤里的味。
有一个女孩子,叫吴琼花,她是乡下顶职进来的,小我一岁,工龄却长我两年。在几个相貌平庸的女孩中她算是稍稍能看那么两眼的女孩。我开始考虑她了。从前,她是不怎么把我放在眼里的,我以为那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痛恨的表现,哪知我心里刚刚有了这么一个小九九,她就迅速地靠了上来,就好像一只客轮,看到了码头,恨不得立刻泊岸似的。这倒把我吓了一跳,原来这种阶级的观念只是我的一种想当然,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政治挂帅时代对我的影响的一种罪恶的思想观念,其实哪有什么阶级的区别,那全是骗人的鬼话,她先前对我的漠然无非是因为不觉得跟我有什么可能,一旦发现未必如此,她就兴奋得有些乱了方寸。
我后来细心观察,她的五官还算标致,只脸上一些标志着正在健康发育的数不清的青春痘严重损害了她的容貌。出一个美人确实太难了,仅仅一个地方符合审美的标准绝对不够,必须所有方面都达标,才能出类拔萃。我不禁再次感叹自己的命运,碰上这么一朵可以顺手采摘的鲜花,却又发现它好像花期已过了似的,令人兴味索然。想闭着眼睛摘了算了,实在有些不甘心,可放弃呢,又不甘寂寞,真想让感情和肉体都同时得到一点慰藉,熬过这段度日如年的日子。这种进退两难的心情,使我就像一片飘落的绿叶,轻轻地落在这朵花的枝叉上,既不属于这枝花,表面似乎又跟它合在一起,我的算盘是这样的:拖拖再说,如果可能,就在花枝上做长久的打算,如果实在不适应,那也只需要一阵微风,就可以飘走。
这个时候,有娘们也上来撺掇我。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好做媒婆的娘们,她们有时很有用,确实能缔造一对美满姻缘,有时却好心办坏事,给人制造麻烦。以我的命运,想碰上前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后者。她们的撺掇叫我非常为难,因为我还没有拿定主意,不便说同意或是不同意。她们就拚命做我的工作,要我多注意注意吴琼花的屁股。
“那是多好的一张屁股啊!典型的宽股肥臀,显然口子也大,挤出来的东西准是胖大小子。你家祖宗积德,在只准生一个的时代都不绝后。再有,吴琼花性情温顺。如今女孩大多水性扬花,稍不如意就给你戴绿帽子,讨了她,她准给你紧闭门户,一辈子你都不用担心老婆失窃。”
不可否认,这些没有文化的娘们因为做惯了媒婆,这方面的口才非常出色,简直可谓三寸不烂之舌。我左支右挡,硬是没招架住,让她们说得垂头不语。
要把一种摇摆不定的想法付诸行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有过很多次这样的体会,也积累了不少应对之法,可临了我发现自己竟还是跟一个毫无经验的人似的,完全进入了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我真的就跟花枝上的那片落叶一样,既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解放自己,最后还是决定往下拖。
我不知道,究竟是自己有意模糊了这个事实,还是真的因为深沉的矛盾心理使自己的判断力大为下降了,我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将我们之间的这场感情游戏拉开帷幕的。偶尔,四只眼睛会不经意地那么对视一下,在我这方面,传递的是一种枯涩的情义,收回的是一种既别扭又可笑的感觉。至于她那方面传递的是什么呢,我就看不太明白了。就我们各自的条件而言,我自认为她传递的应该是托付终身之意,顶多带点朦胧的味道而已,可实际上细细咀嚼,我好像又不敢确认。我甚至觉得她的目光比我的目光还要散淡,像打鱼撒出去的一张大网,并不专门针对哪条鱼,只要能网住鱼就行。她的这样一种纯托付式的态度,叫我原本就难以体会到快乐的心就愈发品出了几分枯涩,真想立刻中止这场荒唐的游戏。但我立刻就把自己说服了,其实这是好现象,她不太当回事,就意味着这只是一种规矩并不那么完整的游戏,约束较少,进出自由。再说我的态度是这样散淡,也根本没资格要求别人态度严谨。不管是玩感情还是玩游戏,公平是必须首先懂得的道理。
我们之间开始出现一种气团,一种柔柔的,轻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即使真的细心去感觉它也好像感觉不到,只是当两人接近的时候,朦朦胧胧觉出来的,似有若无的那么一种气,将我们罩住了。我敢说那绝对不是吸引力,但我又没办法给它准确定性。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气团的特点,那就是非常容易让人丧失警惕性,两人不知不觉地经常凑在一起说话。
有一天,我正在磨刀。她忽然把刀子递了过来,要我给磨一磨。我微微一笑,问她:“人要不要也磨一磨?我看人更应该磨一下,不然会生锈的。”
她立刻叫唤了起来:“啊呀,你是教授的崽呢,也学得这么下流啦!”
我撅着嘴嘀咕说:“教授的崽又怎么样?教授的崽就是这种鬼样子。”
她扑哧笑道:“呀,你倒是蛮……”后面的话她没说出来,我估计她是想夸夸我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可找不到合适的字眼。
说那话时我并没想太多,似乎完全是随口的一句话,我甚至都说不清是一种追求者的心态还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态,可过了一会,我忽然惊讶极了,我好像为那句话感到了十分的愉快,甚至还有十分的得意。那样的自我批判精神从前我是没有的,即使偶尔有那么一丁点反省,都会叫自己万分难受,比事情本身给予我的难受更甚。大概正因如此,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就不断地犯错误,便一步步错成了如今的惨不忍睹。我也曾劝过自己,一定要学会自我批判,或者是深刻地自我反省,不允许老是受制于那种狭隘之极的自以为是的本性,可总是不见效,最后依然被狭隘的心胸收拾得干干净净。哪知不知不觉的,无意识中,我居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这样的学习。我欣喜地看到自己开始成熟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品味到成熟带给自己的快乐,我还惊讶地发现,这样的快乐比从前那种盲目的狂妄带给我的快乐要真实得多,尤为可贵的是它的稳定性显然高于狂妄的快乐,而这自然会对我的精神发展给予极其有益的影响和帮助。成熟的滋味确实太美妙了,它跟我平常体会到的快乐还不完全一样,它更柔和,更细微,更轻松,也更容易弥漫在我的心田。我觉得我的灵魂世界豁然开朗了许多,像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蓝天白云,我可以像一只鲲鹏在其中自由地翱翔。整整一天,我都沉浸在这种愉快的感觉中,似乎已经有很多年了,我都没有这样高兴过。如果非要拿它跟上次的感觉相比,那好像还得追溯到少年甚至童年的时光。不过当这股高兴劲完全过去后,我觉得它还是有遗憾的,那就是这种成熟居然是由一件自己其实并不太愿意去干的事造成的,我便觉得成熟的价值打了些折扣。我一直期待的理想状况是在书籍中学到成熟,可实际上书籍非但没让我如意,还一天天地增加着我的失望,把我不断推向去跟已逝的历史进行无谓纠缠的状态中。
我的高兴甚至延续到了睡梦里。这个晚上我梦到的全部是阳光和花朵,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女孩。次日早上,高兴的余韵依然将我包裹着,我闻到了一股仿佛是从心灵深处散发出来的香气,它源源不断地扩散到了空气中,我便觉得连空气都能体会到我的愉快情绪了。以此推之,那整个宇宙世界应该也体会到我的情绪了。我真不认为这是什么很荒诞的想法,因为我看见眼前的一切景象都跟平常大不一样,树林在对我笑,野草在对我笑,山峰在对我笑,即将隐去的星月和正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也在对我笑。它们绚烂的容貌甚至比我的表情还要丰富热烈,好像不是我成熟了,而是它们成熟了。
当然,我也不会忘乎所以,以为自己真正成熟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成熟的开始。我之所以高兴成这样,是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进步,而这样的状况通常是不容易体会到的。
上午,我又去磨刀。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刀子钝了还是我在期待出现什么故事。不过故事是真的出现了。没磨几下,边上就有人递过来了一把刀子。那是我昨天磨过的那把,显然吴琼花又追杀了过来。我扭头看着她。她笑眯眯的,还是用的那种哀求的口气,虽然话语没变,但我听得出来,内涵是有些不同的,掺杂了一点柔情和不可抗拒的意志。我接过她的刀子,也用昨天的口气问她:“人要不要也磨一下罗?”
她今天不嗔怪了,竟还很配合我的无聊挑逗:“刀子磨快了可以切菜,人磨快了能做什么?”
“人磨快了好生崽嘛!”
“你是教授的崽呢!”她摇着头拉长音调感叹道。
“教授的崽就是这个鬼样子!”
我本想以昨天的方式为今天制造同样多的快乐。哪知同样的自我批判,今天我却一点没有感到快乐。不过我依然还是有成熟的得意,这大概是不会随着高兴劲的过去而消失的,因为它不是感觉而是一种认识。
我的确不太喜欢磨刀子,我喜欢磨人。自从说了这句有水平的下流话后,我就常常在磨的时候把吴琼花想象成一把刀子。这并非胡思乱想,在我们省城的土话里,就有将女人的那个器官看成是一把杀人刀的说法,男人们在对两性关系高谈阔论时一般总要这样感叹一番,表现出他们那种对这把刀子既无限喜爱却又万分恐惧的深刻的矛盾心理。事实上还真不是玩笑话,把这把刀子磨得越快,那被其割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就是刀,刀就是人,人做了刀子可以杀人,刀子做了人可以磨刀,人磨刀,刀磨人,磨来磨去,杀来杀去,真不知道究竟是刀杀人,还是人磨刀。
我一边磨刀,一边想人,不停地摇头叹息,人世间的事实在太复杂了,即使是一件看似简单的事,只要稍稍钻进去,就会发现跟先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我把磨得寒光闪闪、冷气逼人的刀子递到吴琼花手上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