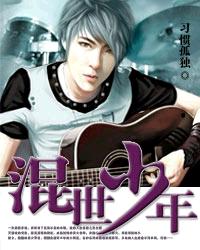混世和光-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天秦轮对我非常不高兴,他显然认为我昨天敢旷工大半天是仗着我曾经拜访过他几次,他原本也是可以看在这一点上原谅我的,可问题是这段时间他察觉到我又缩了回去,就觉得似乎是上了我的当,便对我板着面孔,要我知道我没有任何资格享受旷工的特权。我想向他解释一下,可书院废墟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它使我觉得跟它相比这种由旷工引发的领导信任危机根本不值一提,最后硬把想解释的念头彻底粉碎了。立刻,我就听到秦轮像一头马似地喷了个响鼻,这是他否定一个人的典型症状,我对他的那几次拜访便就此化为乌有。
今天我又去了书院。废墟上还在冒烟,我知道,那是它死灭的躯壳的呐喊。我真想帮它喊几嗓子,可昨天遭受的无妄之灾使我马上把嘴巴闭上了。毕竟我还活着,而活着的人是不宜随便呐喊的,否则就会无端惹上麻烦。能在心里帮它喊上一喊,也算对得起它了。我的血迹依然留在讲堂的台阶上,被寒冷的山风吹了一晚,它透出的凄惨的气息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块暗黑的影,除了我,再没有人知道那是血迹。可怜我苦痛的见证,竟是如此的一文不值,在世人的眼里它也许还不如台阶上的一块青苔,或者墙角处的一块霉渍。
我到处转悠着,在讲堂上仔细观看那些壁刻诗词、文章、学规和箴言。我认为从前的学问比现在的学问深多了,而从前的学生也要比现在难做多了。那时的学生更像苦行僧。难怪我一直觉得书院阴气很盛,一定跟这有很大关系,要培养出世纪风云人物,确实必须要有僧侣的修行。我踩过曾国藩的脚印,走上谭嗣同的讲台,进入蔡松坡的书房,读一行毛泽东的文字,就觉得有四股清流从山上直泄而下,冲开我愚昧的胸襟,将我的灵魂清洗了一遍。这是一种我期待已久的清洗,我觉得已被食堂的油烟污染得肮脏不堪的灵魂再度纯净明洁起来,甚至真有点像水晶一般透亮的感觉了。今天的拜访使我对书院的留恋之情越来越深,这段时间我便每天都要抽些时间来书院转转。即使看到的全是重复的东西,想到的也全是重复的内容,我仍非常重视这样的转悠。我认为这样的转悠就像磨盘一样,一点点地将盘里的东西磨成碎末,然后就好拿去做自己想要的食品。
封院的这天,我特地买了一瓶酒来,倒在讲堂的台阶上,完成了我最后的祭奠。
也就在这个清晨,我看见峡谷口处突然一扫数日阴霾,云开雾散,清风吹送出这个春天里的最嫩绿的万千叶片,热烈地飞翔出峡谷,飘向了东边那轮喷薄而出的太阳。
我不禁一阵惊喜,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红日当空。
一个陈年旧梦,前不久就进行过复活的挣扎,不过仅仅只是闪烁而已,可现在,经书院的光照,似乎已挣出束缚它的岁月的躯壳,趁着我的灵魂沐浴着光明的机会一并获得了新生。是因为受了启发,抑或是对书院里的那些人物有些不服,我不知道,只知道在这偶尔喷发的激情里其实蕴育了人生的必然选择。曾几何时,那个梦,也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它对我的意义就如同现在书院对我的意义,给予我启迪、思想和力量。我每次在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摔得鼻青脸肿,都是它把我扶了起来,包扎好我的伤口,抚慰我的心,支撑着我继续艰难地前行。如果说人的欲望是条大河,那个梦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它又像是我精神的催化剂,使我的精神每每膨胀到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地步。它推动我精神的发展,就像火箭推动导弹,经常迅速地把我送入高层空间,然后轰然爆炸;四分五裂。从所有的结果来看,这种催化剂固然非常有效,却又是带剧毒的。显然是这个原因,我实在吃不消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爆炸,所以早在两年前我就已经拒绝它的催化了。当然,未必完全是这个缘故,文学的盅惑力显然更胜一筹。即使是在我对文学最痴迷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也许有朝一日我还是会承认那种催化力的现实意义,甚至会更加固执地追求它的现实作用。果然,那个梦不仅重新回到了我的心里,而且回来得这么快,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不过短短两年啊,我原以为我们的分离至少应该是这个时间的两倍。
每天,一回到房里,我就站在窗前,看着书院模糊的影子,浮想联翩。那个梦显然就是曾经在我少年时代熊熊燃烧了好几年的野心。那种猛烈地燃烧,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让我感到炽热难当,我甚至仿佛又听到了骨头被烧得吱吱作响的声音。我彻底明白了,野心是不会消亡的,它的不会消亡,比文学的难以消亡更甚,因为它的历史更为悠久。两年来,它不过是蜇居在我灵魂的最深处。那是一种连我自己都很难探到底的深,所以我误以为把它消除了,或者埋葬了。也许它只是想休整一下,或者因为实在找不到出路,就姑且让文学来折腾我,它则从旁窥探我的弱点,以便有朝一日将我更紧地拽在手上。我不能肯定我现在于书院中获取的某种与它相通的力量其实就是它无形的影响力的结果,但我基本上可以相信这么一座废墟的书院居然都能赢得我的喜爱,跟它绝对不无关系,因为文学搁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解释不通。文学是属于峡谷的,需要的是松涛和星月,而不是文化和学问,更不可能是烁金淬火般的意志。我一直以为,命运把我安排到山里来是为了让我跟爱晚亭做邻居,现在我怀疑了,我开始认识到也许这是命运的一个骗局,它让我天天与峡谷的清风和明月为伴,情意缠绵,哪知其最终的指向,却是书院。如果真是这样,那它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告诉我呢?我想了一整天,好像懂得了它的深意,也许命运知道很难在这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让我放弃文学,另外它也很了解我固执的秉性,就设下这么一个局,先叫我在文学中挣扎,让我碰个头破血流,等到这方面的趣味淡薄了,意志削弱了,再让书院以死亡的方式来收拾文学,给我支撑起一片野心的天空。我的命运真恶毒啊,总是玩这一手,以一种毁灭换取一种再生,而且毁灭的往往都是我最钟爱之物。我不禁流了一行又一行的泪水,我实在忍不住,一方面我无法抵挡书院给予我的博大的野心,一方面对文学难舍难分。这样的泪淅淅沥沥,最后化做了一场霏霏细雨,把我整个灵魂都淋透了。
山中的小房依然透出那么无奈的灯光。有天我从外面回来,从茂密的树林间看过去,突然觉得那片灯光透出一片柔和的冰色,仿佛就是一团冰,结在春天的绿色中,凝冻了我生活里的全部内容。我一走进去,也立刻有了一种仿佛被冻得僵硬了的感觉。这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冰冷刺骨,然而却又丝毫感受不到死亡的威胁,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舒服,反而觉得比尘世更安全、更自由。
我在冰团里僵硬了很久,这样的时间仿佛成了一段久远的时间,带着远古的气韵,云雾般地袅绕在冰团四周。我恍忽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什么透明的树汁干胶凝固在里面的小动物,已有了百万年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我决定来当自己的这个考古工作者。我奋力将这透明的干胶剖开,把自己放进了我平常最喜欢的峡谷深山之中。我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来,又看见了漫天闪烁的星辰和月亮,又享受到了柔情缱绻的山风的吹拂。当然免不了有熟悉的伤感和愁绪,然而似乎不知不觉变得不重要了,成了一种亢奋情绪的陪衬,倒像是为了证明亢奋的可贵而刻意生发出来的,与昔日的真切相比,变得绵软无力了。我看到了夜暮中的爱晚亭,亭亭玉玉的风姿什么时候竟有了展翅飞翔的豪情,两片池塘的蛙声也合成了一道雄浑有力的山的合鸣,至若春的残存的温柔和夏的新生的凉爽,则显然预示着两种季候的更迭,和两种情绪的替换。那浓浓的愁实在是薄了,那沉沉的悲也实在是轻了,照着水里的影,随底下的月划过树枝和落叶、峰岭和柳条,还能记忆起往昔的诗情画意吗?其实这往昔并不远,这诗情画意也不可能全被池水洗尽,因为每次光临此地,目光就总有点模糊,总能看到在久远的过去所沉进去的心灵和滴进去的清泪。我带着文学的神韵度这一个个的夜晚,每每发现归来时已满身的疲乏和满心的伤痛。其实文学依然很亲切,那神韵也未完全消散,可架不住隔夜的寒霜把一切化为了虚无,而这虚无最终总是将书院托举在冰团的前面,托举在一片繁华的星月之下。
当我与文学走近的时候,文学非常顽固,而当我与它分开时,它竟又变得非常脆弱。我知道这还是命运在跟我开玩笑。在命运的手上,文学就像一个调节器,打开,可调出我的仙风道骨,关闭,则将我调成污泥浊物。它的调节究竟是根据什么呢?其自身的变化规律,还是我的生活状态?这个以前对我来说最简单的问题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我认识到至少近期内绝对不可能解答它,至于以后,也未必就能找到精确的答案。房间里的冰团开始融化了,这只百万年前的化石开始复活了。融化的冰水如同一道光雾,万千粉尘般地向窗外无边的黑夜流动,仿佛是一片浓缩了的云海,在一些讲述关于群山峻岭的纪录片中我曾多次看到过类似的景象。我不禁十分舍不得它们离开,我真希望它们再一次聚集起来,将我又凝固成一个化石。可惜它们的流动和凝固一样,都是很难改变的。我只能去感受这小片云海的魅力了。我好像能把融化的冰水吃进去,清凉地滋润我的五脏六肺,清爽之感美妙难言。但清爽也很浅,不能钻入灵魂深处,我便看到在心里最黑暗的地方,依然还是沉沉的困惑。
究竟是文学想放弃我,还是我想放弃文学,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巨大的。不过,对我来说,搞清楚这种区别其实倒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知道它们能对将来产生什么影响。野心的复活,就目前而言,或许更多的只能算一种思想游戏,它本身的可靠性尚未得到验证,至于前景,更是难以预料。在一幅幅看似很清晰的图画中,其实最关键之处尽蒙着层层迷雾。我的文学是被我扼杀过无数次的,它对我的精神伤害早就有了免疫力,所以面对融化的冰水,还有野心的进攻,它大概并不为意,甚至有可能还暗暗嘲笑,认为在这一番可笑的折腾之后,依然是它的天下。
第八章 牛年七
文学的这种自信,叫我不禁又心生恐惧。我真的很怕再经历一次被它始乱终弃的遭遇。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艺术特质决定了它喜欢玩这样的游戏。其实就感觉来说我也喜欢玩,可问题是它的生命力是无限的,我阴寿短暂,根本陪它玩不起。而野心不同,这是一种恶念,它不可能在社会中得到永恒的认可,就注定了它跟我会有同样的急迫感,我们当然就容易接近一些,容易锁定一个共同的目标。然而终究也不过仅此而已,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站在文学和野心中间,左顾右盼,摇摆不定。我有些发神经了,乱抓自己的头发,还时不时自抽耳光。缕缕青丝便飘扬在峡谷森然的落叶中,清脆的耳光便响彻在峡谷月光闪烁的空中。这是一种很有效的解脱办法,果然,立刻我就仿佛听到了一个来自半山腰上麓山寺里的声音,那好像是佛祖借助悠长的钟声传来的永恒的偈语:你在书院废墟之上取得的真经呢,你在书院的历史中锻造而成的砾石溶金的意志呢?我的灵魂就仿佛被佛掌拍了一下似的,有种整个儿变成了碎末的感觉。不过佛祖的声音很快消失了,留下依然空寂的山谷,偶尔响起一两声流莺的怪叫。哦,是的,意志,我怎么把它给忘了呢?我不觉为自己如此低下的运用能力感到羞愧。这样的能力是不配玩弄思想游戏的,可恨的是我却又乐此不疲,而且往往我进行自我否定的时候都会更注重被否定的方面,现在尤其如此,因为我觉得面对眼前的窘境,也不能谴责意志,意志的坚定必须以欲望为前提,倘若撇开欲望,它就像无本之木一样难以挺立。意志的对象永远是主动者,只有当它决定之后意志才会活起来。这是绝对的,惟有在背动中阐述其深刻的思想方成其为意志,如果反客为主,那恰恰是它的一个自我否定。不过以绝对的理论肯定意志与其对象的关系,似乎也容易造成新的问题,即如此清晰地划分主客体,又容易造成两者对主体地位的争夺,势必导致客体的冷场,而客体若不能得到确认,那主体即使有了定论也未必合法,更严重的是在客观的运用过程中它未必能真正发挥作用。我糊涂了,天啊,我该怎么办。这样的精神游戏,玩起来很快乐,可不容易拿到结果,又让人很不快。我非常为难,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我对意志进行了谴责。但我立刻遭到了猛烈反驳,意志显然认为在事情的两方面没有得到确认之前,它是不宜有所作为的,文学的轻浮是造成目前窘境的根本原因。文学就跟意志争执了起来,互相指责,甚至咒骂。它们的交锋让我痛苦万分。我该支持谁呢?我求教于峡谷,叩问于星月,向山上的佛祖讲述我的困惑。但我没有得到一点回声。似乎都不屑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还是太复杂。我便还是坚守着我的中间路线,将文学留在春天里,再将意志拴在时间上,我得好好想想,春天总会走过时间的,但春天又永远超不过时间。
思绪像一尾羽毛,飘浮穿行在云雾袅绕的时间长河上。
野心,像一朵生长在坚硬的岩石上的野花,花瓣里还带着毒刺和毒液,在苍茫的云海间盛开来了。
死亡的书院以一道海市蜃楼般的幻景不断挑逗着野心,似乎它担心野心脱离我的视线,更甚于我。它希望野心不仅鲜丽地开放,还能长久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希望有如日月一般光明浩大。书院飞翔的魂魄不断给野心讲述它近世纪的辉煌。对一般的人来说,都是老掉了牙的故事,一颗正常的心灵是不大容易听进去的,然而野心却似乎被迷住了,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吸吮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