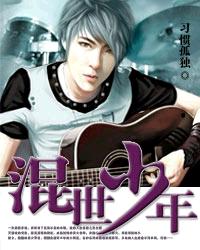混世和光-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道道的痕迹,这是我不能熟视无睹的。无论我怎样怀疑,无论我用什么办法去竭力证明那四年的虚无,最后我都只能回到眼下的大雪中,体会冰凉的寒意,一点点的将那四年串联到我的头脑里。虽然不管我如何努力,这样的串联都不会带我任何实质性的收获,更不可能重现那如梦如幻的四年时光,但至少它能证明,那四年确实存在。
然而,它就是那样的、轻飘飘的过去了,甚至连一道影子都还不如,不能向现在的我提供一点可资回忆的故事。时间仿佛在那四年里学会了一种魔法,一边占据着某个空间,一边又无情地将空间消灭。而且它消灭的方法极有意思,那就是把人和人的故事转换成大自然。这大概是它唯一不让我讨厌的地方,可我实际上并说不出原因,我不知道当时间的流水猛力冲刷着一切时,这样的大自然是否能领悟到时间的良苦用心。
反正四年已经过去了。我真的很不想重复那样的感受,可我还是必须再说一遍:无声无息。我佩服时间,表面看它是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怪模样,实际它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改造成了一种自然之物。简单地说,对于自然之物而言,时间当然是凝固的。不过除了佩服,我更多的其实还是仇恨。时间既然能使它的长度被压缩成一个点,压缩成惊鸿一瞥,那它就该将这种神奇的效果永恒地保持下去。但它没有,它可耻地背叛了它的初衷。也许这样说不对,它的初衷本就是包含了背叛的,只是我当时浑然不觉罢了。
山峰陡峭,雪片如刀,梅香四溢,风急天高。我伫立山头,看漫天白云卷过来卷过去。当然,我也会往下看的,特别注意观察山脚的形状,我想象那里应该跟记忆中的山脚有些不同,因为那无声无息的四年正在那儿一点地清晰起来。
再怎么样的清晰,也还是一片虚空。这是由那四年的基本元素所决定的。没有那样的元素,也就不会有那样的四年。
奇怪,那些元素似乎跟造成其它年份的元素没什么不同,单调的故事,单调的人物,单调的感觉。我忽然想,会不会是这样:从前的单调只是一种量的积累,所以我感受不到它的变异,可到了那四年里,它的积累达到了改变性质的程度,于是就变异了。是的,肯定是这样。一种平淡的生活,既不甘愿接受,又无法摆脱,天长日久,当希望彻底崩塌之时,那种生活的客观存在就必将被虚幻的感觉取代,做出一个巨大的坟墓的空壳,将之深深地埋葬在里面。
一眨眼的工夫,四年就过去了,居然什么也没给我留下。起初我还愚蠢地不肯相信这个事实,总觉得是自己的感觉还有点问题,或者说记忆库没有被完全打开,静一静心,等待等待,也许就会有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呈现出来,就像一滴水虽然是滴在一团海绵的背面,但时间一久就会慢慢浸透到正面一样。可我错了,我等待了足够的时间,始终没有等来什么东西。不知道是真的那四年什么故事也没有,还是我所寄予希望的这团精神海绵不善于浸透历史的点点滴滴。不过,严格地说那四年并非一点东西也没留下,因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它就是把一片时间的虚空如烙印般地烙在了我的头脑里。这难道不是一种纪念吗?这难道不是留给我的东西吗?千万别以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算东西,很多时候,真正有意义的给予是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只能让人永远咀嚼、品味、琢磨,挟带着它上天或者入地。
我似乎想通了,是的,我愿意接受那像云雾一样飘过去的四年,我愿意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变成一片时间的荒原,青草全部枯萎了,河流全部干涸了,山川全部消失了,阳光全部褪色了,没有方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找不到任何形容它的语言。突然有一天,我头清目明,就落在了它的尾巴上,像是被它吐出来的一颗核枣。当然,我不能说我一定喜欢这颗核枣,但至少我接受它的客观性,这对我今后的人生也许至关重要。
我并不想说因为这种接受我就一点儿悲痛都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毕竟那是镶嵌在我青春时段上的四年,是我青春的精华,甚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实际上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痛彻肺腑,心如刀割。他人的那种四年如旭日初升,霞光万道,灿烂辉煌。可我的四年居然连一道一掠而过的影子都不如,就更不要说一缕风,一幅画,或者一道光了。这样的痛应该是可以痛死人的,我之所以还能痛着活下来,大概得归功于曾经在剧烈的家庭冲突中所练就的承受力,苦难于我早已麻木了,故天底下最最伤痛的事现在不能奈何我。那么,应该怎样来形容我现在的痛呢?我想了很久,最后竟然忍不住莫名其妙地苦笑了一下,似乎这就是我最熨贴的解释。
我相信,对痛苦最深刻的描述不是眼泪,而是笑,是有些儿难看的笑。
我不知道这四年到底怎么过来的,不知道自己每天干了些什么事,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想的什么,说的什么,七情六欲是如何安置的。可山外却大为不同,我觉得那外面的每一粒沙尘也许都是一个极其精彩的世界。
我在大雪里走着,顶着千万片雪花,仿佛顶着千万片天空。这是我对那个悄然逝去的四年光阴的最深刻的哀悼的感觉。我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晚又一晚。虽然时间回来了,现实世界回来了,可我仍不觉得自己跟那座肮脏、可恶、丑陋、罪恶的食堂有什么联系,我只知道自己在走,好像要让这座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印上我的脚印。
从来没有哪一年的大雪下得这样久,这样无休无止。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的风光了,而弥漫了恐怖的气息,每过一分钟,它的恐怖气氛就会增加一分。我不免要想,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恐怖呢,难道无限的风光被时间拉长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奇异的变化吗?实际上我倒更愿意把那四年被压缩成一瞬间的奇特现象当成恐怖,因为它无条件地吞噬了我的青春。而这场大雪何罪之有?它不仅让我重新找回了时间,还让青春在我身上一点点地还原了。虽然这种还原肯定是非常有限的,但毕竟胜过虚无。
当然,绝不可能真正无休无止。忽然有一天,大雪停了。我不想去计算大雪到底下了多少天,那只能使我好不容易轻松下来的心再次沉重起来。我全身心地感受这冰天雪地,感受好像与我分别了四年的岳麓山。
又过了几天,久违的太阳从东方天际的云翳里露出脸,忍不住甩了几下,那意思好像是为着我对它的长久的期待而洋洋自得。大片的积雪便在它的吝啬的温暖中开始了消融。
我的心就也随之消融了。这颗随同主体被埋葬了四年的心,它似乎完全被冰冻了。它的冰层极厚,又为肉身覆盖,所以消融得十分缓慢,当外面世界的积雪全部化成一股股小溪流入湘江之后,它仍在冰团里慢慢地挣扎,轻轻地跳跃。这之后它消融的就仿佛不是冰水了,而是一滴滴眼泪,为它这么深沉的痛楚,为它这么难以融化的苦难。
我忽然恨起这场大雪来。自从我住进山里,每年的开年大雪都是我的节日,说得再准确点是我一年里精神上的节日,是我一年里精神上的定海神针,是我一年里绝不可缺失的物质营养,很多时候它会成为我期盼的良辰美景。可此刻,我真的恨它,恨雪,因为是它的到来结束了虚空的四年。现在看,我其实更喜欢时间被继续埋葬,一直埋葬到我真正的死亡。但我又知道,这种看似对生命十分放纵的态度实际是一种贪婪,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我跟时间完全合二为一了,那是只有成仙得道才可能有的境界,我离那境界还差得远呢,或许我得等时间被埋上一百次才能达到。不过我还是试图进行一番这方面的努力,竭力让自己忘却时间。自然,我失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丁点成功的可能。我只能空对着越来越清晰的时间长吁短叹。
有时候,我感觉失去的不是白花花的四年,而是身体上的哪一个部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跳动得非常厉害,足以证明这种感觉。似乎,我身上的血液减少了很多,常常供不应求,身体的有些部分就好像要离我而去了。过了一段日子我才弄明白原来这是心脏的毛病。当年的心肌炎留下的后遗症现在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我的生活,经常让我呼吸不畅,心悸气短。因对时间的清晰感觉而重新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感便有所缓解了。早上,我起床摸着咚咚乱跳的心,觉得可能来日无多,如果还为未来担忧那实在愚不可及。
时间是不饶人的啊!我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虚空的岁月,陈旧的苦涩,传承的悲凉,我倒甘愿在时间的河流中载沉载浮,最后慢慢沉入河里,去享受一种有点类似于穿云驾雾的舒服的长眠。
我绝不会去研究,我是怎样度过那虚空的四年的,我宁愿它是一个谜,是无数的问号,然后填充着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那些日日夜夜是需要填充的啊,如果不用谜填充,那什么东西能填充呢?
再来那么一次四年,甚至四十年,四百年,四千年吧!
我非常愉快地想象着,想象四千年后苏醒过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不会吓着人吧,我的遥远的子孙后代们,如果你们没被吓着,请祭书以告。
昨天分别的食堂,今天再见,已恍如隔世。我伫立在食堂门前那颗大楠木下面,看着人字形屋顶升起的缕缕炊烟,看着大门上的斑斑污迹,心里有无尽说不出的滋味。这是滋养了我八年的食堂吗?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但我又不愿意承认,我觉得准确地说不是它滋养了我八年,而是它埋葬了我八年。从那虚空的四年复活之后,我认识到一切对我都是埋葬,我早就死了,在食堂里是骷髅,在食堂外是僵尸。那虚空的四年不仅将我最珍贵的青春年华付于苍茫的云天和流水,还教我学会自我认识。我何曾在这个世上活过?我的“活”不过是死的一种形式而已。甚至可以说,我越有“活”的感觉,我“死”得就越彻底。那么,能不能反过来认识呢?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被它刺激得猛一激令,仿佛在寒冷的天气里有一滴水珠落进了脖子,使我仿佛被一条细小的冰带抽了一下似的。
我实在迈不动脚步,我不愿意进入坟墓,我被埋葬的时日太多太多了,我想真正地活个一天两天,哪怕因此将被埋入坟墓的最深处。我仿佛闻到了从前尸骨散发出来的腐烂的气味,好几次差点吐出来。我疑心自己已变成了一条狗,因为我对那种腐味似乎颇有点儿喜欢了,无论多么恶心,实际上我感觉自己在很认真地吸吮。我懂了,毕竟那是我曾经的肉身。一个人不管如何痛恨自己,都是会有那么一些自怜和自爱的。
这一次长久的伫立使我忽然觉得我再不能让“埋葬”成为生命中的主题,我必须对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提出我的异议。尽管这样的异议并非始自今日,可从前的一切思想都是不做数的,要有一个全新的自己,只能是重新自我塑造。但显然又太理想化了,自我塑造,这将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创造工程啊,我拿得下来吗?
眼前的食堂跟四年前的食堂一模一样,就连它屋檐上的一根青草和从屋顶上落下来的残破的瓦片都没有变化。南侧墙角下臭水沟发出的混乱嘈杂的流水声也是旋律依旧,音调低沉,似乎还在那里埋怨四周的人们不关心它的状况。这都不算什么,最奇的是我看见污渍斑斑的大门爬着一只蜘蛛,它居然也是我四年前见识过的,其在门缝上爬行的姿式竟让我看不到一点跟四年前的不同。一会儿它就爬到漆黑的屋檐上的一处角落里,开始习惯性吐丝。经历了四年时间的消耗,它的精力竟一如从前一般地旺盛,吐出来的丝依然又长又富于弹性。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是真的,确实有一只蜘蛛,贯穿了我四年的生活,悠然自得地活动生长在我坟墓的边缘,构筑着它那虽然狭小,却仿佛映照出了整个宇宙空间的奇妙世界。我由此觉得,食堂四周以及它里面的所有小昆虫小动物,都比食堂的人还要亲切。看看食堂那些人的嘴脸吧,我没到过阴曹地府,却常常觉得自己相当于生活在那样可怖的境地里。但我并非不知道,在那些人眼里,我更像是从阴曹地府出来的人,他们甚至很不明白为什么我还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无不认为我破坏了他们的环境,使他们本来每天都会有的快乐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一点不怪他们这样看我,如果把灵魂对换一下,我肯定跟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憎恨我这样的人。我想离开这里的心情比他们希望我滚蛋的心情更为急迫。可惜的是,我们都得学会忍耐。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眼光将对方视为阴曹地府的人,或者阴曹地府的鬼,而又不必妨碍我们之间相安无事。论力量,当然他们远远大于我,但一般而言,他们对我的厌恶感并不足以使他们联合起来跟我做对,因为我没有得罪他们,我给予他们的坏印象完全是纯心理上的,尚未上升到生理的高度。就我的精神状态来说,我不可能让他们的厌恶感上升到生理的高度,所以他们在共同的感觉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又只能是个体的态度,这就为我跟他们完全平等相处提供了条件。就我这一面来说,我的本事,他们是都见识过的,当年跟那姓张的主任的放对,曾闹得一向非常袒护张的科长都拿我无可奈何,后来科长没办法,只能把姓张的调开,任命了一个新主任,这样我才重新回到了食堂,没有继续吃单位的闲饭。大家因此知道了我这个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发起脾气来也是惊天动地的。所以,他们在厌恶我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跟我闹矛盾。我因着那么一场跟头头的无所畏惧的斗争而赢得了一种相对较为稳定的生存状态,别说跟姓张的主任掌权的时候相比,就是跟当年秦轮掌权的时候比,我在食堂的地位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如果说我在食堂里偶尔也能有一份微薄的愉快心情,那就是为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每每想起来就颇有那么一点自豪。当然,这是苦涩的自豪感,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张学友凑上来问我:“还是孤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