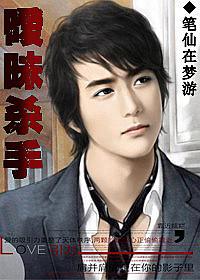暧昧的政治-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去说:“车马倒没什么,只是让皇帝知道我管理下人不严,就太不好了。希望江君放一马。”江充不听,上奏武帝,武帝表彰他说:“你一个臣子,就该这样啊。”江充之名大震京师。
武帝到了晚年,由于生理和心理原因,脾气渐坏,多疑症不能避免。当时一般人认为以巫蛊咒诅,或者以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使得某人得病遭灾。武帝一有小恙,便疑心有人谋害自己。而江充见武帝年老,又觉得自己以前得罪过太子,怕太子即位后为难自己,便上奏说皇帝得病源于巫蛊。武帝便派江充为使者彻查。
江充以治巫蛊为名,前后杀了数万人,绝大多数当然属于冤狱,但终得主上信任。江充得寸进尺,贯彻他自己的既定意图,向武帝上奏说宫中有蛊气。他们掘地求蛊,甚至将御座搞坏,至于皇后及太子宫中则更不在话下。史书说“掘地纵横”,皇后、太子无处可以放床,而且当然从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咒诅用的木人,还有大逆不道的帛书。许多人常常羡慕高位尊荣华贵,殊不知他们有时身受的打击与磨难更甚。正好2000年后,据说入宫搜索二毛子的拳民,要在每个宫女额上拍一下,拍出一个十字来的就是汉奸,前后也算是异曲同工。
此时,武帝在都城数百里外的甘泉宫养病,皇后、太子派去探问的使者根本不能见到帝面,他身边围着的只是一帮武帝自己认为可靠的人物,这也是独裁者晚年的普遍境况。太子打算出城向父皇辩明冤屈,他把老师石德叫来问怎么办,石德思忖此案如果发作,自己必无葬身之地,便跟太子说:“公孙贺丞相、两位公主等人都因巫蛊案被杀,现在太子宫中又被掘出木人,已经有口说不清,皇上又多日没有露面,说不定已死。我看可以假传圣旨,将江充等关进监狱,拷问他们的奸诈情状。当年秦始皇死,太子扶苏被奸臣诛杀。你今天难道不应该想想吗?”刘据说:“我这个当儿子的,怎敢擅自杀人?还是去见父皇吧。”但此时江充逼得太子极紧,太子手足无措,只得假传圣旨,将江充收监,太子亲往监斩,骂道:“你这个赵国来的王八蛋!把赵王父子害得还不够吗?还要来害我父子俩!”太子由是发兵。
按照史书的记载,武帝此时尚说:“太子惧罪,又对江充愤恨,致有此事”,并派使者召太子来见。使者怕死,不敢进城,就回来汇报说:“太子已反,欲斩臣,臣逃归。”武帝于是大怒,遂让丞相率兵诛太子,自己随后赴京。一场死者数万人的混战由此酿成。兵变前后10日,杀得血流成河,最后以太子兵败告终。
太子造反(2)
这场混战的场面浩大和细节繁复,这里也无法一一说明,最耐人寻味的是各级官员在其中的困难选择。战场两面,一为太子,一为皇帝,而后者一开始隐约不出,不知其存亡。两方面皆为朝廷领袖,无明显的标志可以一眼看清对错,所以各级官员煞是为难就很好理解。如丞相刘屈牦一开始不敢发兵征讨太子,在武帝的严词训斥和授权下才自将兵卒。太子先后召北军指挥官任安相助,任安受节,回营后闭门不出,后来被判定为坐观成败,腰斩。太子兵败时,司直(副丞相)田仁认为太子与武帝毕竟是父子之亲,不欲执之过急,放了出门。丞相欲斩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说:“司直是2000石高级官员,要斩得先请示皇帝。”武帝闻之大怒,将田仁腰斩,并迁怒于暴胜之,暴因惶恐而自杀。可见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一遇中枢有变,大多情形下各级官员都会不知所措,只能静观其变,等待中枢自身借某种力量或机缘澄清。在此之前,过分主动地选择,往往是为自己惹祸。这就可以解释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何遇到突发事件,总是无法反应,以致运转失控,造成一场场多余的祸乱。
太子逃亡到湖(今河南灵宝县北),藏匿于泉鸠里。他所居住的人家很穷,但很忠心,以织卖草鞋供养太子。后来因为向太子富有的老朋友借贷而走漏风声。大约是逃离长安的20天后,太子的住处被包围。刘据自忖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主人格斗而死,太子之子也一起遇害。吏员们破门而入,有的提着兵刃戳向已死的太子,此人后来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太守;有的急忙去把上吊的太子放下来,此人后来被封侯。
兵变被平而太子逃亡在外期间,武帝狂怒,几近于疯狂,群臣吓得要死,不知如何是好。壶关县(在今山西)的教育官令狐茂上书说:太子与皇上有父子之亲,又有继承皇位的重任,如果不是皇上被奸臣包围,亲情隔绝而不通,太子无法见到皇上,又被乱臣胁迫,是不会起兵的。太子完全是自卫,这点天下人都明白,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不亦痛乎!武帝见了,有些感触,但气尚未消。等到太子遇害后,又碰到多起以巫蛊相诬的案子,查验都无证据,武帝终于明白妖术的虚妄和太子的冤屈。此时刘邦祭庙的管理员田千秋上书说:“儿子乱用父亲的兵器,罪不过鞭笞;天子之子犯错杀人,该当何罪?下场太惨了。这是一个白头老翁梦中让我说的。”武帝马上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公独能清楚其中不对的地方。这肯定是先祖的神灵让你说的。”于是任命田千秋为部长级高官,而族灭江充全家,把苏文焚于横桥之上。可怜那位以兵刃戳过太子的北地太守,先是风光无比,此时也被族灭。武帝造思子宫,又建归来望思之台,天下闻而悲之。
详细了解这场人寰惨祸,沉溺于由误会和隔绝造成的悲剧情感,不是我们今天读史的本意。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武帝这般对人情世故及政治的洞察力,为何他还容得江充之流在其间搬弄是非?换句话说,纵使专制君主的晚年身体固然必定差下来,又为什么一定要让通常所说的小人物服侍,而大臣妻子反不得交流?再通俗一点说,以武帝这般的天赐英才,能够变更制度,开边拓疆,为何自己的家务却处理不好?是他不知建立一个好制度的重要性呢,抑或他根本对此无能为力?
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比找到一个好的领导人物要重要10倍,这几乎是当代人的政治共识。而传统中国的性质也被一般地判定为无法治、无制度等等。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难道中国古代的英才俊彦们都是那么愚笨和不开化,他们的政治智慧竟然全不如今日的一介之士?难道他们对自身的困境毫无觉察,而委屈求全地一次次承受循环的治乱,永无止境?
一个问题如此来提问,答案已经有了一大半。事实上,一般地判定古代中国无制度,当然是缺乏常识的表现。问题只在于传统的制度与我们今天脑海中的概念相去太远。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制度制定时很难找到切实依据,生发由心,制定后便常常难以落实执行,盼望着杰出人物在施行时能因地制宜、随时校正。当制度本身的来源、依据和落实都存在问题时,又遑论坚持制度重于一切!人们平时常常夸夸其谈建立好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坚持、执行制度的重要性,却不知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须从长久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而来。制度如果只由当政者随意制定,抑或迫于某种压力甚至向更高级的文明抄袭照搬,结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在制订时就充分反映现实和民意的制度,才有成为好制度的可能。
回到汉武帝身上来,我们可以发现:大汉帝国确实有很多天生的缺陷。当初将广阔的地区整合成一个庞大帝国,固然有种种现实需要,但也留下了致命的病根。那就是指导帝国的原则必须是超越现实的(至少是超越部分地区之现实的)、笼统的、宽泛的,因此落实后是必然要打折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原则又必须是不可动摇的,是应该坚决维护的,因为任何对原则的怀疑和修正,都有可能导致大帝国的解体。这个与生俱来的矛盾在传统中国确实无法解决。如此,一些在武帝看来需要严办的案件,在刘据这里就可从轻发落,而其间本也没有一定的准则。所以即使没有坏人从中播弄,政见也容易产生分歧。随着武帝晚年生理、心理的恶化,他被一群谄谀小人包围也是顺理成章,因为只有这帮人才能彻底抹煞胸中的良心而专门维护专制权威,并借机牟取私利。每当这种专制权威产生交替时,一有风吹草动,发生的事情可以无奇不有,而使用的手段也可以无所不择,一切都在强力和阴谋中进行。如此,父子亲情远不敌那一切就毫不为奇了。
但是,越是研究武帝的一生,你还不得不越是佩服。一般的专制君主,到了晚年,大多堕入魔道,倒行逆施,万劫不复。而武帝以70高龄,竟然深知己非,洗心革面,而深深念及百姓的苦痛,毅然改换政策,真是至为难得。所以在历史上,汉武帝的英名永难抹煞,尤其是看了后面诸多老年君王昏庸暴虐、不知悔改之后。
杀母立子
汉武帝共生6子,立继承人一事踌躇难定。原来正宗的太子刘据因巫蛊案被杀,一子早死,剩余几个儿子全有继位的可能。燕王刘旦能文能武,是把好手,但刘据死后,刘旦认为两位兄长皆已不在,按次序该轮到自己当太子了,马上上书请求从诸侯国入京。这反而引起武帝的疑忌,他干脆将刘旦派来的使者下狱,立储一事自然泡汤。广陵王刘胥,是个赳赳武夫,力能扛鼎,喜嬉游射猎,敢于空手同熊和野猪搏斗,被判为“动作无法度”,也不在汉武帝考虑范围之列。素受宠幸的李夫人,有子昌邑王刘髆,最有被立的可能。但是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率大军出征匈奴时,与丞相、也是亲家刘屈牦商量说早日请立刘髆为太子。武帝一日听到汇报,为了保证乾纲独断,防止外臣揽权,断然将丞相全家斩首,连随李广利出征在外的妻儿也未能幸免,全收入监狱中,刘髆也于一年多后病死。太子的名分理所当然地落到武帝晚年所纳的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身上。
武帝60多岁生刘弗陵,钩弋夫人得武帝晚年之宠应无可疑。刘弗陵生得白白胖胖,人也极聪明。武帝看看这个8岁的小儿子甚是可爱,决意立他为太子,但是有一桩隐隐约约的心事,武帝一时难以决断。
有一天,钩弋夫人偶然犯错,正好被武帝得知。武帝暴怒,突然大发雷霆,见惯风霜的老脸胀得通红。钩弋夫人觉得武帝浑不像平时模样,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她急忙脱下头上的首饰,叩头谢罪。武帝下令说:“送到掖庭狱去。”掖庭狱是宫中的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宫中的犯罪女性。钩弋夫人面无人色,在卫士们的挟持下频频还顾,武帝此时又大声呵斥:“快去,这回你不得活。”遵照武帝的指示,钩弋夫人被处死于狱中。
过了几天,武帝闲着无事,问左右说:“钩弋夫人被杀,外面怎么议论?”有人答道:“人家说:‘将立其子为帝,那又为何要杀她?’”武帝说:“对啊,这不是你们下等人所能明白的。自古以来,国家乱的话,都是因为君主年少,其母却青春正盛。女主独居,骄横难制,难免淫乱,做出乱七八糟的事来,而没人能够制止她。你们难道没有听过吕后的事情吗?所以我不得不把她杀了。”
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汉武帝此事做得不仅惨无人道,而且在法理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一般也都讲究罪刑相符,但是关涉专制权力中枢的偏偏另当别论。景帝时吴楚七国并没有叛乱,但是晁错从长远考虑,一定要将其削弱,即使逼他们真的叛乱也在所不惜。因为中央与诸侯国之间没有明文的契约关系,即使有契约也没有权威的机构监督执行,惩罚不依契约办事的一方,只有靠实力说话。正因为如此,有实力的一方不如趁早限制对方实力的发展,防微杜渐、以免酿成大乱。杀母立子正是循着这条思路推演的自然结果。有人认为武帝死时诸事疑点甚多,很可能是武帝猝死、霍光擅自废立。但是我以为光是杀母立子一事,表现出洞察一切的睿智和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不可能不出于武帝之大手笔,以霍光的脑筋还真不一定想得出来。
不过,靠牺牲一些东西来稳定国政,是否就是理想的政治境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人以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就是这种观念的老祖宗。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条人命比天下更为重要,因为得天下不外乎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而以杀害无辜的手段取得天下,早已失却了得天下的本意,所以他们宁肯失天下也不愿杀一无辜。当然这一派人士在古代中国早被判定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无裨于世。另一派则主张以较小的代价去换取大局的胜利,如汉武帝的立子杀母。他们也许确实止息了后来本会发生的一场动乱,而后来这场动乱假若真的发生,代价当然远不止一条人命,所以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显然划算。只是今天已身处21世纪初,世人早已眼界大开,明晓世界上有些民族还就是傻,真把百姓的一条人命当回事儿,连参加一场大战也要计较几个士兵的性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孟子所云未必就是迂阔和不切实际,而那些洞察一切善于以决断方式预防灾祸的也未必就是伟人。无论如何,尊重每一条生命毕竟更近于人性的理想境界。人类注定要在魔界和神界的接壤地区徘徊,正是有了对神界的倾心爱慕和不懈追求,人才不致于完全坠入魔界,而至今保持我们的人身。所以我们在叹服汉武帝睿智英明、敢于决断的同时,对他身处的环境和背景不能不加以清醒的省察。
霍光:忠臣抑或野心家?
在稍知西汉历史人们的心目中,霍光一人十分关键。他以霍去病异母弟弟的身份入侍宫中,受武帝临终托孤,自后辅政20年。不少时人及历史学家视之为伊尹。伊尹为商朝重臣,受先王嘱托辅佐几朝后王。太甲当政时荒淫无道,伊尹将太甲放逐出京,待到3年后太甲悔过,才接回复位,伊尹是一个敢于逾越常规但骨子里忠心耿耿的人物。偶尔也有人指责霍光过分揽权,逾越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