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垒浮云-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惯,总是抓起第一副牌,首先往桌上一翻,然后看下风的牌,但这天不同,捏牌在手,先私下看了一下,却不作声。
“上门地八,天门瞥十,下门和五。”
等马副官报了三门的牌,张宗昌才将牌翻了出来,是个六点,吃两门,配一门;其时翁左青已为马副官兑换了一批现洋在那里,银圆丢在红木桌子上,叮叮咚咚,益显得热闹。
“你怎么不玩?”张宗昌向站在他右面的富春楼老六说:“来、来、坐下来。”
富春楼老六便在上门坐了下来,坐在他身旁的翁左青献殷勤,将一叠筹码送到她面前问道:“两千块,够不够?”
“够哉!”她取了个五百元的筹码,押在上门。
赌了两把,一赢一输扯个直;推到第四条张宗昌大声说道:“推末条。赶快押,别怕!”
小牌九向例只推三条,如今推第四条,又有“别怕”的暗示,所以赌注异常踊跃。富春楼老六依旧押了五百元。
“六小姐!”站在她身后的毕庶澄说:“这一把要多押,听我的,没有错。”
富春楼老六尚未答言,翁左青已不由分说,将她面前的筹码,都推了出去,说一句:“这副牌你来看,一定是好牌。”
骰子打的是七,由天门开始分牌,分到富春楼手里是最后一副,她拿起来一看,说一声:“格未真叫作孽。”便要将牌翻开来。
不道背后伸出来一只手,轻喝一声:“别亮出来。”随即将她的手揿住了。
她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张宗昌已经在喊了,“庄家彆十,统通有。”接着,便将两张未翻开的牌,推入“湖”中,一阵乱掳。
富春楼这才明白,她也是一副瞥十,倘或一翻开来,“彆吃彆”有心通赔一把的庄家,亦爱莫能助了。
又赌了一阵,富春楼老六说她作女主人,有事要照料;起身让位,转脸与毕庶澄四目相对时,秋波一转,翩然而去;毕庶澄目送她的背影,进了后房,心中会意,站了一会儿,悄悄移步,也溜到了后房。
后房有张大铜床,陈设着一副烟盘;富春楼老六便说:“毕旅长,阿要香一筒?”
“我没有什么瘾,也不会打烟。”
这不成问题,富春楼老六打得一口“黄长松”的好烟;两人隔着烟灯,相对而卧,几乎与共枕无异;她的头发中散出来的幽哪的香味,中人欲醉,毕庶澄顿时下了决心,要剪张大帅的靴边。
“六小姐,我今天吃过你的饭。”
“喔,”富春楼老六问:“阿是勒浪一品香?”
“不错”
“味道那哼?”
“好极了。”
富春楼老六表示,一品香的“六小姐饭”尚欠讲究,她要手制一客什锦炒饭,供毕庶澄品尝,问他何时有空?
一听这话,毕庶澄受宠若惊,因为这比“吃私菜”更为难得。原来长三的组织分两种,一种是“住家”;一种是常见的“铺房间”——由“本家”租好一幢房子,分租“先生”们,各做生意,水电费用,按房间大小分摊,另设大厨房,客人设宴请客,菜用大厨房承办;如在馆子里叫菜,须贴大厨房柴火钱。“先生”平时伙食,亦大厨房供给,粗劣不堪;逢年过节,始特送佳肴四色聊资补报。“先生”则每邀恩客共享,谓之“吃私菜”;涉足花丛,常有“先生”邀吃私菜,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如今富春楼老六手制美食以飨,较之吃私菜更为一进,无怪乎毕庶澄受宠若惊。
“多谢,多谢!”他说:“我什么时候都有空,你要找我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
富春楼老六盘算了一下,约他第二天晚上来吃;时间总在十点以后,奇書網電子書特为叮嘱,晚饭不可过饱。
“明天晚上我就不吃饭了,留着量来陪你吃。”
正在款款深谈之际,听得门外有足步声;门帘启处,只见单军需陪着一个中年人进门。毕庶澄从报上见过杜月笙的照片,急忙起身招呼!
“杜先生!”
“毕旅长,你不好这么叫,叫我月笙好了。”
“那太没有礼貌了——。”
“毕旅长,”单军需打断他的话说:“我们都叫月笙哥,你也这么叫好了。”
“好,好!月笙哥,你请坐。”
这时富春楼老六已另端了一张椅子过来,杜月笙坐下来问:“毕旅长在上海很熟吧?”
“不算很熟。”
“那么,想逛逛什么地方呢?”
“一时倒想不起。”
“毕旅长,你做了我的客人,就千万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想办,或者想到哪里看看逛逛,想吃点什么东西,尽管交代。”
“是,是。多谢!”
“恐怕瘾还没有过足,请躺下来吧!”杜月笙站起身来,转脸说道:“老六,你代为好好招呼毕旅长。”
“杜先生,依放心末哉。”
杜月笙作了这番礼貌上的周旋,与单军需退了出去;只见张宗昌已经吃完“狗肉”,桌上堆了许多钞票银元,正在散发,各房间的先生、娘姨、大姐,无不笑逐颜开。
收拾赌局,开始花酒,名为替毕庶澄接风,其实还是张宗昌坐了首席。刚刚坐定,翁左青还在写局票时,张宗昌的随军参谋长,派了个参谋来,将张宗昌请到一边,低声说道:“参谋长让我来请大师回去,有要紧事要请示。”
“喔,”张宗昌问:“他人在哪儿?”
“在陈帮办的公馆里。”
陈帮办便是陈调元,他的新衔是“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作为卢永祥的副手,长驻上海,联络各方,跟张宗昌自然走得最近。他的手腕灵活,耳目众多;李藻麟一定是在他那里得到了什么重要消息,必须即刻有所行动。因此匆匆向主人告辞,赶到陈家。
“效坤,”陈调元从烟榻上一跃而起,“恭喜、恭喜!伯仁在书房里写东西,你请进去吧!”
说着,亲自陪他进了书房;伏案作字的李藻麟站起身来,拿起一份电报一扬,“大帅”他说:“咱们要组织‘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部’了。”
张宗昌愕然:“这要打谁啊?”他问。
“陈雪公另外有消息。”李藻麟先关上了房门。
“是这样的。”陈调元拉着张宗昌井坐在沙发上,低声说道:“张雨帅已经决定了,让姜超六来接江苏,郭茂宸接安徽,茂宸已经派他的参谋长,带了一个旅进驻蚌埠了。”
“这意思是,要俺给他们保驾?”
“对了。”
“不干!不干!”张宗昌大摇其头,“俺保卢子嘉到江苏,现在又保姜超六来接卢子嘉,‘又做师娘又做鬼’,教人把俺看成什么了?”
“错了!效坤,”陈调元问:“你不想衣锦还乡?”
“这是怎么说?”
“你想,苏、皖、鲁;还有个鲁呢!”
张宗昌恍然大悟,江苏、安徽以外,还有山东这个地盘:“对!”他猛拍他的长腿,“俺老娘四月初八生日,俺在济南给她做寿。”
“大帅,”李藻麟说:“咱们的司令部,应该设在四省枢纽的徐州。”
“好!”
“部队宜乎从速开拔;长江以南,对咱们的部队,印象不怎么好,早走为妙。”
“伯仁的话不错。”陈调元说:“不然,卢子嘉一定会请你留下来,见面之情很难应付。”
“好!”
第二天晚上,毕庶澄准十点钟来应富春楼老六之约,这天他穿的是新制的中装,宝蓝湖绉灰鼠皮袍;上套玄色华丝葛琵琶襟的坎肩,用的是珊瑚套扣;头上一顶青缎瓜皮帽,帽檐镶一块批霞;下穿纺绸单裤,踏一双黑呢便鞋;口街一枝八寸长的象牙烟嘴,俨然浊世翩翩佳公子,丝毫嗅不出武人的气息。
富春楼老六为他脱卸马褂时,恰好并排在一面大穿衣镜前;忍不住攀着他的肩,去看镜中人影,出生以来,也不知照过多少回镜子,只有此一刻她才觉得父母真没有白生了她这幅相貌;镜中一双壁人,她配得过他,他也配得过她。
“六小姐,”娘姨三宝又在门口喊:“作料都预备好了,”富春楼老六答应一声,关照三宝先上酒菜,是在她卧室中小酌,生着极旺的一个烧煤油的洋炉子,毕庶澄皮袍穿不住了,由三宝帮他卸衣。那三宝三十三、四年纪,生得一双很风骚的眼,水汪汪地看着毕庶澄,只赞他的皮肤既白又细,不逊于“先生”。
毕庶澄始终地微笑着。走到大理石面的百灵台席面一看,红的火腿,黄的鱼干,白的春笋,绿的菜心,黑的冬菰,颜色配得十分鲜艳,不禁酒兴勃然。
“喝什么酒?”三宝建议:“我看喝白兰地罢!”
“也好。”
于是三宝开了一瓶三星白兰地,在鸡心形的玻璃杯倒上小半杯,递给毕庶澄,然后站在桌旁,一面布菜,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
“你替我喝一杯!”
“不作兴的。”
长三堂子里的规矩,除非“先生”交代娘姨、大姐代酒,否则不能陪饮;因为“先生”是“花”,娘姨、大姐是“叶”,红花虽须绿叶扶持,但其职责在于帮衬。能有与客人私下示好的表示,便是喧宾夺主;为了防微杜渐,所以定下这样一个规矩。
“六小姐的饭,大概炒好了,我去看看。”
“已经好了。”有个小大姐在门外接口,接着便见她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碟五彩缤纷的炒饭。
“尝尝看!”随后跟进来的富春楼老六笑嘻嘻地说。
这盘饭用料讲究,远胜过一品香的“六小姐饭”;毕庶澄一半是讨好;一半也确是有些饿了,用长柄汤匙舀着,接二连三地往口中送;咀嚼之余,不断称好。
看他狼吞虎咽的模样,富春楼老六和三宝都笑了。“你门别笑,丘八吃饭,就是这样子。”
“你慢慢吃,”富春楼老六说:“还有汤。”
一听这话,三宝便转身而去,不一会端来一碗三丝汤。毕庶澄又吃一半,还剩下四分之一将长柄汤匙搁了下来。
“吃不下了?”
“吃是还能吃,不过太饱了,喝酒不香,停停再说罢。”
“停停冷了就不好吃了。”三宝凑趣着说:“我看六小姐吃了吧!”
“我吃不下,你拿去吃。”
三宝能食毕庶澄的吵余,正中下怀,高高兴兴地端着剩饭走了,顺手掩上了房门。
于是富春楼老六移一移凳子,紧靠着毕庶澄;自然而然地将手握在一起,隅隅细语。正谈得情浓时,外房的电话铃响了,然后是三宝接电话的声音,却听不清说些什么。
“六小姐,”三宝在房门上叩了两下,“毕旅长的电话。”
“谁打来的?”毕庶澄问。
“单老爷。”
单军需打来的电话,非接不可;毕庶澄起身出屋,很快地回了进来;富春楼老六看他脸色不。冶,急忙问说:“那哼勒?”
“我得走了,马上就得走!”
富春楼老六顿时花容失色,盈佑欲涕,望着毕庶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大帅下了命令,马上开拔,他自己已到南京去了。”毕庶澄安慰她说:“你别难过,我大概会驻防在蚌埠一带,等我部署停当了,我会来看你,或者接你到蚌埠去玩几天。”
“蚌埠?”富春楼老六问:“蚌埠勒浪啥场化?”
“在安徽。”毕庶澄探手入怀,掏出皮夹子来;富春楼老六枪上去揿住他的手,不准他打开皮夹子。
“勿!”她只说得一个字。
“三宝应该给她一点钱。”
局帐可以总结,“下脚”是要当场开销的;富春楼老六便从他手里取过皮夹子,打开拈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将皮夹子交还给毕庶澄。
“太少了吧!”
“好哉!”富春楼老六喊道:“三宝,来谢谢毕旅长!”
三宝便进来谢了赏,诧异地问道:“毕旅长为啥弗多坐一歇,”
“张大帅下达命令,要开拔到安徽去格哉!”
“格末真叫作孽,刚刚碰头,倒说就要分手哉,阿要难过?”
她不说还好,一说将富春楼老六强自压抑着离愁,又挑了起来,眼圈一红,急忙背转身去,暗自拭泪。
见此光景,三宝顺手端起两碟菜,‘退了出来;英雄气短的毕庶澄,抚着她的肩说:“你别哭,你一哭我心里更难过。”
富春楼老六收了泪,擤一擤鼻子,转身问道:“依啥辰光再来?”
毕庶澄想了一下说:“一个月。”
“是依自家讲格,下个月格今朝,我等耐。”
“好!我如果不能来,接你到蚌埠去玩,你去不去?”
“哪能弗去?”
“那就一言为定吧!”毕庶澄说完,掉头就走,步履很急,倒像逃走似的。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03张宗昌一到徐州,就接到电报,张作霖力保张宗昌为山东督军,郑士琦则调安徽。但郑士琦大有恋栈之意,授意他部下的第五师师长及十五个混成旅旅长,表示拥护郑士琦,不欢迎张宗昌。
张宗昌一心打算着衣锦还乡,四月初八为他老母在济南大张寿宴。哪知好事多磨,老母的生日愈近,愈不耐烦;一气之下,决定动武,派许现率领两个旅,进入山东枣庄,要唱一曲“取帅印”。
生日当然还是要做,不过只能将老母由掖县原籍接到徐州来受贺。这天贺客盈门,大多是“会说掖县话,便把洋刀挎”的同乡,郑士琦亦送了一份厚礼,并派专差致贺。
开席时,王鸣翰赶到了。张宗昌一眼望见,离开主人的席位,将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俺已经叫许金门带两个旅开进枣庄,你得赶紧预备接应。”
“不,不!”王鸣翰正是为此而来的,急忙摇手说道:“大帅,你得赶紧打电话给许金门,立刻停止前进,在原地待命。”
“为什么?”张宗昌诧异:“为什么不能打?”
“打?咱们打得不错、由天津一直打到上海,可是现在不能打,一打,大帅你的督军就打飞了。”
“怎么呢?”
“老郑是段芝老的小同乡,山东是皖系的一点根苗,只为张雨帅的压力,段芝老不能不听,其实是敷衍手段,正在找机会。咱们一开枪,好!他有话说了;到时段振振有词,以为防糜烂地方为理由,设法把你调走,你的督军还当得成吗?”
“人家要打,怎么办?”
“山东虽有十五个旅,愿意打的也很少。像第七混成旅旅长奇書網電子書胡聘三,他是老郑的台柱,他跟我同学,我就知道他不愿意打。咱们想办法,和平接受山东。”
“好吧,你去办。”张宗昌问:“你打算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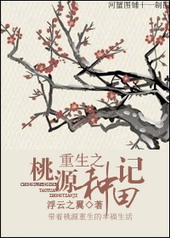
![(家教同人)[家教]浮云飞吖飞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6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