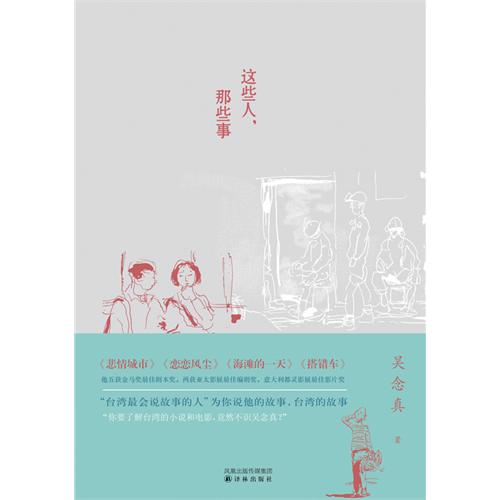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啊——菊菊!”
是菊菊,果然是菊菊!你终于来了……彭树奎像是从阴暗的洞里乍见阳光,又像刚从阳光里走进地洞,眼前一
阵金花,一阵黑暗,眼睛辣辣的,像是要哭。多少天了,他睡不着时想过,菊菊走丢了?掉河里了?遇到坏人了?……他睡着以后梦见过,菊菊坐在连部等他……红脸笑着扑到他怀里……现在,是真真实实的菊菊站在他面前了。她那曾是白里透红的脸蛋儿,变得憔悴了,像是大病了一场。她好像在笑,但那是强装出来的……
许久,彭树奎没说话,也没挪步。还是菊菊先开口了:“是二兄弟送俺来的……”
彭树奎这才看见,福堂老爹的儿子——当年领头抢馒头的二愣子站在一边。他赶忙说:“啊,二愣子,走,到班里坐坐……”
二愣子憨憨地笑着说:“不了,彭班长,菊菊姐走到俺村就病了,在俺家住了三天。俺娘让俺告诉你,菊菊姐还没有好实落,让你好好照看她。要是连里住着不方便,就还到俺家去。”说完,向彭树奎和菊菊道了别,走了。
彭树奎木然地领着菊菊往班里走,连包袱也忘了替菊菊拿。进了屋,才像冈缓过气来似的喊了一句:“菊菊!这么多天了,你……你是怎么来的呀!……”
菊菊一下子坐在铺上,双手捂住了脸……
她这一路上,简直像孟姜女千里寻夫一样……那公社革委会主任把一千元票子送给她哥后,就像买了个猪娃儿似的,立时拽她去登记结婚。她从早晨哭到晚上,至死不肯在结婚证上按手印。趁那主任出门的当口,她打开后窗冒雨连夜出走,连家都没敢回。她先躲到姑家,后又躲到姨家,眼看哪里也躲不住,就启程上路了。可姑姨两家也没凑够路费,坐车赶到离这龙山还有一百三十多里的县城时,身上分文没有了。她打听着往龙山奔,半道上求人搭了一次拉货的车,下车后又赶路。没有吃的,她个姑娘家放不下脸来去讨饭,就像做贼似的到沿途的菜地里摘几个茄子拔几棵葱,好歹填填肚子再赶路。奔到龙尾村时,她连饿加病晕倒了……眼下,要是有个背人的地方,她真想扑到树奎怀里哭上三天。可她强把眼泪咽下去了。
她见树奎眼里贮满了泪。
“树奎哥,你别难受……俺这不是好好的吗……”菊菊擦着泪说。
这一下,彭树奎的眼泪反倒止不住了。他两手抱着头,不敢张口。
“……世上总算还是好人多。福堂老爹一家子听说俺是来找你的,把俺接到家当了贵客待。老爹让二愣子给俺去抓药,大妈上顿给俺做面条,下顿给俺打荷包蛋。在她炕上躺了三天,大妈陪俺聊了三天,这就好好的了。”
彭树奎卷起旱烟吸了口,重重地叹了口气。
“听二愣子说,你们郭营长的那什么‘万岁事件’跟你还有点牵连。那年头老百姓都饿得趴在炕上起不来,营长带你去送小米,那才真是共产党办的事呢!共产党对穷人,哪有见死不救的?咱不怕那些!”停了会儿,菊菊又劝慰说:“树奎哥,你也知道,家俺是不能回了。俺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你提不了干咱也就别去指望了。你有的是力气,天地这么大,总有咱俩吃饭的地方。咱们去闯关东吧,去投奔俺舅!你还记得那比你大两岁的大顺子吧,人家闯了十几年关东,去年回家说上媳妇了,带着媳妇一块儿又走了。”
彭树奎羞惭地垂下了头。自己当兵九年了,难道也得像老辈子那样,像大顺子那样去闯关东求生……
“树奎哥,别老恋着这身军装了。”见树奎老不言语,菊菊又劝道,“年底快复员吧,千万别巴望着提干了,命里有三升,咱不去求一斗!”
“提干……咳!肯定是不行了。”停了一大会儿,彭树奎接上说,“为那‘万岁事件’,上级让我揭发郭营长,我……”
正说着,殷旭升一边高声吆喝着“树奎”,一边走了进来。
“这就是菊菊同志吧?路上受累了……”
菊菊忙起身让座。彭树奎介绍说:“这是殷指导员。”
殷旭升亲热地对菊菊说:“我也是聊城人,不远……哎呀,咋不提前来个信儿,让树奎去接接呀!你看你看……”他朝席棚外大声喊道:“通信员!把连部的暖瓶提过来!还有,告诉炊事班,中午加个菜!”
他诈唬了半天,才坐下来。“听说咱那儿新生政权都成立了?怎么样,形势挺好的吧?”
“……挺好。”菊菊望了彭树奎一眼,应酬道。
“你来了好哇,菊菊同志。歇两天,给全连介绍一下家乡大好形势吧。这对战士们是个鼓舞嘛!”
菊菊身上一阵发冷。彭树奎闷声闷气地说:“她拙口笨腮的,不会说啥。”
“哪能呢!这事以后再说。你们先歇着,我还有事儿,得空再来看你们。啊?”
菊菊起身目送指导员出了门,然后回头问彭树奎:“俺遇上的事儿,你没跟领导说?”
彭树奎难言地摇了摇头:“唉,跟谁说也没用……”
彭树奎面对菊菊坐下来,两双眼睛对望着。
菊菊身穿浅蓝色的土布褂,褐色的粗布裤,脚穿的黄胶鞋还是两年前树奎送给她的。她早已过了扎辫子的年龄了。墨黑的短发偎在衣领边……彭树奎倏地想起参军时菊菊剪掉的辫子,只觉得自己欠菊菊的感情债,愈欠愈多了。
半晌,彭树奎脸上才有了点笑模样儿,说道:“菊菊,正巧连里来了两个女兵,你就跟她们住在一起。好好歇些日子再说……”他翕动着发颤的嘴唇,再不知该说啥了。
“哒哒哒……”坑道口响起报警的枪声!
彭树奎“噌”地跃起,箭一般冲出席棚。
菊菊不知出了啥事,也跟着跑了出来……
第十七章
十七
坑道里一片惊慌,混乱。
“塌方了!快去救人……,’
“哪个导洞?”
“‘锥子班’的,一号!”
彭树奎的脑子“轰”地一声,像要炸开。他不顾一切地拨开挡路的人,朝导洞飞跑……
刚刚放过排炮排完烟,当班的四个班的战士正准备进洞作业。此时都抄起一件家什,朝一号洞口拥来。等彭树奎赶到,只见通往“一号”的台阶上已拥挤不堪。郭金泰站在导洞口厉声喊着:
“出去!都给我出去!……陈煜,你来把住洞口,谁也不许进来!”
彭树奎几乎是从人的肩膀上爬过去的。进洞一看,王世忠大半个身子都被压在小山似的乱石堆里……
郭金泰带两个战士采取紧急措施,在最要紧的地方支起圆木,以防塌方的余波砸着抢险的人。
彭树奎和其余的同志流着泪,气急败坏地喊叫着,拼死力救人。橇棍撬弯了,肩膀扛紫了,手指扒出血了……全班在嘤嘤的哭声中苦斗了三个小时,才把王世忠的遗体扒出来。
现场惨不忍睹。王世忠除头部完好,大半个身子已化做肉泥,与泥石粘在一起……
当天夜里,王世忠的遗体便被装进了棺材。
一片悲哀和惊恐的气氛,笼罩着“渡江第一连”。
“锥子班”的席棚里,全班呆呆地坐着,炊事班早晨送来的一盆馒头,到晚上还一个也没少。
消失了,一个孔武有力的人转眼消失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突然消失了!死个人难道这么容易吗?昨天头午,他还抱着钻机“突突”轰鸣;那一霎问,他还抱着支撑木龙腾虎跃……可现在,他睡过的床铺就在眼前,那叠得有角有棱的黄被还摆在那里,可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陈煜坐在马扎上,两手狠狠地搓着大腿,暗暗流泪。他气恨自己,他追悔莫及。
当时,看排烟排得差不多了,他像往常一样比别人提前十分钟进了洞,打着长手电逐段观察支撑过的拱顶。未等他发出可以进洞的安全号令,一心要争速度的王世忠带着孙大壮已来到他身后了。
就在这时,陈煜听见前面的支撑架上发出了疹人的响动:
“汩汩汩……”是山体渗水的声音。
“哗啦啦——哗啦啦一一”是大塌方前碎石滚落在木排顶上的声响。
“吱嘎嘎,吱嘎嘎……”是支撑木承受不了沉重的负荷,在扭曲断裂的呻吟……
他急转回身,伸开两手拦住走过来的王世忠和孙大壮:“前面危险,不要进洞!”
不料王世忠猛一下把陈煜推了个趔趄,弯腰抱起一根支撑木:“共产党员,跟我上!”
后面的人还未进洞,身边只有孙大壮。王世忠那声喊,反倒使他迟疑了一下,因为他是个团员。少顷,他还是抱根支撑木,跟着往前冲!
劝阻已来不及,陈煜猛地伸出右腿,给怀抱支撑木的孙大壮狠狠地下了个绊子!
孙大壮“哎哟”一声,被绊倒在地。他爬起来,刚要上前冲,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前面塌方了!
“班副——”陈煜和孙大壮连忙上前去救王世忠……里面漆黑一团,陈煜打开手电,只见王世忠已躺在石堆下,暴睁着两眼,张着嘴,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陈煜扑过去,不顾头上仍在纷纷下落的碎石,用身子护住王世忠的头:“班副!班副……”他希望能把他唤醒。从那一刻起,他忽然觉得,这个一直和自己针锋相对的人,是那么可亲!记得自己刚下班时,曾给会抽烟的战士每人一盒前门烟。一是想和大家表示一下亲近,二是希望大家在施工中多关照他这书生。不料正在卷旱烟的王世忠一下把那盒烟塞回他怀里,眼一瞪:“革命队伍内部,不要拉拉扯扯!”那一瞬间,羞得陈煜无地自容。面对王世忠,他感到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后来,他虽然处处看不惯王世忠那一套,却不能不佩服王世忠是个没有私心的硬汉子!
“当时,我为啥不给他也下个绊子啊!”陈煜痛悔地想。他无数次地顶撞王世忠,还时常玩个圈套让王世忠钻,每每使王世忠受挫,惟独这最后一次,陈煜的努力失败了……
彭树奎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他老想:如果我分配工作时硬一点,不准他抱钻机呢?如果后来我不离开导洞呢?如果我早点返回洞里……事情会怎么样呢?他感到内疚。他可怜这个副手,可怜他钻进牛角尖里倒不出来。他好像被谁打了一针吗啡似的,犟牛一样和这个顶,和那个斗,终于挣断了“缰绳”,为自己挣来了一死……不然的话,这是个多好的战斗骨干哪!
郭金泰躺在铺上,盯着天棚,脸色难看得吓人。
刘琴琴忍不住又哭出声来了。她今天才感到,陈煜的话没说错。她好像注定要和什么“悲剧”——牺牲的“山羊”打交道了……
席棚外响起一阵急促的哨音,值班排长吆喝集合。
全连列队站在连部木板房前那块平地上。
秦浩从吉普车中走下,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而来。
指导员殷旭升心吊到嗓眼里。连里出了这种恶性事故,不仅影响到全连的荣誉,更会影响到他的前途。
他在等待师政委的判决。
“同志们,世忠同志给我当过警卫员……对他的死,我无限悲痛……”秦浩声音喑哑,眼里似有泪光,“请大家脱帽,为世忠同志默哀……”
秦浩脱帽垂首,全连也都脱帽低头。
然而,秦浩可不是来寻找失败和悲痛的,他历来就是一只处处寻找成绩和光明的吉祥之鸟。
三分钟默哀毕。
“同志们,我们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秦浩昂起头,神情肃穆地说,“这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龙山是英雄辈出的地方!王世忠是‘渡江第一连’的光荣,是龙山工程的骄傲!……”
殷旭升的眼睛霍然一亮。
龙头崖上,出现了第一座坟。
第十八章
十八
陈煜和郭金泰一车一车地往坑道外运石碴,塌方的落石已经快清理完了。
郭金泰下到班里后,彭树奎有意安排陈煜伴着老营长一道干活。陈煜有文化,有见识,懂道理,陪着说说话,聊聊天,好解解营长心里的闷气。
下午一上工,陈煜就发现郭营长的情绪不对头,脸涨得通红,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于是便悄悄地问:“老营长,又怎么了?”
郭金泰摇了摇头,咆哮般地“嗯”了一声,最后恨恨地骂了句:“真他奶奶的‘英雄辈出’了!……”
原来,他中午看报纸时,发现省报的一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和一幅照片。从消息上得知,潍县战役之后,那个一次睡了地主两个姑娘的范书记,如今已成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并作为“拥军”慰问团的团长,将率领省歌舞团下到沿海边防部队慰问演出。照片上,姓范的美滋滋笑着站在几位女演员中间,笑得左额上当年被郭金泰一枪托子捣过去留下的那疤瘌,也好像变成了跟敌人拼刺刀落下的光荣标记……
他把那张报纸撕了个粉碎!
奶奶的,这“命”是越“革”越奇了!这些年,那姓范的又是怎样爬上来的,怎样爬上来的啊!……郭金泰想骂,想跳。可是跟谁骂?跟谁跳?
他感到自己像战场上误入了地雷阵。不是不敢举步,而是不能开口。一开口,不知哪句话就成了拉弦,撞响了“政治地雷”。真不如战争年代拼刺刀好受啊,那阵刺刀一端,怒吼一声,左劈右砍,血肉横飞,死也死得值得,活也活得痛快!可眼下,有嘴得装哑巴!
陈煜见郭营长又火顶脑门子了,赶忙把他拉到坑道口的石头上坐下来,递过一支烟,慢慢说:“营长,不管什么事,还是想开些才好。”陈煜压低了声音,“别说是你,连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老帅们,眼下又怎么样了呢!……像咱这些无名之辈,明知回天无力,也就不要勉为其难了。弄不好,又会授人以柄……”陈煜吐了口烟,意味深长地说:“营长,你也知道,我这个兵当得有点油了,玩世不恭。今天,你就听我这个兵油子送你几个字,叫做‘难得糊涂’……古人说:聪明难,糊涂更难,聪明而后糊涂尤难。其实这就是告诉人要学会装糊涂,所谓‘大智若愚’,就是这么个道理。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见识……”
抽了大半支烟,经陈煜这么一说,郭金泰心中平和些了。他猛然想起秦浩在雨夜跟他谈的那番话,便掐灭手中的烟头问道:“小陈,你研究过‘三国’吗?”
“读过。”陈煜不解地望着营长。
“官渡之战是咋回事?”
“嗯……官渡之战是实力雄厚、兵多将广的袁绍,跟曹操在官渡打的一仗。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