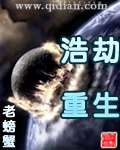花魁劫-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感觉在跟别的人讲话时,从来没有试过。
贺敬生并不漂亮,然,他轩昂,有气派,能慑得住人。
商家汉又能有个大学学位,在那年头,倍添身份。
我对这个还真有点虚荣感。
物以罕为贵。在大同酒家楼头出现的,难道还少腰缠万贯的富豪?独独就少有如贺 敬生般的有股读书人的气质。
当然,敬生来接我下班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还只是留在彼此敬慕的地步,很发乎 情,止乎礼!
这在当时,对我,更加必要。
说到头来,我不喜欢在仍有选择的情况下,当姨太太的脚色。
贺敬生第一晚要求送我回家,便坦白说:「我不会离婚的,太复杂,太划不来!
只是我妻总不是个难缠的脚色,她是旧式女人,对我于依百顺。」
我听完,微微笑,道了晚安,就径自回家去。
睡在床上,我想,冰清玉洁的一个人儿,既有机会出污泥而不染,何必淌这种浑水 !
从此,若即若离。
贺敬生是必要不放过自己的追求权利,就由着他去好了。
就是那一晚,他独个儿自斟自酌,等我下班。
我则被冯部长派去招待一位警署内的红员:洪照祥探长以及他的一班手足。
听他们说,只为刚破了一件棘手的奇案,于是跑到大同来庆祝。
洪探长几杯下肚,捉住了我的手说:「漂亮的姐儿要当心,像案中那个遇害的美人 儿,就是生成了观音似的面孔,招来横祸。要真是天生丽质,好歹找个有权有势的护花 使者,陪在身边,以策万全。」
说着,竟乘了几分酒意,捏着我的手不放。
做酒家女,至多也是牺牲色相到如此地步而已。
我初出茅芦时,遇上这种毛手毛脚的客人,还有七分惶恐。其后,经验多了,每每 是嘴上虚与委蛇,回敬几句好话,手就乘势抽出来了。
这回一样画葫芦,却不得要领。这洪探长力大如牛,紧紧的扣住了我的手不放,我 只好强舒笑脸,道:「怎么洪探长把我当贼般看待呢?像狠狠地给我上了手铐似的,我 还要腾出身子来替你们添酒呢?」
洪探长依然没有放松,声如洪钟地说:「不忙不忙,今晚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我只 要你好好的给我坐在身边,别的功夫且不去管它。」
洪照祥看了站于一旁的另一个女招待叫陈芷芬一眼,随即说:「芬姐,你来,替我 们和你的三妹妹添酒。」
我的面色剎那间阴睛不定,硬脾气快要使出来了。
芬姐跟我共事三年,晓得我的脾气,把情况老早看在眼内,慌忙打圆场说:「洪探 长肚子空空的灌下这么多好酒,怪不舒眼的,也是上菜的时候了,让我和小三捧些佳肴 来,让你们好好品尝,今儿个晚上,冯部长特地为你们留了一条极好的苏眉呢!」
芬姐趁势走过来,轻轻拉我的手臂。
我还未及反应,洪照祥一手拍打在芬姐的肩膊上,将她重重的推开,芬姐不防有此 一着,连连后退几步,掸到几上去,几上那个上好的花瓶就此摇摇欲坠,一晃眼,就跌 到地上去,粉碎!
「不识抬举!」洪照祥还口出狂言。
我使出吃奶的力,挣脱了他,一把冲前扶住了芬姐。
「你没事吧?」
芷芬摇摇头,示意我快快引退。
第二章
「怎么?不招呼我们了?我们的钱不是钱?」
那洪照祥就此站起来,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气得不能再气了,说:「请让开,我们没有一定的责任要招呼某些客人!」
「你敢踏出这房间半步?」洪照祥咆哮。
「为什么不敢?」
迫虎跳墙,我容壁怡有什么不敢?
十五岁时在乡间,姨母迫我嫁个虽无过犯,却面目可憎的男人,我也有胆子独个儿 自江门逃到深圳去,再偷渡来香港谋生。反正自出娘胎就是孤儿,我能自管自活得好好 的,是我的造化,要有逃不了的祸,也叫命了。
抢前一个箭步,我就冲出房间,下意识地直奔到贺敬生的那一桌去。
「敬生,带我走!」
贺敬生才拿起了外衣,洪照祥带着几个手下一齐拥上前,狠狠地看了贺敬生一眼。
「先生贵姓?」
「贺敬生。」
「名字好熟。」
「不敢当。」敬生拿身子护住我。
「贺先生盛行?我姓洪,小名照祥,在警界任事。」
「都是服务群众的行业,我任股票经纪。」
「既是江湖道上人,自知些少江湖规矩吧!这位容姑娘正在招呼我们那一席酒,还 未酒阑人散,她怎么就钻到别个客人的桌上去了?」
「她有选择权。」
「这可要问问冯部长了。」
那冯部长跟大同几个姊妹,包括芬姐,都知已出了事了,围拢上来,候准时机,以 化解这场恩怨。
因此,冯部长慌忙站出来,不住的打恭作揖!道:「这就给小弟赏光,好好的再坐 下来,让大同作东,请一瓶好酒,再唤几位姑娘侍候侍候。」
「容三姑娘可赏这个面?」洪探长伸出手来,作了个有请的手势。
我自别过脸去,看也不看他。
出道以来,从没试过这么令人难堪!
大同酒家跟我没有合同,要走就走,不见得我会饿死街头。
初来香港,人生路不熟,站在宵箕湾那几间纱厂门口,几个星期,才获得开工三天 ,肚子实在饿扁了,才转到大同酒家来应征。现今地头熟了,手上也有几个月的钱粮, 顶多重新到工厂排队去。
做酒家女这种拋头露脸的工作,已是我最大的极限,平日有谁对我稍为大声大气一 点的呼喝,也教我想掉头就走,别说要闹这么个不得体的笑话。
我若然就这么屈服了,难保没有茶客以为有先例可援,得寸进尺。
在往后的日子里,要是人们误会我畏强权,不知已委屈到何种地步去了。我岂非水 洗难清,无以自辨?
我当然屈服不得。
贺敬生只望我一眼,心领神会,说:「我陪你回家去!」
随即对冯部长说:「你如不满,我明天派人送支票来,小三辞职不干了。」
「贺少,且别这般认真嘛!」冯部长抓抓头皮,不知如何是好。
「姓贺的,你如敢带着容小三这就踏出大同半步,香港的治安如何?你好自为之。 」
贺敬生嗤之以鼻,说:「本埠乃法治之区,你的头是我的客户,不见得他像一些酒 囊饭袋,狐假虎威,置市民的安全于不顾!」
说罢,拉起我就走。
一路上,我们都默然。
心上突然间澄明一片。有种浓浓的被爱宠的感觉,侵袭心头,完完全全掩盖了刚才 的无依与惶恐、气愤与屈辱。
一个从没有过的念头,非常清晰的出现脑海里。
原来女人能有个自己喜欢的男人站在身边,是会矜贵百倍的。
我稍稍望了贺敬生一眼。
当这个男人出现后,很自然的,我不想他离去了。
我们紧紧握着手。
心上当然还有那一抹的阴影,同时交替着出现两个模糊的面谱,一个当然是贺敬生 的妻,另一个则是……不提也罢。阔别经年,再重逢,怕撞面也不相识了,还有什么指 望呢?
敬生陪我走回家去。
我住在荷里活道的一幢唐楼内,分租人家的一个尾房。
贺敬生从没有到过我家来,每晚都陪我蹬蹬的跑上了五楼,就话别了。
连今晚都不例外。
经历过这场风暴,大概彼此的心情都有点东歪西倒,需要静静的自行整理一下,始 日后算。
敬生轻轻的吻在我脸颊上,说:「好好的睡一觉,明天我来看你!」
我点点头。
等待明天。
明天终于来了,可是,敬生没有出现。
当芬姐面无人色地跑到我家里来,向我报道敬生昨晚在回他家途中被欧打的消息时 ,我吓得一颗心像要从张大的嘴巴掉出来似。
第一次见到贺聂淑君,就是在养和医院的头等病房走廊上。
眼前黑压压的一群人,个个面如土色,紧皱着眉,都有一副要冲前来跟我算帐的表 情。
我不是不恐惧的。战栗来自心底,却是根源于贺敬生的安危吉凶,并非为求自保。
我当然知道是自己间接地害了他的。
「你叫容壁怡?」这是那个自称是贺敬生太太的女人,给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点点头。
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哀伤都看不出来,却有一份令人惊疑不定,惴惴不安的冷 漠。
「请随我来,敬生要见你!」
芬姐仍拖住我的手,走进了病房。
贺敬生卧在床上,一眼见到我,下意识地移动身子,旁的人立即按住了他的肩,示 意他少安毋躁。
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扑倒在他身上去。
论关系,我和敬生还是朋友。
讲感情,我们没由来在旦夕之间跨进了一大步。
如许的融和,如许的亲切!
我只静静的站着,以眼神表达我深深的感受与关爱。
「你平安,我就安乐了!敬生闭上了眼睛:「我怕他们瞒着我,事必要看到你,我 才放得下心!」
眼泪一下子汨汨而流。
敬生再疲累地张开眼睛,说:「你先回家去吧!我好起来了,就会来看你,你放心 !」
我泪眼模糊,再看不清楚周围的人,是何嘴脸。
回到家去。坐到床沿,芬姐给我绞了条湿手巾,又泡了杯热茶,让我渐渐回过气来 ,她才悄悄地告诉我:「贺少是难得的有情人,只他那妻子,脸色难看至死,日后怕不 好相处!」
芬姐的顾虑并不多余。
当然,这是日后才知晓证实的事了。?当贺敬生身体康复过来后,我们便赋同居, 顺理成章的事似的。
我问敬生:「这城还是法治之区吗?」
「法治之区,法治之国,都有很多不便张扬的处置手法。人家以黑暗手段对待我, 我也投桃报李。你不必多管了。」
「可是,我们以后安全吗?」
「当然,已经惊动了上头,我有我的势力。总之,有我在你身旁,祸事断不会蔓延 到你身上来。我阻不了的,我会全身挡在你面前,就这么简单!」
最简单的事,从来最美丽,最令我欢喜。
我连旗袍都从来不尚花巧,不捆边边,不扎花纽。
敬生这么多年以来,深知我心!
再复杂的情况,到了他手里,都被简化掉。
自那次意外之后,真的没有什么可怕了。
稍稍经历过生死的人,那种再世为人的感觉,令人更超脱、更洞悉世情、更挥洒自 如、甚或更不顾一切。
似乎每一想起旦夕之间,可以有人撩是斗非,惹来公案,可能有人会取你性命,又 有人会拔刀相助,扭转乾坤,就觉得风险真不是一回什么事。
年轻时,有的是豪情壮志!
故此,再遇上七三年的股海风云,我有敬生在旁,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人既有旦夕祸福,钱财更是身外之物了。
能保得住人,就是上上大吉。
原来,我这种处世的思想与态度,令我和敬生的感情与关系,跨进了一大步。
就为了我肯把所谓私已,悉数由敬生变卖套现,他的一盘经纪生意得以复苏。
当然,也是命不该绝。那年头,不知怎的,敬生以我是女流之辈,或许喜欢押一些 宝金,竟然一直下来代我存放了不少黄金。也因为黄金最易脱手。反而留至最后关才打 算变卖,先行出售了物业,以维持手上的股票。
如此一来,七四至七五年的黄金价格不住上扬,使敬生先穷而后通。
直捱至七七年初,敬生拿了一块德辅道西的地皮出来,跟建筑商合作,兴建当时少 有的商住大厦,竟然其门如市,一下子就已翻了身。
这以后的三年,股市气势如虹,自不在话下了。
敬生一直将我的功劳夸大来表扬。
我但笑不语,心上极之安慰。
其实大方的人是敬生,取诸于他,用诸于他,他硬要说成是我的义气,怎不教人感 谢?
或许他以此为借口,令我名正言顺地踏进贺家的门吧!
聂淑君再无从反对。
因为贺敬生毫不让步地说:「股票跌至一百五十点时,我去叩聂家的门,商讨你父 以一个合理的价钱,让回聂氏百货的股票,都吃了重重的闭门羹。你一家大小几时分过 我的忧、解过我的患了?」
聂淑君无话可说。
当我恭恭敬敬地给她敬茶时,她才板起脸孔说:「不敢当。照理,是我带着一家大 小给你敬茶才对。敬生说,我们还有今日,是你的功劳。也真没想过才几年功夫,你能 积累到这一大笔,以救敬生燃眉之急。从此以后,我这个做姐姐的,倒要向你学习,好 歹多抓些金银珠宝作后备。以前我就是笨,克勤克俭,循规蹈矩,连家用都是稳扎稳打 ,才没法子逞强!」
并不需要多大的智能才能听得明弦外之音,唯其如此,才更显得说这番话的人之心 胸与气量,别说我不便多行辩驳,就算我有充分理由,我都宁愿选择随那些自暴其丑的 人去吧,何必斤斤计较?
聂淑君见我微垂着头,默默听训,并不打算得些好意须回手,只继续道:「原本贺 家的亲友们都劝我,既然容得你回家来,喊我一声大少奶奶,也得依规矩,给你一个别 名,好为贺家带来福气与好运!这虽是七十年代的摩登世界,仍有值得保存的老惯例。 然,我看你小三这个乳名也真易上口呢,但望以后小二、小三、小四全都是你一人,再 没有什么狐狸精跑上我们贺家的门来打扰就好了!我的那几个姑奶奶都说,壁怡的名字 总要改掉一个,应叫壁松还合心情环境一点,我看还是作罢,一喊壁松,倒提点了自己 ,是迫于无奈依从,蛮激心,是不是?这以后就依旧叫你小三算了!」
若不是敬生忍无可忍,一站起来,跑进书房去发牢骚,我看还有更多的难听话要听 进耳朵去。
事实上,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活受罪。
然,我常念,有人知道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