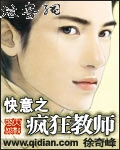李敖快意恩仇录-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衲”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姊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还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通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作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姊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世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姊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采绝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同,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大大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
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
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姊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凡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官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入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六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价格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黏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怠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床卜还撤些砂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仟,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村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则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迟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以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从二姊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姊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他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他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胀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突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凡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入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都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姊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姊陪我注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姊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卜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姊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未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人姊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宣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半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咪斤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个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掉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村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量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占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占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见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下。我赶快进套问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相反地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一九四八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村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匕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村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