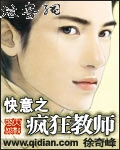李敖快意恩仇录-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jī巴还没长毛;如今jī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2 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
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对象,或者把经验同客观事物等同起来(贝克莱、马赫等);,庆祝我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升。我恨王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过程哲学又称“有机哲学”。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哲学理,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拭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立刻停骂了。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天培台大电机系毕业离台,蒋介石还看老居士老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情味于权谋之中,由此可见。李天培离台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独与我谈,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
“善培如还俗,我大没面子,盼李先生出面劝阻此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