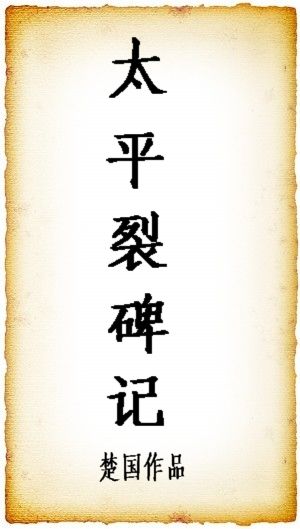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妈那个巴子的,居然是它,怪不得那味道很熟悉哩!小时候在竹林里不知见过多少回了——那是一支周身雪白,戴着一顶同样雪白的面纱,并扣着一个深绿色瓜皮帽儿的竹荪。
竹荪,又叫竹菌或竹姑娘,在我们当地很常见。只是,像眼前这只如此巨大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一般的竹荪,其菌柄最大不过锣锤大小,而眼前这支却粗如挑柴的钎担,直径少说也有十厘米,周身雪白,布满了细密的小孔;一幅巨大的网状菌裙从头到脚罩着菌柄,像灯罩子一样;深绿色的菌帽将落未落,犹如一个调皮娃儿歪戴着瓜皮帽儿。
浓郁的清香从这支竹荪身上散发出来,丝丝缕缕纷纷扰扰涌入我的鼻端,一时间,竟然扫除了我心中的杂念。我忘记了我在哪里,忘记了我在干什么,忘记了覃瓶儿……
又是大东西!大得超出常规!
我在清香中陶醉了一回,摇摇头,把思绪拉回现实。莫非真让我说中了,这段时间,遇到这么多大东西真的是对他人起着震慑作用?
前面遇到的怪蛤、摩芋树、地牯牛、龙桥、娃娃鱼、猴头鹰除了出人意料之大以外,或多或少有让人感觉恐怖的成份,而眼前这支大竹荪,非但不让人害怕,反而是,其英姿让人心旷神怡,其味道沁人心脾,又何来震慑作用呢?
我看着那支竹荪,越来越觉得它是如此美丽如此可爱,渐渐的,湿雾浸润了我的眼睛,模糊中感觉那支竹荪象一个身着婚纱的少女在我的神经上翩翩起舞,又像覃瓶儿在我面前扭动着她曼妙的身姿……
覃瓶儿?我如五雷轰顶,思绪彻底穿回现实,我这是怎么啦?
想起覃瓶儿,我想挣扎着站起来,继续找出路,却发现不知是寒冷还是长时间蹲着的缘故,我的脚仿佛石化了,动不得分毫。
我苦笑一下,准备继续努力站起身。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那支竹荪正在慢慢发生颜色上的变化。从它的根部开始,一层红晕正在渐渐浸润上来,那红晕是暗红的,类似血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奇怪,紧盯着眼前这只竹荪,心中转了千百个念头,难道这怪异的竹荪也会象姑娘一样“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以前见过的竹荪不会在光照下变色啊!
惊惧疑惑的同时,我注意到那竹荪身上的红晕越来越浓,越来越高,那层红晕自底向上慢慢延伸,半分钟不到的功夫,红晕就爬到了竹荪的腰部,而且,那红晕渐渐变成了红中透黑,与没有浸润过的地方那种雪白色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竹荪的躯体变得更加肿涨,活象一段煮熟的香肠。那竹荪的清香倒是越来越浓。
我打了个冷噤,注意到我的脸越来越冷,隐隐感觉浑身的血液快速向脚底涌动,双脚已经没有知觉,所以想站起身来变得异常困难。
我想抬头看看周围的环境,查找身体越来越冷的原因,竟然发现脖子已经不能转动,身体其它部分也僵硬了,不能动上分毫,全身上下唯一能活动的只有眼珠了。这种感觉,与做梦“鬼压床”一般情形。手电被我握在手中,白喇喇的光束静静地照在竹荪上。
意识倒还清醒,因此我心中既惊且疑。目光所及,那只竹荪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已经完全变成血红,随着它身上最后一丝雪白被血色吞噬,那暗绿色的菌帽被逐渐肿大的躯体顶掉下来,落在地上轻轻滚动两下停住,菌帽上看似乱七八糟的皱褶竟形成一幅诡异的笑脸,那笑,是那种不安好心的冷笑。
周围静静的,反衬得我的心如拖拉机般突突急剧跳动。随着心跳加快,我感觉周身的血液向脚底涌得更快了,而那只竹荪浑身的暗红,因为再无其它位置可以浸润,使得竹荪肿胀得更大了,渐渐的,竹荪已经大了三倍有余,而且菌柄与菌裙紧紧地贴在一起,转瞬间,就已经分不清哪是菌柄哪是菌裙了。
竹荪上渐渐浸出丝丝暗红的液体,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吞没了先前那股清香。不到一分钟时间,那竹荪就象一只被吹胀了的红色气球,更加诡异的是,这“气球”看上去虽然快胀到极限,却硬是没有炸开,我甚至看到竹荪的身体里,那血液竟然在快速流动。
在这个过程中,我周身越来越冷。垂下眼睑,我瞥见我的双手变得死白,嘴唇上也起了一层薄薄的冷霜。脚胀得难受,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流到脚底,看着越来越大的竹荪,我暗道难道我的血液竟然流到竹荪上去了?
——嫁血?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嫁血?
一件亲身经历的往事从逐渐模糊的意识中很突兀地冒出来。
我们当地有一句谚语:正月莫看鹰打鸟,二月莫看狗连裆,三月莫看蛇生巳,四月莫看人成双,这句谚语中的几种情形指的是动物在做那个事,如果某人该倒血霉,恰好在特定的时间看到这些情形,按照老班子的说法,轻则有血光这灾,重则有性命之忧。而我在七岁那年,就恰恰在二月里见到了所谓的“狗连裆”,当时不懂事,问正在挖地的爷爷,那两个伙计在做什么呢,爷爷一瞥之下,马上闭眼,急赤白脸地跟我说:“快莫看!快莫看!”说完拿起放在旁边的拐杖,在我身上点了一下,就抬着拐杖指着旁边一根青枝绿叶的小杉树说:“我孙娃儿在叫你看那两个畜生快活哩!”我对爷爷的举动不以为然,不过见爷爷心急火燎的样子,倒也不敢再看。
后来,我追着问爷爷为什么要喊小杉树看那狗连裆,有何讲究,爷爷叹了口气,说:“那是把你我身上的灾星转嫁给它哩!你信不信,三天过后,那根小杉树就会死!”“真的?”我不太相信。爷爷又叹了口气,没接话,沉默了半天,才对我说了上面的谚语,并一再告诫我以后如果见到谚语中的情形,千万记得仿照他的样子,把“灾星”转嫁给别的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最好不要转嫁给动物。我将信将疑,第三天去看那小杉树,已经死了,全身枯黄,与周围其它植物青翠欲滴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爷爷后来就说到“嫁血”。他老人家说的情形就跟我现在的遭遇一模一样,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全身的血液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转嫁”到其它动物或是植物上,最终的结局很恐怖——全身僵直而死。
想起“口不能言”,我才意识到想大喊一声,然而,别说喊了,就连微微张开嘴也不能够,而那只竹荪,就在我回忆的过程中,已经膨胀得象一个篮球,而且,是一个血红色的篮球……
第二十四章 土家图腾
越来越冷,意识已经模糊,感觉身体越来越轻却又越来越硬。
意识模糊,眼睛自然也模糊了。矇眬中,那只血红色的“篮球”膨胀得更大,大得几乎贴近我的鼻尖,将破未破。似醒非醒间,那腥甜的血腥味笼罩了我的整个脑袋。
当然,我此时心中早已没有了恐惧或惊奇,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至于覃瓶儿、满鸟鸟、寄爷、花儿等映像仿佛已经随血液流淌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
就在我感觉最后一丝意识快从身体里抽走的时候,“笃——笃——笃”三声异响象三根针一样从脚心刺入,我的意识霎那间就变得清晰明亮,人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而那篮球般大小的竹荪在我站起来之前,也像被突如其来的异响捅破,“啵”的一声炸裂开来,暗红色的液体飞溅起来,喷得我满脸都是,而那竹荪转瞬间就萎了下去,丑陋而湿溺地菌体无可奈何地挣扎几下,渐渐融成一摊血肉模糊的烂泥。
我顾不得再看那摊烂泥,也顾不得满脸的血污。左顾右盼一番,想弄清异响的来源。此时想起来,那异响异常熟悉,经过几秒钟的思索,我心中既惊且喜,那声音不正是我爷爷拐杖杵在地上的声音呢?尽管我爷爷已经去逝十几年了,他的一举一动,一频一笑,乃至狗头拐杖杵在地上的声音都象镌刻在我脑海一般清晰。
我东张西望搜索一番,没弄清异响的来源,周围的环境仍如先前一样若暗若明,而我身体也逐渐回暖,惨白的手开始有了血色,嘴皮上的白霜也开始融化,有了一丝温润的感觉。
我抬起脚,却“啊”的惨叫一声,感觉脚底有千百根牛毛针在扎,这当然是蹲久了的缘故。我跛着脚,吃力地在原地转了一圈,仍然没弄清那声音的来源。虽然我非常清楚爷爷已经去逝了,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哪里会想到那么多,心中早已喊了一千遍爷爷,难道我先前的祷告竟然起作用了?我爷爷竟然显灵了?没得说,回家就“寄钱寄车”。
只是,爷爷在哪里呢?周围除了那些默默静立着水竹等,哪有人的影子?难道这根冒出来的救命稻草又将从我手中滑落?
正在惶急之间,耳畔又传来三声熟悉的拐杖杵在地上的声音,我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应该是在我的右前方。忍着脚下踩在钢针上的剧痛,我拔腿就朝声音来源的方向急奔而去。
跑了一段,前面仍然没有人的影子,刚才明明听见声音应该在这个位置啊!
还没来得及细看,又是三声同样的声音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响起,我又向声音来源的方向跑去。脚下的不适经过跑动,已经轻了许多,基本上没感觉到疼痛了,所以我跑动的速度就快了很多。可是等我扑爬连天跑到声音所在的位置,仍然没看见人影。
就这样,那熟悉的声音一响起,我就不管不顾追过去。跑跑停停,当我第七次听到三声相同的声音,等我跟跑到那声音响起的地方后,天地间一下子就亮堂了,视线也看得远了,看得清了——我终于跑出了那几乎让我英年早逝的古怪环境,来到先前看到的那个岩隙边。
我长吁了口气,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的环境,两个几乎浑身赤裸而且浑身血红的怪人猛地扑到我跟前。“啊——!”我狂叫一声,转身就跑,感觉心脏就像摩托车轰了下油门,突突突……跳个不停。
“鹰鹰,莫跑,是我们!”背后一声熟悉的声音响起。
“满鸟鸟?”我疑惑地停下脚步,麻着胆子,转身看着那两个浑身血红的赤裸怪人。
等我终于看清那两个怪人确实是满鸟鸟和寄爷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心脏的跳动也慢慢变得轻快而有节奏。
而此时,那两个“怪人”又是另一番情形。
只见他们像练相扑一样,互抱着对方的肩膀,脑袋交替在对方的身体上胡乱擦拭。稍壮的那个人自然是满鸟鸟,他仅穿着一条花里胡哨地三角短裤——这条短裤我当然见过——本来就肌肉隆起的各个部件布满了血红色的条棱,象套着一件补丁盖补丁的紧身服。寄爷也裸着身体——相比而言,他老人家的肌肉就不叫“肌肉”而应该叫“肥肉”了——同样是红色条棱满身,随着身体的不断晃动,肚皮也跟着波澜起伏,就象腰上套着一个充气不足的红色游泳圈。
满鸟鸟边忙碌着,边侧头裂嘴朝我笑了一下,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吃力地说:“你龟儿子跑个铲铲啊?快把你脑壳拿来帮我止痒!”
我愣了下,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估计这两个伙计也是从那藿麻林中钻过来,但是没我走运,除了衣服,没有可以裹住身体的棕绳,才导致他们穿了这一身旷古奇闻的红“衣服”,那本来的衣服,肯定粘满了藿麻草的绒毛,如果坚持穿在身上,那与慢性自杀何异?
我在好笑的同时,心里唉叹一声,满鸟鸟是个猪脑壳,未必连寄爷这等高人也脑子搭铁,仿照我的方法,用头发去解满身的藿麻草毒?
“你杵在那里搓卵啊?你的良心被花儿吃了是不?老子们冒死来追你,你竟然见死不救?”满鸟鸟见我似笑非笑,站着不动,急了,嘴里开始冒“粪渣渣”。
我醒过神,见他们的神情痛苦不堪,忘了刚在心里骂满鸟鸟是猪脑壳,跑过去伸着脑袋准备去他们身上擦拭。
“等等,我有办法解你们身上的毒。”我及时刹住车,扯开那两个正在“练相扑”的人。
“你龟儿子有铲铲办法,快点,老子痒得直差刮皮了!”满鸟鸟高声叫嚷,嘴里的脏话就像涓涓细流连绵不绝。
我正准备反攻,想起他和寄爷最终还是没有抛下我,忍着如此大的痛苦追我而来,心里有点感动有点愧疚,所以,隐忍着满腔的“枪弹”不发。
寄爷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被我扯开后,他丑陋的脸对着我,让我吓了一跳,那哪还是一张人脸啊,嘴歪鼻斜,额肥眼肿,胡子象被野火扫过一般凌乱不堪,与画中的钟魁兄还要丑上N个档次,N大于等于五。
我也急了,拖起寄爷和满鸟鸟,就往水竹林中钻,刚靠近水竹林边缘,突然想起那莫名其妙的环境,这么冒冒失失让他们进去,他们会不会在里面迷路?
想到这里,我迅速解下腰上的棕绳,两头分别捆住寄爷和满鸟鸟的一只手,折成对折,再把对折形成的绳头牢牢捆在离水竹林边缘一米远的一棵青岗树上,“好了,你们进水竹林吧,等下就可以解去藿麻草毒。”
满鸟鸟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你这是么子波依办法?”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搞法!”我阴笑着看了他一眼,“快进去吧!少里鸡拉巴啰嗦!”
满鸟鸟和寄爷对视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双双哈着腰钻进水竹林中。
我的想法是,既然我身上的藿麻草毒可以在这诡异的水竹林中解除,让他们到里面去滚一转,兴许也可以解去他们身上的毒呢?既免了我脑袋辛劳,又可以让他们尽快免除痛苦,这是屙尿擤鼻涕——两拿的事,何乐而不为呢?他们早点解毒,我们就可以早点去搜救覃瓶儿,时间早一分,覃瓶儿的危险就少一分。人多力量大,撞鬼也不怕。通常说,钱是男人胆,这话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在现在这个场合,钱有毛用啊。依我说,朋友才是男人胆,人在困难时有友情支撑,那胆色自然壮大许多。
想是这样想,心里其实也难免十五个吊桶打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身上的藿麻草毒是水竹林中的雾气所解还是那只竹荪的香气所解,如果是后者,那就惨了,如果不能解毒,寄爷倒没什么,满鸟鸟那张破潲缸嘴还不把我“日绝”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算了,不想了。如果真像满鸟鸟所说,命中该吃卵,称肉搭猪茎,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猪茎也要吃下去,总比没肉吃要强。
我给满鸟鸟和寄爷捆上绳子,目的就是怕他们和我一样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