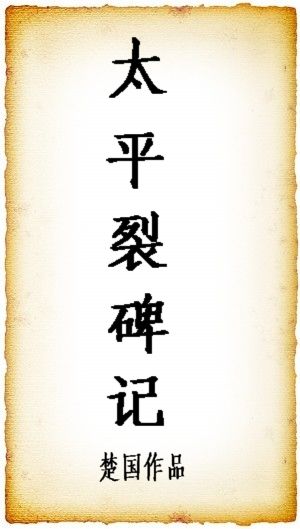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旋归来。
第二十二章 肉身(2)
而我爷爷,已经走进凉桥,离我有十几步的距离了。他没扭头,也没看两边跳茅古斯的人,自顾自在前边施施然走着,姿势正是他生前那种佝偻着腰的样子。
我到此时,仍没看见我爷爷的脸,而内心被强烈的好奇填满。看他老人家的穿着打扮,怎么和陈老形容的土家梯玛一样呢?难道我爷爷生前居然是一名梯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无论是他的装束,还是他手中的的怪刀、挂着六个铃铛的物件、悬在腰上的牛角,我都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见有人来请他主持什么法事之类的活动。
我忽然想到另一个人。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如洪水在我心中汹涌澎湃,一发不可收拾。
“清和大师!”我狂叫一声,顾不得害怕正在大跳“茅古斯”的那些人,撒腿就向那极像我爷爷的人追去。
那人走得不疾不徐,无论我跑得多快,却始终离我两丈多远,宽大的八幅罗裙完全掩住了他的身躯,我根本看不见他的脚是如何迈步的,那直差拖在地上的八幅罗裙也像从来没动过,没有丝毫飘逸的感觉。
“清和大师……清和大师……”我边跑边嘶声狂呼。
我口中的清和大师充耳不闻,默默低头走路。
不知追了多久,我无意从扭腰摆胯的“茅人”空出来的间隙中一看,发现几株桃枝挂满白色的桃花,斜依在凉桥栏杆外面。
这么说,我已经走到吊脚楼后那片桃林上面了?
就这么一疏忽,走在前面的清和大师就不见了,而且,桥两边大跳“茅古斯”的男人们也像被一阵狂风吹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立柱还是那黑色的立柱,栏杆还是那黑色的栏杆,瓦面还是那黑色的瓦面,桥面还是那白色的桥面,前方还是看不见尽头,而我,意外发现站在桥上的一个亭子中间,头上是一座宝塔式的亭阁,四条黑龙从亭阁的四个角上探出头来,口中各自含着一颗发出强烈白光的宝珠,昂首欲飞。
我疑惑地扭头一看,发现我走过的凉桥已经消失不见,就像我们当时在安乐洞中过那条埋孤坟的石桥一样情形。
我此时已经说不清是怎样一种心情,踯躅走近断桥边,探头一望,发现下面正是那片桃林,花团锦簇,枝桠纵横。再扭头向上一看,发现亭阁之上四条龙尾紧紧缠绕在一起,巧夺天工地构成了阁顶。
看见这个亭子,我心里隐隐觉得在哪里见过,感觉非常熟悉,想了半天,再次仔细看了一遍亭子的结构和样式,我霎时觉得心脏快跳出口腔——这亭子不正是道师先生口中描述的“望乡台”么?“一入望乡台,魂魄不转来。”这句话我爷爷也曾经说过,意思是人死后魂魄飘飘荡荡到了“望乡台”,再望一眼自己生前住的地方,魂魄就会真正进入阴间,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家乡了。
难道我现在不是在做梦,而是死了?我看见的那些裸女,那些男人,甚至清和大师难道都是阴间的阴魂?难道刚才那座凉桥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不对啊,各种传说中的奈何桥不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孟婆呢?那个给人喝忘魂汤的孟婆呢?
妈那个巴子,我决不相信我已经死了,这次的遭遇一定是其它原因造成的。难道是花儿的眼泪?难道它不但能使我看见平日看不见的东西,还会夺去我的魂魄?——日白!
我刚想转身看看没有尽头的凉桥,背后一股大力袭来,我像一只断线的风筝直直朝开满白花的桃林倒栽下去。
还没得及惊呼出声,我在桃树的枝桠上几经反弹,重重倒在雪白地面上,头顶前方是一条不知从何而来的檐沟,沟中正汩汩流淌着腥气扑鼻的黑水。
这檐沟,不正是和石牌坊前面那条檐沟一模一样么?这黑水从何而来?怎么……怎么有股血腥味?
正百思不得其解,我的身体瞬间僵直,不能动弹了。心神俱裂间,我竟被谁托了起来,转眼间就被放入那条流淌着黑水的檐沟,面孔朝上,顺着檐沟开始飘流。我的身体一接触那黑水,我的思想仿佛从身体里抽走了,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甚至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当意识再次稍稍恢复,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来到了那座石牌坊前面,并且是呆呆站着正对着石牌坊的大门。那三扇紧闭着的大门仍然紧闭着,而我,隐隐听到门里有狗吠声和女人的嘤嘤哭泣声。侧耳一听,那狗吠声和女人的哭泣声都很熟悉很亲切,再一回想,那狗吠声不正是花儿的声音么?而那嘤嘤的哭泣正是覃瓶儿娇媚哀婉的声音……
听见花儿的叫声和覃瓶儿的哭泣,我心中一下子轻松多了。只要覃瓶儿还在,只要她还安全,我就彻底放心了。但是,她为什么在哭呢?
听见覃瓶儿在门内哭得几乎肝肠寸断,我的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我走到那只石狮子前面,轻轻一跳,就跳到石狮子头顶,再纵身一跳,很容易就攀住了那堵墙的边缘,顺势撩脚骑跨在墙上,正准备跳下去,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傻愣愣地坐在墙上不再动弹。
那个哭泣的女人确实是覃瓶儿,尽管我看见的是黑白的覃瓶儿,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此时的覃瓶儿怀中抱着一个我很熟悉的人。那个人,没办法不熟悉,因为,那人就是我——满鹰鹰!
用布缠着的脚是那个人身上最明显的特征,那是覃瓶儿撕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帮他裹的。
此时的覃瓶儿并没注意到骑跨在墙头的我,当然,她不可能注意到一个阴魂。然而,她没注意到,站在旁边低声哀叫的花儿却突然抬起头来,定定看着墙上的我,汪汪吠叫两声,扑到墙下,前腿撑到墙上,徒劳地往上攀爬。
我看见花儿眼中溢出了眼泪。当然,那眼泪此时在我眼中是白色的。
我此时已经明白我确实死了,魂魄和肉身已经彻底分离。想明白这个问题,自从抹了花儿的眼泪之后的一切遭遇就很好解释了。
我心里一酸,轻飘飘地蹦到墙下,伸手去摸花儿的脑袋,那手虽然摸在花儿的头,却没丝毫触碰的感觉。花儿似有所觉,立起身来想舔我的脸巴,却直直从我身上毫无阻拦地扑了过去,我没产生任何身体接触的感觉。
我缓步走到覃瓶儿身后,想去摸她的肩,手却从覃瓶儿的肩上斜插进她的胸前。如果我活着,此时肯定是温润细腻满手,现在却没任何感觉,覃瓶儿的身体就像空气,或者说幻影更确切。
花儿应该能看见我的魂魄,见我去摸覃瓶儿的肩,覃瓶儿却一无所觉,折身回来咬住覃瓶儿的裤管,脑袋上扬,似乎想叫覃瓶儿站起来,覃瓶儿却不理,头垂在我肉身的胸口位置,哭得哀婉凄楚之极。
我叹了口气,缓步走到我的肉身头顶前,凝目一看,肉身双目圆睁,有一种死不瞑目的感觉,额头上那个已经不是“土”字的“土”字格外突兀醒目。
花儿又去拉覃瓶儿的裤管,覃瓶儿似有所觉,猛地抬起头来,惨白的脸上挂满泪珠,两只黑洞洞的眼睛定定看着我站的方向,黢黑的小嘴嗫嚅着说:“鹰……是你吗?”
第二十三章 瘟灯(1)
覃瓶儿能看见我?
我欣喜若狂,全身因激动而开始轻微颤抖,嘶声叫道:“瓶儿!是我是我!”边说边伸手去摸覃瓶儿苍白凄楚的脸颊,想要抚掉她脸上的眼泪。
覃瓶儿瞪着两只黑洞洞的眼睛,满脸凄楚迷茫,对我的手根本没任何感觉,雪白的上牙咬住下嘴皮,全身也像冷得打摆子一样微微颤抖。
“瓶儿……”我跳起来大叫一声,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换作平时,覃瓶儿肯定会被我这声高昂的鬼哭狼嚎吓得飞起来,可现在她对我的喊声一无所觉,连脸上的肌肉都没出现半点抽搐,我站在她面前,还不如一缕轻烟。
我内心充满绝望。“阴阳隔层纸”这是我爷爷生前在讲那些所谓“阴间”“阳间”的故事时老是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当时就想那层“纸”在哪里呢?“纸”后面的另一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层“纸”无处不在,那层“纸”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远得明明看得见自己心爱的人,却永远无法摸得着她,永远无法跟她耳语呢喃……
我脸上抽搐,两眼含泪,地上我那黑白分明的肉身一动不动。
花儿站在我的腿边,嘴巴一拱一拱,我腿上却没任何感觉。覃瓶儿痴痴站了一会,长叹口气,蹲下身子把那个肉身又紧紧抱在怀中,脸颊贴在肉身的额头,轻轻摩擦,双肩一抖一抽,又开始嘤嘤哭泣起来。在那层“纸”后面的我听见那哭声,心如刀绞。我长叹一声,终于体会到什么是“肝肠寸断”的滋味了。
花儿拱我的腿无果,抬起头来看着我的脸,眼角的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滚滚而下。
看见花儿的眼泪,一个差点被我遗忘的疑问泼喇喇涌进我的脑海——格老子的,我是怎么死的呢?这个问题想不明白,我可能一辈子寝食难安。当然,我现在的处境,也谈不上什么安不安的问题。
我仔细回忆了下,要说我躯体发生剧变,就是从把花儿的眼泪抹在我眼球上那时开始,在之前,我可以真实地触摸到花儿,从跳下围墙、闭眼奔到花儿身边,再托起花儿爬上石狮子,用绣花鞋挥断那条巨蛇……一直到发现覃瓶儿失踪,我都能清晰感受到真实世界的温度,跳下围墙时,我也能清晰感觉脚上传来的剧痛,甚至我手指沾上花儿的眼泪,我也能感觉那泪水的清凉,不像我现在做梦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出——除了能听见花儿和覃瓶儿的声音。
那么,我抹上花儿的眼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记得当时我把花儿的眼泪抹在自己的眼球上后,由于害怕,半天不敢睁眼,直到花儿狂叫一阵,我才下意识睁开眼睛,结果就看见了眼前的黑白世界……疑点出来了,在这个期间,花儿为什么会狂叫?根据它的性格特点,除非它看见或感觉危险临近,才会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吠叫。那么,它看见或感觉到了什么?我是否就是在那时进入那层“纸”后面的世界呢?如果确实如此,不管我现在是在做梦也好,死了也好,肯定当时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花儿那几声狂叫,也许就是我本人不同形态的临界点。
这个猜测还有一个佐证。按说花儿对我,绝对的忠贞不二,对覃瓶儿也情深意重,而当时我抹了它的眼泪后,准备让花儿跟我一同去寻找覃瓶儿时,花儿却出人意料地站着不动,我拿绣花鞋打它的脑袋它也没感觉,对我说的话也似乎听不见,说明我那时就是另一个形态了,花儿之所以站着不动,一定是守着我的肉身不肯离开,绝不是像我当时猜测的那样,因为疲惫或恐惧导致花儿驻足不前。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新的疑点:我当时怎么没看见自己的肉身?
我抬起头来,眼光无意落到石牌坊中门上的张飞像上,发现那张怒目圆睁、胡子巴胯的脸似乎饱含着讥诮——伙计,你不是笑我怎么沦落到这里做门神吗?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我眼光收了回来,记起当时我的注意力全部在那门板上的张飞、黑色兔子和那只鳖上,而且更急于想找到覃瓶儿,根本来不及去看周围的环境,没留心到自己的肉身与魂魄已经彻底分离就变得极为可能。再说,正常人哪会想会发生这样诡异的剧变呢?
现在,那具肉身在我眼前很清晰,尽管只有黑白二色。
说实话,关于传说的“肉身”我小时候倒真的接触过。我有一个远方同姓叔叔——当然不是满鸟鸟——是个“孤佬”,据说是阴间勾魂拿命的“无常”,白天与正常人无异,喝酒吃肉、犁地耙田样样精通,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一旦到晚上,如果有人和他同床睡觉,会经常发现他的身体变得和死人一样冰冷,鼻息也没了,脉搏也不跳了,唯余心窝处一团浅浅的温热。熟悉他的人都晓得,一旦他身体出现这种状况,肯定又是哪里要死人了,他去执行“勾魂拿命”的任务去了,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甚至有人跟他开玩笑,“满无常,你来拿我时打声招呼哈!狗日的好酒好肉不晓得招待了你几多,这点面子要给哈!”满无常只是笑,不答。冬去春来,人死得不少,从没听说过满无常在某人死前事先跟他打过招呼。我那时还小,屁都不懂,满无常有天晚上摸到我家混酒喝,酒醉饭饱就在我家睡了,而且就睡在我的床上,我半夜起来撒尿,无意中摸到他的大腿冷得像冰砣砣,再一摸其它地方,还是冷得像冰砣砣。我当时哪有人死人生的概念,也从来没接触过尸体,所以根本就没朝那方面想,只是在心里嘀咕,怪不得睡了半夜都睡不暖和呢,我以后再也不跟你睡了……第二天一早,满无常爬起来,笑嘻嘻地对惺忪着眼的我说:“走,看死去……”我当然知道“看死”就是有人死了,大伙儿都去帮忙办葬事。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我一夜冷得未合眼,根本没见他与任何人交谈,他怎么知道有人死了?日白吧?谁知我还未穿好衣服,就有人来请我父亲去帮忙扎灵屋……
我把这事儿说给爷爷听,爷爷才告诉我,我那远房叔叔是个“无常”,半夜勾魂去了,当然不是大大咧咧扑哒扑哒踩着方步去勾,而是先到阎王那里领任务,领完任务再以自己的魂魄去勾,魂魄和肉身分离了,所以身体才会那么冷。
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叔叔敬而远之,打死我也不愿跟他接触,别说跟他同床睡觉,吃饭都不敢跟他同桌,更不敢看他的眼睛,实在不巧碰到他时,我也是把脑袋勾到裤裆恭恭敬敬叫一声“叔叔”之后,撒腿跑得比飞机都快。
当然,这个叔叔早已去逝,不知是谁勾的他的魂魄。
我看着地上自己的肉身,忆起我那叔叔冰冷的躯体,暗想,我叔叔的魂灵是怎么回到他自己身上的呢?肯定有个什么先决条件——对了,极有可能是他心窝那团温热,当然还需要一种什么方法,游离的魂灵才能再次与肉身合二为一。那么,我肉身心窝上还有没有一团温热呢?那个让魂灵回到躯体的方法是什么?
我想起灵异电影中,魂灵回到躯体,通常是魂灵向肉身主动扑去,肉身就莫名其妙地复活了,呀地一声,鼻孔开始出气,接着就缓缓睁开眼睛……不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试它一锤子不就行了吗?
问题是,现在我的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