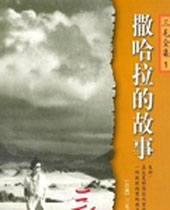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显见是舒拉认为舅父的提议侵犯了他的独立性和热心守护着的自主性。当谢尔杰解释应该怎样做的时候,舒拉在远处注意地听着,但是一言未发,谢尔杰也再没有往他那方面看。
哥哥临行,在门口,并不专对着某人说: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我就需要这些图。”
在他去后,卓娅打开了物理学课本,我和往常一样,看学生的本子,舒拉开始读一本小书。室中寂静了一些时间。卓娅站起来了,伸伸懒腰,晃晃头(她有这样的习惯——用疾速的动作掀起经常落在额上和右眉上的一绺黑发)。我知道功课已经作完了。
“该动手做工作啦,”
她说,“我们可以用一夜半的时间把它弄完,是不是,妈妈?”她就开始往桌上摊放图案。
舒拉放下书,瞥了姐姐一眼,不高兴地说:
“你坐着念你的《大学》吧(卓娅在那些日子正在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比你画得好,不用你,我也能做完。”
但是卓娅没听从,他们两人用图案把全部桌面占用了,我只好把我的本子挪到桌边。孩子们很快就深入到工作中去了。
卓娅这时就像往常在缝衣服、做饭或打扫屋子的时候一样,总之就是像在进行一种不需要人的全部精神,而只需要手眼准确的工作时候一样,她就开始了小声地唱:
草原上的野麦,绿色的芳草,宝石样碧绿的青草被风吹动了。
雷声虽已响过很久,那早年的往事却没被忘掉,它还在活着……舒拉最初默默地听着,以后他也小声地合唱了,以后更大声地唱起来了……两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很清脆,很协调。
他们唱完了关于一个在和盗匪们战斗中牺牲了的哥萨克姑娘的歌,卓娅就开始唱我们大家喜欢的另一支歌,这支歌从前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也唱过。
广阔的第聂伯在哭叫着,暴怒的狂风卷起了落叶,它把参天的茂林折到深谷,它掀起可怕的狂澜……他们就这样一边唱着,一边工作着,我也似听不听地听他们唱:不一定是词句传到了我的耳中,也许光是音调和他们唱歌的情感使我心里很舒服。
一星期后舒拉把完成了的工作送给舅父,并拿着一叠新的图案幸福地回家来了。
“他说:‘好!一星期之后给钱。’你听见没有,妈妈?我和卓娅挣来的钱!”
“谢尔杰舅舅再没说别的话吗?”我问。
舒拉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就笑了:
“他还说:‘这样比较好,舒拉老弟!’”
又过了一星期,早晨我醒来看见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两双袜子,一条很美丽的绸子的白领子,这是孩子们用他们首次的工资给我买的礼品。
其余的钱装在信封里一起放着。
……现在,在下午回家的时候,我时常走到楼梯上就听见我的孩子们在唱歌。
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又埋头在绘图工作中了。
蔚拉·谢尔杰夫娜
在旁观的人看来,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没有任何特殊事情地平淡地进行着。今天总是和昨天一样:学校和工作。有时候到剧院或参加音乐会,接着仍是功课,书,短时间的休息。这就是一切了。但是,实际这还远没有包括一切。
在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人的生活里,每小时全是很重要的。
在他的眼前不停地出现新的世界。他开始独立地思考,他不能不加考虑地便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一切他都要重新考虑和重新决定:什么好,什么坏?什么是崇高、尊贵,什么是卑鄙、下贱?什么是真正的友爱、忠实、公理?什么是我的生活目的?我是否无味地活着?生活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地在那年轻人的心中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即使他寻求和思考;每一件琐碎的事,他都会特别敏锐地和深刻地感受着。
书早已不是仅仅用来帮助休息和消遣的东西了。不,它是朋友,顾问,导师。
卓娅在小时候曾这样说过:“凡是书里说的,全是真理。”但是现在她却很长时间地思索每一本书,她和书争辩,阅读时寻求解决那些使她激动的问题的答案。
读完《丹娘·索罗玛哈传略》,我们又读了那永远不能忘掉的、对于任何一个少年都不能不给以深刻印象的那本讲保尔·柯察金的小说,那本讲他的光明的和美好的生活的小说。
它在我的孩子们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一本新书对于他们都是一桩大事:关于书中所叙述的一切,孩子们都把它们当作真正的生活讨论着:关于书中的主人翁他们常常进行热烈的争辩,或是爱或是非难。
遇着一本有智慧的、有力量的、正直的好书,是对青年有重大意义的。因为遇着了一个新人,就常常可以决定你的未来的道路,你的整个前途。
学校在我的孩子们的生活里向来是很重要的。
他们尊敬自己的先生,他们谈到教务主任伊凡·阿列克谢维奇·亚泽夫的时候,特别表示敬慕。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又是一个公正的教员。”卓娅这样重复过许多次,“他是一个多好的园艺家呀!我们称呼他为米丘林。”
舒拉每次讲到上数学课的情况都是愉快的,他讲到尼柯莱·瓦希里耶维奇怎样要求他们思考,研究,并说他什么时候都指责那些不思考或机械地死记数学公式的人。
舒拉这样说:“哎,他可不喜欢死背课本和像鹦鹉一样光会重复别人的话的人!
可是如果他看出来谁真理解了,那可就是另一回事啦。虽然有时候算错了,可是他只是说:‘不要紧,你别忙,想想。’的确,听到这样的话脑子就更好使了!”
卓娅和舒拉谈论他们的班主任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的时候总是非常喜爱的。
“她那样忠厚,谦虚!
她永远在校长面前维护我们。”
实在,我不只听到一次:如果在班里有人惹了祸,犯了错误,第一个维护他的人就是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
她教德文。她给学生们讲课从来没提高过声音,可是在她上课时候大家都很安静。她对待学生很宽厚,但是在孩子们的脑子里向来没有过马马虎虎地预备她那门功课的念头。
她爱孩子们,孩子们也以爱回报她,这个情况可以保证她上课时不发生纪律问题,学生在她那一门功课方面的成绩也没有问题。
但是从蔚拉·谢尔杰夫娜在她们的班里讲俄文和文学课以来,在卓娅和舒拉的生活上就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
卓娅和舒拉一向说话都要加以斟酌,甚至在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也很谨慎。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个性上的这一特点,就更逐渐明确了。他们像怕火一样地怕说夸张的话。他们两人全不轻易表示爱、温情、狂喜、愤怒和憎恶。
关于孩子们的这类的情感,关于他们的心境,我根据他们的眼神,根据他们的沉默,或是根据卓娅在伤心时候或着急时候如何在屋中由这一屋角到那一屋角往返地踱着,倒是能了解得更多些。
有一次(那时候卓娅12岁)一个男孩子在街上,在我们窗前虐待和逗弄一条小狗,他投石块打它,又拖它的尾巴,以后又把一块吃剩下的腊肠送到它的鼻前,在它正要张口咬住这一块美味的时候,他马上又把手撤回去了。这一切,卓娅隔着窗户全看得很清楚,虽然那时候已是深秋,她连大衣也没披上,就那样跑出去了。看她那时候脸上的神色,我怕她马上去大声叱责那男孩子,甚至用拳头去打他。可是她并没嚷,并且也没举拳头。
“别淘气啦!你不是正经人,你是坏孩子。”卓娅走到台阶上说。
她并没有大声地说,但是带着无限鄙视的表情,致使那个男孩子哆哆嗦嗦地一言未发就狼狈地侧着身子溜走了……如果卓娅说某一人:“他是好人。”那就足够了。我就知道了:卓娅很尊敬那个被她这样评判的人。
但是关于蔚拉·谢尔杰夫娜,卓娅和舒拉却毫不隐藏自己对她的钦佩。
“你要是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哪!”卓娅重复地说。
“什么样的呀?她为什么这样合你的心呀?”
“我简直不会说……不,我会说。你知道吗?她走进了教室,开始讲述,我们全知道:她不是因为功课表里有她的一门功课才给我们上课。
她本人是认为她所讲述的东西很重要并且很有兴趣。也看得出来,她并不需要我们把她所讲的全牢记下来,她只希望我们能思索和理解。同学说,她把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交给我们,让我们‘解剖’。真的,她说:
‘你们喜欢这个主角么?为什么?你们以为他应该怎样做呢?’我们甚至不等到她的话停止了,就全教室里的人都一齐说话了:忽然这个站起来,忽然另一个站起来……我们争辩,气忿,以后在大家都表示了意见之后,她自己就开始讲话了。她那样平淡地、声音不大地讲话,好像教室里不是30人,而是3个人一样。谁正确,谁错误,马上都清楚了。多么希望把所讲的东西都读一遍呀!
听了她讲述之后再读那书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见以往完全没注意到的东西。另外,我们现在是真正了解莫斯科了,因为这个我们应该对她道谢。她在第一课上就问我们:‘你们到过托尔斯泰博物馆吗?到过奥斯坦基诺吗?’她接着就很气忿地说:‘嗐,你们还是莫斯科人哪!’可是现在我们和她一起什么地方都去遍了,所有的博物馆都参观过了!每次她都要我们思索一下新看到的东西。”
“真的,她真是很好的人!”舒拉帮助她说。
他说这样富于情感的话仍是有些拘泥的,并且为遮掩他的羞涩,或者为使他的话听起来更肯定,他每次赞美这位女教员的时候都是用成年男子的低音来说,不过他的嗓子还不成。但是他的眼神和脸的表情则清楚明确地说:“她是好人,很好的人!”
可是,只有在他们班上开始了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什么是被唤醒了的对文学、对作家、对历史的兴趣。
最高的尺度
“您的女儿在专科学校读书吗?”有一次我按着卓娅开的书单向图书馆的女馆员借书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书单子向来是很长的并且包括的种类很多。为了准备写一个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什么书卓娅没读哇!既有深奥的历史著作,也有翻译的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和克列曼的作品。
她读了多少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著作呀!卓娅在梦中还念着库图索夫和巴格拉齐昂的名字和对战斗的描写,并且醉心地背诵着《战争与和平》的章句。她在准备关于伊里亚·木罗米次的报告的时候,给我开了一张很长的书单子,其中的书都是不常见的,为了搜寻这些书我跑遍了各样的图书馆。
卓娅会认真地钻研,寻找最深的参考书,研究事物的本质,把全部精神都用于所研究的题目上去,这一切我都不觉得新奇。但是她从来还没像这样把整个的心都用在研究一件事情上。遇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是卓娅一生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蔚拉·谢尔杰夫娜给孩子们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下了那一课,回到家里,卓娅就决然地说:
“我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你明白吗,妈妈?在学校里只有《怎么办?》。请你问问,你们的图书馆里还有什么。我希望得到完全的传记、书札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我想知道他的一生。”
这只是开头的几句话,可是我就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卓娅忽然变成好说话的人了。显见她需要把她和每一思想,每一发现,把她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所爆发的每一火星,都拿来和我讨论。
一次,她给我看一本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说:
“你看,这里说他在大学初年除了功课以外并没关心别的事,可是,你看他在那时曾托他的表兄翻译什么样的拉丁文的诗:
‘让公理胜利吧,不然就让世界毁灭吧!’还有:‘让虚伪消灭了吧,不然就让天坍了吧!’莫非这都是偶然的么?还有他给裴频的信里说:‘为自己的祖国争取永久的光荣和为人类谋幸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崇高的,更为人所热望的事呢?’妈妈,我不再打搅你了,可是再听一段吧。这是日记里记的,‘为了自己的信念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友好和快乐,为消灭贫困和罪恶,我毫不吝惜生命!假定我确信我的信念是公正的,并且一定胜利,那么我并不以我不能看见它们的胜利和实现为憾事。只要我确信这个,我就能为此而死去,并觉得甜蜜而不苦恼。’……你想想:既然这样,怎能说他除却功课以外不关心别的事呢?”
卓娅开始读《怎么办?
》以后就放不下了。她那样地专心读这本书,甚至有生以来第一次忘了在我回家之前给我温中饭。她几乎没看见我走进屋里来:她只是一刹那间抬起了头,用疏远的眼睛看了看我,好像没认出我来一样,马上就又专心读书去了。我没惊扰她,自己燃着了煤油炉子,把汤菜放在炉子上,又提起水桶往洗脸吊桶中倒水。这时候卓娅才猛然醒悟了,她跳起来就由我手里把水桶夺去了:
“你干什么,妈妈!我自己做!”
晚饭后,舒拉睡觉了。
以后我也躺下睡着了。醒来后,睁着眼躺了一会儿,不久我又睡着了。在深夜里又醒来的时候,发觉卓娅还在读书。于是我就起来,默默地由她手里拿过书来,把它合上,放在书架上。卓娅用抱歉和哀告的眼光看了看我。
我就对她说道:“在灯光下我睡不好觉,可是明天需要早起。”我知道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服她。
早晨舒拉忍不住不挑逗姐姐了:
“你知道么,妈妈,昨天她由学校一回到家里就沉到书里去了。只是读,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我看她快像拉贺米托夫那样在钉子上睡觉了!”
卓娅当时没有说话,可是下午她由学校里拿回来一本书,在那本书里曾引证了季米特洛夫论到拉贺米托夫的话,说俄罗斯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拉贺米托夫,在某一时期也曾是初参加革命运动的青年,保加利亚工人(指季米特洛夫本人)的好榜样。季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