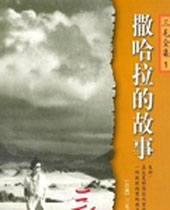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向彼得里斜沃进发了,那里有大批敌人。一路上我们割断了敌人的电线。夜间我们接近彼得里斜沃了,村子的周围全是葱密的林子,我们进入了林子的深处,在那里燃起了真正的营火。队长派出去一个男同志警卫我们,其余的人们都围火坐着。圆圆的、昏黄的月亮升上来了,已经降了几天雪,在我们的周围屹立着雪罩着的高大葱密的罗汉松。
‘这样的松树放在骑兵教练场才好哪!’丽达说。
‘是要有这样的装饰!’卓娅接着说。
以后鲍里斯开始分配最后的口粮,每人分得半块面包干、一块糖和一小块干鱼。男孩子们一下子就都吞下去了,我们不然,我们一点一点咬,为的是尽可能地多尝尝滋味。卓娅看了看她的邻人说:
‘我已经吃饱,不愿再吃了,给你吧。’她把面包干和糖向他递过去。
他最初还拒绝,以后就接受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丽达·布雷基娜说:
‘真愿意活着!’不要忘了这句话的意义!在这句话里含着极大的信心,相信在前头有长久的,美好的生活。
这会儿卓娅开始背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过去我一向没听见过她朗诵诗。这的确是不平凡:夜,雪罩着的森林,营火在燃着,卓娅小声地、清脆地背诵着诗,声调充满了动人的情感:
天空飞着黑云,雨压缩了黄昏。
在破车下躺着工人们。
上下的水都听见了骄傲的耳语: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也喜欢马雅柯夫斯基,并且很熟悉这首诗,可是在这里却像是第一次听见一样。
手足因潮湿而痉挛,泥水里的舒适不怎么好。
工人们在黑暗里坐着,嚼着泡湿了的面包。
但耳语比饥饿声音更大——
它咒骂着雨点: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回头看了看,大家全都丝毫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卓娅。她的脸又发红了,她的声音逐渐增强起来了:
我知道——
将来会有城市,我知道——
花园里将盛开着花朵,因为苏维埃国家有那样的人。
‘再来一首!’在她朗诵完的时候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卓娅就开始连续地朗诵她所能背诵的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她知道很多。我还记得她怀着什么样的情感朗诵了《大声疾呼》叙事诗的片断:
我要像举起布尔什维克的党证一样,举起我的一百部党性的小书。
我们就这样记着了这一夜:营火,卓娅,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您一定很喜欢他吧?’鲍里斯问。
‘很喜欢!’卓娅回答说,‘各样的好诗人很多,可是马雅柯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侦察清楚了地方情况之后,鲍里斯就开始分配任务。我曾听见鲍里斯和卓娅之间的简短的谈话:
‘您留下值班吧。’鲍里斯说。
‘我请求派我出去执行任务。’‘只是男孩子们出去执行任务。’‘应该平分艰苦啊。我请求您。’‘请求’这两个字她是像‘要求’那样说出的。队长同意了。我侦察去了,卓娅到彼得里斜沃执行任务去了。她在临行的时侯对我说:“咱们换换手枪吧,我的比较好,可是我使用自己的和使你的全一样。她拿去了我的普通七星手枪,把自己的自动七星手枪给我了。这支手枪现在仍在我手里,它是图洛工厂1935年出品,号码是12719,在战争终了以前,我决不和它分离。
卓娅完成任务回来是变了样子——只好用这句话形容她。她放火烧了马厩,烧了住房,她相信希特勒匪徒也在那里烧死了。
‘做了真正的事之后,心情完全是另样的!’她说。
‘难道以前你什么事也没做吗?你出去侦察过,割过电线……’‘究竟不同!’卓娅打断了我的话,‘这点儿事太少!’经队长许可后,她又往彼得里斜沃去一次,我们等待了她3天,可是她没回来。其余的事您都知道了。
卓娅对我讲过,说您的一家人是彼此很亲热的,差不多没分离过。所以我深信,我能告诉您的这一点事,对于您一定也是宝贵的。我虽然认识卓娅仅仅一个月,可是她对于我也和对于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们一样,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光明最纯洁的人物之一。
在您来到彼得里斜沃的时候,我也曾看见您的儿子舒拉,他曾在卓娅的坟前挨着您站着。卓娅对我这样说过:‘我和弟弟俩谁也不像谁,我们的个性完全不同。’可是我看见舒拉之后,就知道他们的个性是相似的。我如同现在还看见他一样,记得他站着,看着卓娅,咬着嘴唇,但是不哭。
我没有安慰您的话,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话,我知道在世界上没有在您的悲伤中能安慰您的话。但是我愿意告诉您:卓娅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不死,也不会死的,她活在我们之间。
她将鼓舞很多人奋起斗争,她的壮烈行为将给很多人照耀道路。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的爱,您的女儿们和儿子们的爱,在我们的全国土地上,将永远围绕着您。
克拉娃。”
###我去彼得里斜沃数日以后,无线电播出了卓娅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的消息。
……3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往克里姆林宫去领取卓娅的证书,迎面吹来温暖的春风。我在路上想着:“卓娅不能看见这个了,永远不能看见了。她曾爱过春天,现在没有她了。她不能再走过红场了,永远不能了。”我和舒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悲思,我们无论想什么,我们每次向前迈一步,都忘不了这个。
并没需要我久待,很快地就把我领到一间大厅里去了。我并没一下子就看清周围,了解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桌子后边站起来了。
“加里宁……米海尔·伊凡诺维奇……”我忽然醒悟了。
对,是加里宁迎接我来了。他的面貌是我凭着照片看得很熟的,他在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我也看见过他不只一次。他的仁慈的微微眯缝了的眼睛,永远是微笑着的,可是现在它是严肃的和悲伤的。他完全是白发苍苍了,并且我觉着他的面容是那么疲倦,他双手握了我的手,小声地、非常亲切地祝我健康和坚强。以后他把证书递给我。
“纪念您的女儿的崇高的功绩!”我听到他说。
……一个月以后,卓娅的遗骸运回莫斯科埋葬在诺伏捷维奇公墓了。在她的坟上竖立了纪念碑,在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卓娅曾做为标语、做为座右铭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并用自己的短短的生活和死证明了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做的斗争了。”
舒拉
我和舒拉两人的苦难日子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念的——我们希望团圆,相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搂抱我们的卓娅。每次走近邮箱的时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给我们传来关于卓娅的消息。现在我们由它前边走过去连看也不看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欢喜的东西。
我父亲由杨树林寄来了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卓娅的死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在信里写道:“我不了解,怎能这样?我,老头子,倒活着,可是她没有了……”这几行字里含着多少无法解除的痛楚和悲伤啊!全篇信上都是泪痕,有几个字我始终没有能认出是什么来。
“可怜的老人们……”舒拉读完信小声地说。
舒拉现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我。他在过去像怕火一样怕表示温情,可是现在却对我很温柔了。现在他总是用他从5岁以后再也没用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现在他已经注意过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开始吸烟,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烟,那就是距离落泪近了。看见我找纸烟,他就注视着我的脸,走近我说:
“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请求你,我请你不要这样……”
如果夜里我不睡觉,他总能感觉出来。他走近我,坐在床边,默默地抚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无依靠了。舒拉成为家长了。
下课后(学校又恢复上课了)他就马上回家,如果没有空袭警报,他就坐下看书,在看书的时候他也不忘掉我。有时候他小声地招呼:
“妈妈!”
“啊,舒拉……”
于是他又继续专心读书。可是隔一会儿又说:
“你没睡吗?你听着……你看,说得多好哇。”他就给我朗读他特别欣赏的那一段。
有一次,他在读克拉姆斯基的书信的时候说:
“你看,这有多么正确:‘美术家的最宝贵的品质是心。’好吧,我这样了解:不仅是要会看见还需要理解和感觉……
唉,妈妈!”他忽然高兴地喊道,“不知道战争完了以后我要怎样学习呀!……”
另一次他问:“你没睡呀?我可以打开无线电吗?好像播放音乐哪。”
我点了点头,室中忽然充满了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中的华尔兹的声音。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一切都是使我们伤心的事,这一桩事也不例外:卓娅最喜欢第五交响乐。我们默默地听着,不敢大声地叹气,我们怕空袭警报打断了音乐,因而不能听完……
在终曲奏完后,舒拉深信地说了:
“你看吧,在胜利那天一定要奏第五交响乐和终曲。你以为怎样?”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敌人被由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曾顽强地拚命抵抗。他们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占据了白俄罗斯,包围了列宁格勒,并且还向斯大林格勒突进。
敌人在所经过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烧和毁灭了。他们折磨人,拷打人,绞人,吊人。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残忍凶暴的兽行,和我们在这一次战争中所了解的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报纸烧得我们的手和心都痛,无线电传出的消息常使人惊得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听苏联情报局消息的时候咬牙切齿,以后很长时间还是皱着眉,紧握着拳头在屋里往返走着。他的朋友:细瘦的瓦洛嘉·尤里耶夫(这里在四年级时教过卓娅和舒拉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尤拉·布娄多、沃洛嘉·奇托夫和另外一个男孩子(这孩子的姓是聂杰里柯,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几个人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勤了,可是在我回家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讲话,急忙地都走了。
“为什么我一回来孩子们就走哇?”
“他们不愿意打搅你。”舒拉支吾地回答说。
由全国各处
有一次我由信箱里取报的时候,有几封信落在我的脚上了,我拾起来就打开了最先接触了的一封。在折叠地方有一个稍微磨损了的前线的三角印记,没有邮票。信开始就说:
“亲爱的母亲……”我读完了,就哭了。
这些信是不相识的人,黑海舰队的战士们写的。他们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们称呼卓娅为妹妹,并立誓为卓娅报仇。
从此邮局每天给我送来信。由什么地方寄来的都有!由各战线,由全国各地向我和舒拉伸出了那么多温暖的友好的手,那么多颗心转向了我们。儿童,成人,在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被法西斯杀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现在在战场上战斗着的人们都给我写了信,似乎他们全想分担一部分我们的悲伤。
我和舒拉受的伤太严重了,任何医药也治不好这个伤。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表示这个。每封信里洋溢着的热爱和同情心却温暖了我们,在自己的灾难里我们不是孤单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亲切的话来安慰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这对于我们真是宝贵,真能使我们得到鼓励!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后不久,有人轻轻地好似胆怯地敲着我们的房门,随着就走进来一位不相识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脸上肤色微黑,头发剪得很短,两只大眼,只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蓝色的。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娅来。她羞涩地站在我前边,手里揉搓着头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着我说:“我是由军需工厂来的,我……我们青年团员们……我们全体请求您!请您参加我们的团员大会……并且给我们讲话。我们请求您,请求您!我了解这对您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我们……”
我对她说了,我不能讲话,但是我一定到会。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设在莫斯科郊区,周围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导看出我心中的疑问,就对我简单地解答说:“落下一枚炸弹,着火了。”
我们走进工厂俱乐部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首先我看见的是卓娅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边墙上看着我,我悄悄地在旁边坐下听着他们。
讲话的是一个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说已经第二个月计划未能完成了,他的态度很气愤,很激动。以后一个年龄较大些的登台说,熟练的人在车间里一天比一天少,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徒们身上了。
这时台下有一个人喊着说:“可是多么冷呀!车间比冰窖并不强!手都往铁上粘!”
我的向导猛然转身向他喊道:“你真不害臊!问问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来了,并请求了许可我发言。他们请我登上不高的讲坛。在我向前走着的时候,像片上卓娅的眼睛始终正视着我,现在卓娅的像已经在我背后,稍微旁侧,好像她站在我肩后看着我。但是我没讲关于她的事。
我说:“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姊妹在前线上,每天、每小时都牺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着饥饿……每天都有人们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下……”
不,我不回忆在那时候我说的话了,我不记得那些话了,可是注视着我的青年们的眼睛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