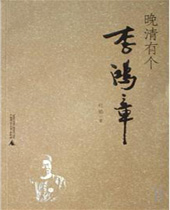李鸿章-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过一面。为人很深沉的样子。”
“深沉就好办。”刘不才有了信心,“深沉的人,利害关系看得透,讲得明白,就怕刚愎自用,蛮不讲理。”
“那,那就不妨说明了,请一起来谈。”
刘不才同意他的办法,趁这等待的片刻,要作个准备。一眼瞥见廊上有个俊俏小厮,心中一动,猜想就是王锡驯所说的那个已为他收买了的,蔡元吉的小马弁,一问果然,便将他找了来,有几句话要问。
先是和颜悦色的闲谈,问他的姓名、年岁、籍贯。那小马弁叫贵福,自道是苏州人,七岁的时候,随家人逃难失散,为蔡元吉所收容,至今八年了。
“你们‘王爷’待你好不好?”刘不才问。
“当然好。”
“‘王爷’的夫人呢?”
贵福摇摇头不答,脸色变得不大好看。刘不才看他那模样,心中明白,贵福必是蔡元吉的娈童,与蔡元吉的妻子等于“情敌”,相处得自然不会融洽。
这样一想,便从腰上解下一柄小刀来,递了给贵福,“来,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这把刀你留着玩。”刘不才说,“将来我要邀你们‘王爷’到上海夷场上去好好逛一逛,那时候再送几样新奇有趣的洋货给你。”
贵福童心犹在,接过那柄雕镂极精的牙柄小刀,爱不忍释,笑嘻嘻地不住道谢。
“我倒问你句话,你家的那位大舅老爷,听说脾气很好,是不是?”
“好?”贵福睁大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撇撇嘴说:“不晓得好在哪里?”
“怎么呢?”
“从来没有看他笑过。除非——”贵福双手一比,“除非看见大元宝。”
原来贪财!刘不才已心里有数了。“还有呢?”他觉得无须绕弯子说话,直截了当地问道:“他还喜欢什么?”
“多得很!喜欢女人、喜欢赌——赌品最坏,没人喜欢跟他赌。”
听这一说,刘不才更有把握,看看蔡元吉去的时间不少,怕他回来发现贵福在此,心生怀疑,反为不妙,便点点头说:“好了。我就问你这两句话。你请吧!”接着,又在荷包里掏出一枚由大内所传出来的金钱,塞到贵福手里,作为额外的犒赏。
其实是过虑了。刘不才等了好久,才见蔡元吉回席,后面跟着一个人,瘦而长,脸上棱棱见骨,一双眼睛似乎黯淡无光,但瞒不过这几年阅历江湖,经过大风大浪,见过三教九流的刘不才,他那一双眼睛是有意掩饰光芒。凡是善于“装羊吃象”的人,都有那么一双眼睛。
最使刘不才触目的是他那一身装束,一件旧宁绸的皮袍,油光闪亮,真像所谓“敝裘”,然而“敝”在面上,骨子里一点不敝,卷起的袖口,雪白的毛片,蓬蓬松松,耸得老高,是件极珍贵的白狐皮袍,衬着大拇指上一只碧绿的斑指,越显得夺目。
那只套着斑指的大拇指,薰得黄中带黑,再看食指、中指亦是如此。刘不才明白了,贵福还少说了此人的一样爱好,他是鸦片大瘾,那几只手指就是让鸦片烟薰黄了。
“我来引见。”蔡元吉指着那人说,“是我内兄,姓杨,行二。”然后又道了刘不才的姓名。
“啊,杨二哥!”刘不才抢着套交情,一揖到地,“我早就听说杨二哥了,今天真是幸会。”
杨二也拱手还揖。跟王锡驯是第二次见,无须寒暄客套,只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然后坐下首作陪。
几句门面话说过,杨二问道:“我们要请教,刘爷是在哪里,听说过我?”
“在上海。”刘不才胡诌着,“在上海就听说,‘听王’那里第一大将是蔡爷,蔡爷又全靠杨二哥辅保。”
真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杨二听他这话,那张“面无四两肉”的驴脸,立刻就有了喜色,“不敢,不敢!”他说,“只怕是误传。”
这一态度,就让刘不才完全将他看透了。他不是什么忠心耿耿,只知道“天王”的长毛,对官军并没有什么难解的敌视。然则,反对蔡元吉归顺,亦只是未餍所欲,有意刁难而已。
转念到此,刘不才越有把握,态度也轻松了,饮酒吃肉,谈笑风生,与先前那种沉重的脸色相比,判若两人。
蔡元吉自不免诧异,而他的困惑,只要一显现出来,刘不才立刻就明白了,“蔡爷,你觉得奇怪,是不是!”刘不才说:“我一条性命捡回来了,怎么不开心?”
“这话,”蔡元吉问:“是怎么说?”
“有杨二哥出面来,事情一定可以谈成功,我就不会好心不落个好报,岂不该高兴,”
“这位,”杨二指着刘不才问,“说的什么?我好像没有听清楚。”
“刚才不是跟你谈了嘛,人家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的。”
“是的。”刘不才说,“我到了这里,才知道人家猜得有道理,我倒好像太相信了朋友了。这些话不必去说他,在杨二哥面前,说了就不够意思了。”
这些语意暧昧,不知所云的话,没有一个能听得懂,杨二只猜出一点意思,刘不才很看重自己,而且很愿意交朋友。
同时他也觉得刘不才是个世故熟透的外场人物,这个人可以交,然而要些本事,一无长处的庸才,他是看不上眼的。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杨二便处处要逞强显能了,口讲指划,从淮军的程学启,批评到已死的谭绍光和长毛中公认的悍将陈炳文,说得他们一无是处。只是对李秀成却还保持相当的敬意。
他的话当然也有些见解在内。然而真如上海夷场上所说的“开口洋盘闭口相”,话一多了,底蕴尽露,肚子里有些什么货色,都让刘不才掂出斤两来了。
席间都是些闲话,王锡驯急在心里,一言不发,反倒是蔡元吉忍不住了,“谈谈‘那面’吧!”他特意提一个头,希望言归正传。
“不忙,不忙。”刘不才看准了才二十六岁的蔡元吉为人老实,因而喧宾夺主地自作主张,“回头我跟杨二哥靠烟盘的时候,细细斟酌。”
于是酒醉饭饱,“开灯”谈心,杨二等十六筒鸦片烟抽过,精神十足,抱着把乾隆窑五彩的小茶壶开始谈到正事。
“刘兄,你行几?”
“行三。”
“那就是刘三哥。”称呼一改,更显亲热,刘不才身子往上缩一缩,弓起了背,将头靠得极近,听杨二低声说道,“彼此一见如故,我倒要请教,刘三哥,你这样子热心,贪图的啥?”
“做生意啊!”刘不才答道,“舍亲朱观察是杭州人,从前王中丞在世的时候,他是浙江官场上一等一的红人,你总听说过?”
“听说过。然而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
“现在就要靠你老哥了。能将令亲说服了,拿队伍拉过去,舍亲朱观察就在这上头算立了军功,‘保案’一上去,仍旧回浙江官场,老实说一句:就都是他的天下!那时候,自然忘不了你老哥。”
“不会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于舍亲有什么好处。现在是同船合命,连左制军在内,都要靠这里。”
“刘三哥,你的话倒说得还实在。”杨二不由得说了真心话,“有些官军,一面孔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把我们贬得一文不值。我就不服!大家真刀真枪,上过明白!”
“照这样说,杨二哥,你大概先当我也是那样的人?”
“这也不去说他了。我倒再问一句:如果我们不过去呢?”
“那,那就只怕要看别人的热闹了!”
“这是怎么说?”
“好比赌台上一样,一上了‘路’,一定要下注,错过一注,心里懊悔,手上就更加谨慎了,要看着再说。结果呢,越看越下不了手,岂不是只好看别人的热闹?”
听这一说,杨二的心就痒了。然而这是拿赌作譬仿,到底不是真的赌,而且一输亦不是输钱,而是输身家性命,所以他不能不强自按捺纷乱而兴奋的心情,仔细看一看,到底是真的上了“路”没有?
抹不掉的是苏州杀降的影子,“刘三哥,”他只有这样问:“你是你的看法,庄家又是庄家的看法,明明看是活路,作兴是在钓鱼。我们跟你的身份不同,一上了钩是再也逃不掉的了。”
刘不才点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上钩不上钩,先不去说它,如果你自己当自己是一条鱼,那就要睁大眼睛看一看,一座池塘,四面有缺口在放水。水放光了,鱼就死了!活活困死,杨二哥,你不甘心吧!”
杨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处于将涸的池塘中,“那条鱼,”他问,“如果从缺口中冲了出去,龙归大海,岂不逍遥?”
“不见得。缺口外面作兴布着网。”刘不才灵机一动,立即改口,“不过,你跟令亲的处境不同,如果你想从这个缺口冲出去,我倒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噢!”杨二深深看了一眼,“怎么冲法?”
“船就在海塘外面。这条船有常捷军的旗子,官军的辖区通行无阻。你想到哪里,到哪里!”
杨二不作声,取起那盏有名的所谓“太谷灯”的烟灯灯罩——整块水晶所雕,用一方手帕擦了又擦,十分起劲。这好整以暇的动作,恰恰表现了他内心的紧张。
刘不才不肯错过机会,紧接着说道:“我倒替你想好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包你安安稳稳,无风无浪,舒舒服服地过一生。”
“是,是哪里?上海?”
“上海,夷场上!”刘不才说,“现在好多长毛在那里,尤其是手里有积蓄的,更加适意,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洋人不都帮官府的吗?”
这就是提出一个疑问:洋人帮官府,官府指名索人,则夷场亦不足以成为逋逃薮。这当然是不明白夷场情况的话,刘不才便从容陈说,将官府的势力达不到夷场的事实与原因,一一道来。在杨二便有顿开茅塞之感了。
“刘三哥,”杨二毕竟撤尽了藩篱,“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替我们开了两条路,我们决定挑一条路走,请你稍为等一等,我一定有切切实实的回话给你。”
“好的!”刘不才隔着烟灯拉住他的手说:“我们都是‘脚碰脚’的朋友,一切都好商量。”
“我知道。”杨二答说,断然决然地,“我赌了!”
他的想法是,举家——包括蔡元吉一家在内,带着搜括来的金珠细软,当夜就搭刘不才坐来的船到上海,以夷场为安乐窝,安度后半生的日子。然而蔡元吉却不是这么样。
“手下的弟兄呢?”他说,“我们不可以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只问你一句话:姓刘的信得过,信不过?”
“信得过。”
“那好!”蔡元吉毅然决然地说,“我年纪还轻,还想做一番事业,躲到夷场上去过无声无臭的日子,我不干。”
听得这话,杨二颇有意外之感,因为他这个妹夫,一向听他的话,说什么,是什么,不想遇到这种重要关头,却会自作主张,而且主张相当坚决。
“二哥,”蔡元吉又说,“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我决定带着弟兄过去,你如果想到上海,你管你走吧!”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既属至亲,患难相共,说不出独善其身的话,呆了一会说道:“做事要留退步,我倒有个两全之道,我送妹妹、外甥到上海。你过去以后看情形,能合则留,自然最好,不然就回上海,先守一守再说。”
“二哥,你倒真是一只手如意,一只手算盘,世界上那里有这样好的打算?”蔡元吉笑了。
“怎么呢?”
“你不想想,虎防人、人防虎,我们相信人家,人家是不是相信我们?”蔡元吉放底声音说:“家眷不过去,一个人去归顺,只怕来的这两位客人先就要疑心,蔡某人搞的什么花样?莫非送走了妻儿老少,后顾无忧,预备敞开来干一场?”
设身处地想一想,自然也觉得不能无疑。杨二倒没有主张了。
“二哥,”蔡元吉却稍为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我赞成你走。
你这两年舒服惯了,投过去了就能做个官,那种军营当中的苦,你也吃不来。倒不如现在脱身。狡兔三窟,你能在上海安个家,对我们夫妇总是一件好事。”
“好!那就这样。”杨二说道,“我们辛苦了一场,总要留下点东西,我替你保管。”
“这——”蔡元吉说,“只能带些细软,现银子不能带。”
“为啥?”杨二问道,“莫非还要孝敬官军?”
“这也不是。弟兄们的饷要发。”
“官军会发饷,何用你费心?”
“话不是这么说。左制军不比李中丞,他那里饷不足。就算能发,一时也运不过来。既然归顺了,一切总要为大局着想。”
杨二心想,能带兵又带饷去,必得左宗棠的欢心,对妹夫的安危与前程,大有关系。白花花的几万两银子,平空舍去,虽觉得于心不甘,也就只好算了。
***
定议以后,告诉了刘不才,他自然要帮忙照办——这件事其实于自己这方面有利无害,因为杨二与蔡元吉的财产转运到上海,自然要作营运,而做生意少不了自己这方面的关系,便等于增加了实力。
不过,这是隐匿敌产,事情要做得很秘密,所以首先就告诫杨二:“这件事要谨慎,千万不可张扬!请你悄悄去准备,等我来好好策划一下。”
等杨二背转,王锡驯立刻就紧张了,一把将刘不才拉到角落上,带着埋怨的语气问道:“刘三哥,你怎么冒冒失失去挑这副担子?挑不下来的呀!”
“担子很重,我知道,不过——”刘不才陪笑答道:“也不至于挑不下来吧?”
“唉!你老兄到现在还是这么不在乎的神气,真正急死人。
我请问你,两军对阵,相持已久,这方面看看支持不住了,那方面就要防备些什么?”
“这我不懂了!”刘不才依然是轻松闲逸的神态,“你老哥官拜都司,我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不够。你不要考我了,教教我吧!”
“也不是什么教不教。我跟你说吧,像现在这种情形,不管苏军还是浙军,都认为到了瓮中捉鳖的局面,要防的就是突围、偷漏,所以水陆两路的外围,一定加紧巡查。你想,杨二带了家小细软,路上岂有不遭拦截之理?”
“说得是!”刘不才深深点头。
“既然你明白,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带杨二过得关?”王锡驯很郑重地警告:“刘三哥,军队里的花样,我比你懂得多,像现在这种情形,真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