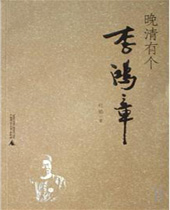李鸿章-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也是这样子想。朱先生,要捧孙老大,你还是另外动脑筋的好。”
众口一词反对,朱大器从善如流,立刻舍弃了他的想法。
于是小张便谈到帮助李小毛创业的事,想拿他可以到手的几千两银子,存在阜康钱庄,问朱大器的意思。
“这我就不便答应了。既然李小毛跟他师父有这样难解的过节,我只能跟他做生意,不能攀交情。不然对不起孙老大。”
虽然一口拒绝,但小张还是很佩服,觉得朱大器的立身处世,在灵活圆通之中,是非分明,确不可及。不由得连声答应:“是,是!这件事就不谈了。”
“还有件事,我也要交代。”朱大器又说,“大丰的老板娘,很帮我的忙,照道理说,我帮李小毛挖她的三千银子,是不对的。如果李小毛拿了这三千银子,另外去弄女人,拿她抛掉,这就显得我更加没有道理了。当然,大丰的老板娘怨不着我,而且她同朱姑奶奶一样,比场面上的男人还能干,还硬气,吃了哑吧亏,也不会说啥。可是,旁人要批评我,说我不上路。我带的人多,眼看杭州光复,我管的事,带的人还要多,不能不顾到全局,做一件事要能够摆在台面上大家来评。小张,这一层,你要原谅我。”
“言重!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朱先生,你恐怕也管不得那许多了。”
“不然。”朱大器说,“杭州灵隐寺飞来峰下的冷泉亭,有副对子:‘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凡事都有个根由,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不是从我这里过手拿到三千银子,他自然还是安安分分,陪着大丰老板娘过日子。你想想看,这个道理!”
道理容易明白,处置却真为难。“那么,朱先生,我倒请问你,”小张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一定要李小毛有句话,决不会做对不起粉面虎的事,你才肯付他那笔钱。”
“一点不错。”
“这怕难。”
“你跟他复交了,就应该劝劝他,他作的孽也够多了。不可再作孽。人总要讲良心,尤其是贫贱之交,糟糠之妻,不可以忘记。我再说一句,既然称到‘粉面虎’,就决不是‘偎灶猫’。帮里不是有句话:‘你做初一,我做初二’?等到粉面虎做起初二来,只怕李小毛就再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这个警告,连小张都有些入耳惊心,因而又是连连点头:“朱先生这几句话,倒是苦口良言。”
谈到这里,窗外咳嗽一声,是松江老大的声音,先报个信,他要进来了。窗内朱大器与小张的那番对白,他是否都已听到,无可究诘,反正关于李小毛的一切,话也谈得差不多了。为了尊重松江老大和他帮里的规矩,大家心照不宣,绝口再不提李小毛的名字。
接下来,便谈如何运米到杭州?以及到了杭州要做些什么事?朱大器这两年蛰伏,无所作为,大家都以为他豪气、魄力、冲劲,似都不如前,这天一夕之谈,方知不然!朱大器依然是那样锐于任事,也依然是那样计虑周详,而且也依然是那样凡事先为手下着想。
(第九章完)
第十章
这夜几乎谈了个通宵。各人该做的事,虽未曾一条一条列出来,但大致都有了定规,亦可以说各人尽其所长,自告奋勇将该办之事,一项一项都认了去。第二天开始,各人归各人去安排,而第一件事是,由松江老大派人专船到嘉兴去迎接孙祥太。
接到上海,照“家门”中的情份,自然由松江老大招待。
接风宴罢,松江老大先说:“老大!明天晚上,我们小叔叔专诚请你。你把辰光空出来,不要答应人家的约会。”
“这,”孙祥太问道:“‘专诚’两个字不敢当。朱先生有啥事情,吩咐下来就是。”
“言重,言重!”朱大器从身上掏出一个帖子来双手递了过去,“孙老大,你一定请赏光!”
帖子是全帖。礼数如此隆重,定有所谓,而且可以猜想得到,不是很轻松的事。但江湖上讲究的是“闲话一句”,即今明知是“鸿门宴”。亦无退缩之理。所以孙祥太反倒不作谦词了:“朱先生赏脸,我不能不识抬举,准到!”
“好极。”朱大器又说,“我的意思是诚恳的,不过也不是虚客套。特地借老孙府上摆桌饭,为的是请朱姑奶奶也好作陪。说句好朋友托熟的话,我虽没有蒙‘祖师爷慈悲’过,其实家门的兴衰,我跟两位老哥一样关心。”
“这倒是真话。”小张接口说道:“门槛内外都是一样的,只要讲义气,做事不违背祖师爷的道理,哪怕没有‘慈悲’过,照我想来,祖师爷一定也会点头的。”
“是啊!”孙祥太感慨又生,“做人凭心!心不好,哪怕上过香、磕过头、当着祖师爷立过誓,一点用都没有。”
这话当然是指李小毛而言的,说下去诸多不便,因而刘不才将话扯了开去。追忆前一两年出生入死的往事,颇多可谈,而官军毕竟打得还好,东南半壁,恢复旧观,只是指顾间事。因而展望前途,又谈到彼此协力,重整家园,做一番事业的计划。这样越谈越起劲,也越谈越投机。大家都深深感受到朋友之乐,不知不觉又谈了个通宵。
孙祥太每天要打拳,要溜马,见天色将曙,便索性不睡,说是一个人要出栈房去走走。
为了尽地主之谊,松江老大便要相陪,小张与他住一家客栈,起居更当相共,而孙祥太一概辞谢,意思相当坚决。最后又说,是有事要办;要去看一个朋友。既然如此,不必勉强,各自归去睡觉。
只有小张不大放心,“老孙,上海只怕你还没有我熟。这一两年夷场上格外发达,新辟了好些路,绕来绕去,越发难走,要不要我陪你去?”他情意殷殷地:“好在我也不困。”
“不必,不必!我一个人去。”
“要嘛,关照栈房里替你喊一乘轿子。”小张问道,“你的朋友在哪里?”
“在——”孙祥太答道,“我晓得地方。你不必费心了。”
是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再要多说,就是自讨没趣了,小张只好听其自便。但回到自己房间,睡在床上,想想不免困惑,孙祥太的行动,似太突兀。这么早不是看朋友的时候,他这个朋友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又何必如此讳莫如深!凡此都不能不启人猜疑。
“嗐!”小张失笑了,事不关己,何苦放着好好的觉不睡,去花这种不相干的心思?这样一想,立刻便能丢开一切,翻个身恬然入梦。
睡了不知多少时候,朦朦胧胧听得有人在喊,睁眼一看,是刘不才掀着帐门站在床前。
“小张,快起来!”
声音中带关惊惶,再定神看他的脸色,亦复如是。小张的心一懔,睡意全消,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下地来,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
“快去通知李小毛,叫他赶快走!”刘不才说道,“孙老大已经打听到了他的地方,约好了人,要‘做掉’他。”
“这——”小张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为啥?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不要不相信。事情一点不假!”小张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好!我去通知他。不过怎么说法,你要告诉我。”
刘不才也不知该怎么说法,只能将消息来源告诉他:“是朱姑奶奶来跟我说的。朱姑奶奶是哪里来的消息?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想来你也晓得,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小张一面扣衣服钮子,一面答道:“这不用说,是松江老大告诉朱姑奶奶的。大概老孙约的人。跟松江老大也熟,消息的来源如此。不过我不明白,事情过去了这么久,香堂也开过了,为啥老孙气还不消,非要他的性命不可!”
“那就不晓得了,现在也没有功夫细谈。事机急迫,你赶紧去吧!”
“当然。”小张索性坐了下来,紧皱眉头,是用心思索的样子:“刘三哥,你跟我一起走。话有个说法,我们在路上商量。”
“一时也没有啥好商量的!如今第一步先通知李小毛避一避。我看就在朱素兰那里落脚好了。第二步该怎么走法?到了那里再商量。”
“言之有理!就这么办。”
于是小张匆匆漱洗,与刘不才出了客栈,两乘轿子飞快地直奔大丰。下轿一看,便觉从伙计到小徒弟,神色都有异状,两人对看了一眼,各起警惕,说话要谨慎。
“敝姓刘。”刘不才先开口,“是朱道台派我来的,有笔生意是跟宝号姓李的朋友接的头。请问,他在哪里。”
“啊,啊!”帐台上走下来一个人,长袍马褂,像是大丰米行中有身份的管事,“刘老爷请里面坐。”
引入后进客堂,小徒弟递过茶烟,那人告个罪转到后面。
过了好半天,只见出来一个三十左右的妇人,面如银盆,眉发如漆,别有一种令人目眩的颜色,不用说,这就是粉面虎了。
“哪位是刘老爷?”她问。
“我就是。”刘不才点点头。
“这是我们老板娘。”管事的说,“朱道台作成大丰的生意,是我们老板娘亲自谈的。”
“是的。”粉面虎接口:“刘老爷有话,尽管跟我说。”
“好,好!我先引见这位,”刘不才手一指,“这位好朋友姓张,他也是那位李老弟的要好弟兄。这笔米生意,他是原经手。”
“原来是小张少爷!”粉面虎微蹙的双眉,顿时舒展,“既然是小毛的要好弟兄,那么,我说实话,而且还要请小张少爷费心打听。小毛出事了!”
刘、张二人的心,不由得都悬了起来。刘不才比较沉着,一面以手向小张示意,稍安毋躁,一面问道:“出了什么事?”
“十点多钟,小毛吃茶回来!走到弄堂口,遇见四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拿他轧住,推在一辆马车里,往西面去了。至今没有消息。不知道到底为了啥?”
“有这样的事!”小张看一看刘不才说:“等我们去打听打听!”
“慢来!”刘不才说,“这好像是绑票!老板娘,你有没有报巡捕房?”
“没有。”
“为啥?”
“因为小毛没有喊。只说:‘有话好讲,有话好讲!’倒像彼此熟识似地,所以我暂且不报捕房。”
刘不才和小张都暗中心许,粉面虎毕竟还有些见识,处置得宜。就眼前来说,李小毛固然存亡未卜,而一报了巡捕房;李小毛就算死定了。说不定连尸首也无觅处——不是如此毁尸灭迹,孙祥太就要吃捕房官司了。
不过,这些想法,不便明告粉面虎,刘不才只问小张:“你们是老朋友,晓不晓得李老弟跟啥人结了怨容?总要寻出一个头绪来,才好下手。不然,上海这么大,人这么多,哪里去瞎摸?”
小张会意,他是有心如此措词,以防精明的粉面虎起疑。
因而也装模作样地皱眉苦思,想了一会才说:“我只晓得小毛从前‘在帮’,现在好像不是了。他们帮里的人,我倒认识几个,只有先找他们去摸一摸底。”
“是的!”粉面虎连连点头,“能托帮里的人帮忙打听,一定会有结果。我们就是一时找不到这样的人,小张少爷有熟人,那就再好都没有。请多费心!”
这是个很大的麻烦。李小毛吉凶莫卜,倘或已经死在孙祥太手里,就可能连那一万石米都落空。如果留得命在,又不知怎么才能将他救出来?刘、张二人一出大丰,先就在路边商议,决定分头行事。刘不才去通知朱姑奶奶,打听消息,小张回客栈看孙祥太,见机行事。倘或孙祥太不在,便到孙家会齐,商量下一个步骤。
说定了各奔东西。小张四到客栈,直奔孙祥太所住的房间,远远就听得鼾声如雷,问起茶房,方知是中午回来的。一回来就睡,鼾声至今不曾息过。
这倒有些莫测高深了——小张心里在想,刚刚杀过了人,心情难免小宁,不能这样恬然入梦。不过久走江湖的人,不同寻常,或者因为宿恨已消、心无牵挂,正好酣睡,亦未可知。
想来想去,无从判断究竟。也不能将孙祥太唤醒了,问个明白。既然如此,逗留无益,小张毫不迟疑地赶到孙家,进门一看,孙子卿夫妇、刘不才、朱大器都在,就是不见松江老大。
“松江老大呢?”他问。
“打听消息去了。”刘不才问,“孙老大怎么样?”
“在呼呼大睡。”小张细说所见、所闻、所想,神情显得相当焦灼。
“看起来不像刚杀过人。”朱姑奶奶安慰他说,“你急也无用,快有确实消息来了!”
果然,话刚完,松江老大就已到达,带来了令人安慰的消息,李小毛只是被孙祥太软禁着,预备秘密带回嘉兴。
“这是为啥?”小张问说。
“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说吧!”松江老大慢吞吞地答道,“孙老大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杭嘉湖一带水路码头,眼看都要光复了,他要重整他这一帮,还有番事业要做。整帮先要整帮规,有李小毛这件事在,他做当家的,话就说不响了。所以,拿他带回嘉兴,想‘借人头’,立个榜样。”
“老大,”不等他话完,小张便抢着说。“你总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吧!”
一向聪明机警,说话行事都很漂亮的小张,这句话却说得不甚高明,不但松江老大无以为答,连旁人都觉得要劝解都无从插手。
始终默默无言的朱大器,到这时候开口了,“小张,你不要着急,只要人活着,包在我身上,保住李小毛一条性命。”
他说,“这件事,松江老大很为难。说实话,就现在这个样子,能把底细摸出来,你如果是李小毛的朋友,亦就应该很见松江老大的情了。”
光棍一点就透。小张也发觉到自己刚才那句话说得“不上路”,随即笑嘻嘻地兜头一揖:“松江老大,太熟了!我说话欠检点,你千万不要摆在心中!”
“言重,言重。不必再提这个了。”松江老大摇着手说;“倒是小叔叔,你有啥锦囊妙计,趁早吩咐下来,我们心里好有个数。”
“等下我一个人唱独脚戏,你们就当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倘或孙老大问到,你们尽管‘装胡羊’。不要紧,越装得没事越好。”
各人都将他的话体味了一下,虽有莫测高深之感,但莫不是这样在想:不管它!听他的话没有错!
***
上灯时分,孙祥太到了,容光焕发,笑容满面,看上去是心情很舒畅的样子。
客厅中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