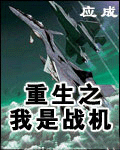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农民--宝珠轶趣录-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被刘德胜训斥一顿,说他想找死,一点亲情都不顾。还说你懂不懂?不懂别乱摸。摸坏你赔得起?
宝珠感到委屈,心里有点恨他。那时候宝珠就想,将来一定做工人阶级。没有想到只过了十几年,当年傲气的工人阶级,竟然也走到这种无可奈何的地步。于是宝珠安慰说:“叔,你活不下去就回咱乡下,弄二亩地种怎么不能过?咱又不是没种过地!”刘德胜说,前几年想过,城里真呆不下去时,就到乡下包几亩荒地种。可也不想回咱们村了,免得人笑话。
宝珠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笑话谁呀?回吧。还回咱村,我,我帮……”
话一出口,宝珠觉得话说得有些冒失了。姚村的人现在也不是好多家没地种了吗?真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宝珠惭愧得连一句有底气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宝珠是个愿帮助人的人哪,但现在让他说什么好呢?
德胜问宝珠,现在正是农忙时节,侄儿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宝珠叹口气,正要把村里发生的事讲给叔叔听,曹子健突然出现在门口。宝珠不知该如何是好,急忙就看门外边,没有见到那个叫木瓜的人。
曹子健见屋子里坐着的三个人,衣服都是湿的,也没有问什么原因,就对宝珠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走吧。”
刘德胜夫妇不知这里发生过什么事,对曹子健说:“我们老俩口想不开,跳到湖里想一死了之,谁知天不让我们死,是他才把我们救上来的,正准备回去哩。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侄儿,十几年没见,不想在这儿遇到了!你说奇不奇?这不是天老爷不让我们死吗?”
“既是这样,”曹子健对宝珠说“你就在他们家躲几天。”然后压低嗓门警示宝珠,“记住,什么话也不准对人讲了。”
刘德胜听曹子键这样说,觉得很蹊跷,他不知在宝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多问。三人搀扶着回到家里,换了衣服。刘德胜指着换上的衣服对宝珠说:“这是今天准备好的,让收尸用。现在穿上吧。”
宝珠发现刘德胜家很简陋,两张陈旧的单人床,合在一起并成个大铺。墙皮脱落,门窗朽腐,屋子里好象几十年都没有添过一件象样的东西,透着一种酸臭和陈腐的气味。屋子中央挂着一张毛主席像,端庄严肃,主席似乎看着屋子里的穷困在想着什么。两床露着棉絮的被子,叠放在一个木头箱子上。一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已用了十几年,那还是刘德胜他那年当了省里的劳动模范,政府奖给他的。为看病,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已经变卖光了。不断地有邻居好友接济他,但终究是杯水车薪。厂里不景气,大家都有难处。
两位老人感激宝珠的救命之恩,羞愧的却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跳湖自杀的行为,要宝珠千万千万不要告知乡人。宝珠说:“那当然。”婶娘问宝珠想吃些什么?宝珠说:“就是想吃干饭。米饭面条都行,需三大碗。”
吃完饭,刘德胜旁敲侧击地提到湖边小屋曹子健说的话,宝珠就把村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告知刘德胜。说,511那天,全村人和警察干了一架,警察现在到处抓人,他就跑到城里来了。相随的几个光棍们也都跑散了。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刘德胜说:“既是这样,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儿躲几天。没有警察会找到我这儿来的。”
说到土地,刘德胜也告诉宝珠,说这风雷机械厂已不死不活的呆了七年,工资停发,人心涣散,工厂已不成个工厂的样子。倒卖的倒卖,受穷的受穷,发财的发财。当今的领导既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也没有和群众商量商量,就把150亩土地全卖给开发商了。价钱低的不能再低了。工人们都心疼哪!可谁能挡得住人家那样干?冠冕堂皇的话是卖了地补发工资,可谁都清楚那其中的猫腻,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厂蒸发了,一卖了之。这样,工厂没有了,人没有了,什么丑事都掩盖了。他们就不怕什么了。
宝珠说:“咱叔侄俩遇的这都是逼上梁山的事。狗儿们欺咱百姓软弱,独食惯了,什么事也干得出来。不闹闹,他们还不知道咱老百姓的厉害哩。咱姚村就有人跑到当年的水泊梁山上去看了看,说那儿已成了旅游区了,不接待好汉了。要有梁山,我也要和林冲一样,挑上个酒壶上梁山!”
刘德胜悄悄告诉宝珠说:“厂里有人带头哩。一个血气方刚的退伍军人!全厂一千多人签名,要求省局说清楚,为什么把土地卖了,谁签的协议?卖了多少钱?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不让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还请了律师呢。”
“律师?律师是干什么的?”
“打官司呀!打官司这些事,律师都清楚条文是怎么规定的。是咱们不懂。他们就变着法欺咱的不懂,胡来了。”
“噢!”宝珠若有所悟地拍拍脑袋,“其实,姚村的事和你们厂的事是一个理。他们卖地也该通通村民委员会呀。卖不卖?卖多少钱?卖了钱怎么分?缺了地的农民该怎么活?中央的条文是怎么规定的?县委怎么说的?这都是问题。杜马就是村民委员嘛。唉唉,杜马呀杜马,你真傻呀,你只知道村民委员会春天,秋天,开会吃蘑菇炖小鸡,就不知道还有法律条文?傻,真傻!”
宝珠倒是听杜马说过,当了村民委员后,村长请他们吃过两次蘑菇炖小鸡,味道好极了。还保密得不让村民知道。看来我们也得请律师呀。这瞎躲得是什么!不行,我明天就得回去!”
刘德胜说:“不可!既然他们到处抓你,就有抓你的理由。你在我这儿避避风头,事不过三。等两天事情也许就淡下来了,那时再作商量也不晚。如今你还不可贸然行事。”
宝珠想想觉得这样也好。宝珠感到城里人就是城里人,比乡下人就是多一根肠子。再说了,如今他是单身一个,也没有人能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宝珠觉得,既然都是卖土地的事,也必然要涉及同一个问题。宝珠想听听他们怎么说,看看他们怎么干,学点什么也有好处。只是宝珠看着这老俩口整日唉声叹气,以泪洗面,让他感到不快活!
有一天,宝珠说:“你老俩不能这样活!”
“怎么活?”
“出去散散心呀。”
“唉!散什么心呀,她腿脚都不利索了,还散心!我现在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羞与见人,更不敢抬头看别人手里提买的东西。”
宝珠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社会是让人觉得不公平,你就别光看别人吃肉呀。看着别人吃肉,你就这样想,这个有肉吃的人,他老婆肯定跟别人好上了,要不他怎么能有肉吃呢?可他吃着肉,想着老婆和别人好,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滋味?肯定不好受哩!古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有你的难,我有我的难;都有难,就是难得不一样。人活着,得让自己心里常有些亮光,有些念想。”宝珠突然觉得他肚子里的理论,挤得满满的。他竭力想说服刘德胜,可就是理不顺,自然也就顺不出什么话来。想了半天才问:“叔,除了想病,想穷,你就没有想过其它什么事吗?”
“还能想什么事?”
“比如,你的心啊,飞呀飞啊,好像很大……”
“没有。现在就是好心酸;一酸就掉泪。”
“我是说……”宝珠想着自己的心,“你没有去想干一件什么事,这件事一想起来你就心跳……”
“抢银行呀?”
“咳!抢什么银行,那不是犯罪吗?犯罪的事能干吗?再心跳也不行嘛。我说的是,就是,咳!我怎么能给你说明白呢,就是一想起这件事就起心劲,心就悄悄地跳!舍命也愿意去干!”
刘德胜想了想,说“没有,一件也没有。”
宝珠为难了。宝珠是不能把自己肚里的感觉变成话语说出来。宝珠知道自己念书少,提升不出理论来,就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了琢磨自己的心事。又觉得肚子里的东西,一时挤得满满的,乱得没有头绪;一时又像被狗吞了一样空荡荡的没了着落。他懊丧地摇着头,找不出肚里的那个能说服人的线头在哪里。
宝珠望着窗外,忽然觉得,纵是一天三顿饭,有二顿吃不饱,宝珠也不失掉对明天的期望!人嘛,就得整日琢磨点好事,那怕这事永远做不到也比没有好。至于这心思是怎么来的,各人有各人的情况。人若没有这点事支撑着,非压垮不可。但心里的事,都是模模糊糊的事,不要说宝珠说不清,就是叫个大教授来,他也是慢慢地琢磨,慢慢地像抽丝一样去感觉、去体会。感觉得真切了,才会恍然大悟!宝珠现在就需要慢慢地感觉。有时他好像感觉到了,一挪身子,又忽然像短线的风筝似的飘走了!笨,真笨!就那么一丝丝东西,像针一样轻轻划过心头,爽爽的、痒痒的,就在心尖上,怎么就捋不住呢?唉,真笨!宝珠对自己也失望了。
宝珠和刘德胜同在一张大床上睡下不久,宝珠就做了一个金黄色的梦。那梦是那么灿烂光辉,那么地耀眼明亮!他回头一看,是一轮明月正从山口吐出,慢慢地那月明竟变成一张圆圆的笑脸,明眸皓齿,像小丽,不,像潘英。对,像潘英!宝珠的心一软,一股细细的东西象针尖一样,轻轻地划过他的心头,爽爽的,痒痒的,好受极了。他就喊“潘英!潘英!”连喊好几声,才被刘德胜推醒。
刘德胜就问宝珠:“做梦了是吧?潘英是谁呀?”宝珠的脸羞羞的,他觉得胯下有些湿粘粘的东西,吱唔着不知说什么好。
刘德胜问:“潘英是个什么人啊!叫得那么柔……柔情,那么忧伤呢?”
宝珠说:“是,是咱们村妇女主任。”
刘德胜说:“爱上了?悄悄爱上了是不是?叔可是盼着你早日成个家哪。”
宝珠说:“不行。她是现役军人的老婆!勾引现役军人的老婆,那是犯法的事嘛。”接着他把村长在大田里如何和潘英亲嘴、干事,他如何报打不平等等,细细讲给刘德胜听。
刘德胜说:“若是在过去,你就是条梁山好汉,除暴安良。可是你知道那个潘英就不愿意吗?村长这个官,虽然无品无位,却是朝庭命官,说白了那就是土皇帝,地头蛇!也就是你呀侄儿,放给旁人,恐怕不会这样做!”
宝珠想不出什么话应答刘德胜,只说我不怕他。
刘德胜说:“你不怕,那你是无家一身轻。有了家,你才知道什么怕,什么不怕哩。”
宝珠说:“我有家。我怎么能没有家呢?我的家在我心中,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还有我很多想念的人和事。那里的人和事都是和眼前的人和事不太一样的。他们常让我高兴,让我心里爽爽的——当然这人里就有潘英。人虽还是这些人,在我心里,却又比这些个人更好,更美。美得我心里悠悠的,让我爱天爱地爱人。”
刘德胜不知宝珠神神叨叨说的是什么?好像在和鬼神对话似的。他坐起来摸了摸他的头,并不发热。刘德胜忽然觉得,宝珠心中好像还有一块绿地,绿地上种满了自己喜欢的花草,宝珠常在那里抚摸观赏。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精神家园吗?如果是这样,那宝珠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其他的不说,单是这苦中作乐,就需有一种大度。也许,他就是通过心灵里的景物,照亮了眼前的现实,才有这生活的温馨和超然,才有这大地上的喜剧吗?
于是,刘德胜问宝珠:“你是不是常把事情都想得很好?”
刘德胜想,如果宝珠说“是。”那他就是得了一种精神幻想症!然而,宝珠说:“不是!”这就让刘德胜不知所措了。
然而,经刘德胜这么一说,宝珠心头一亮,在肚里盘绕的东西一下让他理出了头绪——宝珠爬到刘德胜肩上,对着他的耳朵说:“叔,你给侄儿说句实在话,你这辈子有没有一个梦中情人!悄悄地爱过谁?”
刘德胜说:“没有。只有你婶。我只在乎她!”
宝珠无奈地摇摇头。宝珠有些看不起他这个婶,胖得提都提不动,胖得五官都有些变位,一句话,丑!宝珠想,如果心中一辈子只有这样一个人,那这世界就太没有色彩了!怪不得要跳湖去寻死,这就是没有一个梦中情人之过。作为男人,宝珠觉得这是大忌!于是,宝珠说:“这就不好!”
刘德胜说:“我哪里还有那心劲!又不像你年轻。”
宝珠说:“这和年轻不年轻没有多大关系。”但宝珠觉得,人必须活得有心劲才行。人应该给生命里安排很多值得记忆和留恋的东西。有美好,生活才有魅力,生命才有光亮。于是,宝珠问:“那么你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吗?”
“没有。真没有!”
宝珠笑说:“你是不和侄儿掏心窝呀!”
刘德胜说:“掏出来了。就是没有!”
宝珠说:“你再好好想想,二十岁时?”
“没有。”
“那么十三四岁时呢?应该有吧?”
刘德胜摇了摇头:“也没有。”
宝珠靠近他些:“小时候,穿开裆裤那会儿?你好好想想,细细想,一段一段地想,肯定有你忘不掉的人,想起来你就会自笑起来的。”
刘德胜仍就摇头,宝珠无奈地叹了口气:“叔,我只说你一辈子当工人阶级,当老大哥,住在城里,又支援农业,追你的姑娘哪能少了呢——唉,真扫兴!”
刘德胜说:“你是想出你叔的洋相吧?”
宝珠说:“我是怕你想不开再跳湖去,给你找个支撑点。人总得常想些好事。你闹到今天这个样子,全怪你没有按我说的那样子做。信不信在你。睡吧,时候不早了。”
宝珠要躺下去睡觉时,突然发现刘德胜的眉头,绽放出一股喜气,这股喜气立刻弥漫开来,使得他那张枯黄的脸,充满了一种少见的红润。
“有戏!”宝珠想。
刘德胜来了精神:“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么一桩事,倒被我忘得干干干净净了。”
“说说看。”宝珠低声鼓励刘德胜,他怕隔壁的婶娘听到。
“那一年,我记不清了,是到咱们村支援农业,村西头冯群马有一个姑娘,小我三岁,就像有首歌里唱得那样,‘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那两只眼睛呀水灵灵的,会娇嗔,会妒嫉,还会说话。一颦一笑,一挤一眨,就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那双眼睛哪,和我说过好多好多情深意长的话。她的每一个眼神我都懂,而且懂得很深。可那时候,我正当着劳动模范,不敢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