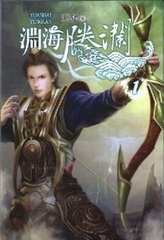渊海腾澜-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钢弩“崩”的一声轻响,弩箭没入漆黑的夜色。只见那哨塔上来回转身巡视的士兵突然身子一震,手中的兵器摔落,双手捧着脖颈软倒在哨塔上。
旁观的众人紧提着的心松了下来,缓缓舒了一口气,庞克叹道:“凤翼这一手真不是盖的,我瞪大眼睛使劲看也只看到个模糊的黑影,不说射得准不准,他怎么能看得这么清楚呢?”
张凤翼打趣地笑道:“千万别夸,一夸下一个就不灵了。”
庞克赶紧捂住嘴巴。
张凤翼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双手稳稳地又一次端起了弩机。弩弦连响,另三座哨楼上的哨兵也被无声无息的放倒了。均是颈部中箭,来不及发出一丝声音。
此时把守营门的四个卫兵竟还没有发觉,张凤翼把钢弩递给了勃雷,自己拿起了长弓,道:“这四个一下子收拾不完,咱们一起来吧,我射左边两个,你射右边两个。”
勃雷也看得手痒,闻言欣然接过钢弩。两个人把弓弩端平拉圆了正要射出,敌营内帐篷间一队火光缓缓地向营门口接近。
庞克皱眉低声骂道:“好像是巡营的督察卫队,妈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在这节骨眼上,若过来看见哨楼上没了士兵可就糟了。”
“不是赶得巧,而是巡得勤。”张凤翼缓缓松开本已拉圆的长弓,双眼凝视着那队火光沉声道:“这里距离前线还远得很,又遇如此恶劣天气,敌军的警戒竟还是如此森严。”
勃雷咬牙道:“现在这队敌兵离营门还远,我们干倒这四个把门的哨兵,大队压上,给他来个乱箭齐发。”
庞克道:“那不就混战起来了,主力还没到位,现在开打会使敌人有时间组织反击的。”
张凤翼略一思忖,拍膝道:“我们要为主力争取时间,既不能让这股敌人走脱,又不能陷入混战。收拾了营门的卫兵后,勃雷指挥部队,我装扮成哨兵立于营门见机行事,你们看我的手势,我一挥手,勃雷即指挥大伙儿用弓弩压制前冲。争取速战速决,后面有我垫底,谁也别想逃入营门。”
勃雷急道:“那怎么行,你是长官,该由你来指挥部队,这事我来就行,上阵厮杀我最拿手。”
“大哥不要争了,若认小弟我是长官,就莫再多说,服从命令吧!”张凤翼话音虽轻柔,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蕴于其中。
“不行,别的都好商量,只有这种事不能答应。凤翼,你别在老哥面前摆架子,老哥我万夫长都当过,不是你两句话唬得住的。”勃雷也不理张凤翼,开始整理装备。
宫策从容插话道:“眼下形势危急,冒点险也是值得的,不如你俩一起去,也更保险些,你俩身手高超,只要别被自己人的弓箭所伤,抵挡一时半刻该不在话下,有这时间大家早冲到营门了。”说到这里,若有若无的瞥了一眼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庞克,“至于武艺不十分过硬的兄弟,就不必再凑热闹了。”
这句“武艺不十分过硬”的评语使庞克的脸涨成猪肝色,呐呐地再说不出要去的话来。
勃雷立即赞道:“好,这个办法好,两全其美。到底是参军,凤翼,宫策先生都这样说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张凤翼摇头无奈地笑道:“你们都定好了,我还能说什么。只是千万别受伤,我可不想未曾开战,先折‘臂膀’。”
四名中箭倒毙的腾赫烈士兵被拖入营外的草丛,张凤翼与勃雷分站在营门的两边,急切间也来不及更换服装,两个人只摘下镶有翎毛与兽皮的腾赫烈头盔戴在头上,至于身上的甲胄,暗夜中一时倒也不易分清制式。这一切都是在那队灯火转过一座帐篷的瞬间完成的。
远处的那队巡哨队伍正缓缓接近,已经清晰地听到军靴橐橐,间中有甲胄与兵刃相击发出的铿锵声。
勃雷绷着脸,紧握着手中的长柄狼牙棒,对面的张凤翼冲他展颜一笑,道:“一会儿你别开口,全由我来回答。我一挥手,咱们立即躲在栅栏门后面,别让后面兄弟不敢放开手脚射箭。”
勃雷压低声音道:“知道了,这些还用你交代?拜托站笔挺一点,你这副随便的样子根本不像士兵,很容易让人起疑的。”
“噢?有吗?士兵们夜间站岗都如此的,有长官的时候严肃一些,没人的时候放松一下。看来老兄当官的时间比当兵的时候长呢!”张凤翼撇嘴轻笑道。
“立──正──”随着领队队长拖着长音的高喊,百馀人的巡哨官卫队停了下来,两个“哨兵”也知趣地像标枪一样站了个笔直。由于凛冽的疾风,几十个火把都被风吹得明灭不定,光线并不是很好。为首的将军身材颀长瘦削,十分精悍,给人一种钢筋铁骨的感觉。他身披一领熊皮大氅,手按腰刀,走动间甲胄哗啦作响。
他缓步踱到张凤翼与勃雷身前,皱着眉头逼视着他们道:“怎么只剩你们两个人在站岗,其它人呢?如此大胆,竟敢私自擅离职守!”
远处灌木丛中的士兵们已经拉圆了长弓,庞克焦急地道:“怎么还不打手势,和这些腾赫烈军夹缠什么?”
宫策道:“现在敌人还在营门内,动起手来,会散开藏在栅栏后面,达不到一举歼灭的效果。”
庞克一听更急了,道:“那怎么办?这些腾赫烈军也不会听凤翼的。”
宫策拈髯笃定地道:“别着急,沉住气,等着凤翼的手势。即使腾赫烈军识破了他们,以他们的武功,一时也不会有什么闪失。再说我们近在咫尺,随时都可救援的。”
庞克想想也是,长出一口气,不再吭声了。
看着这位总巡官一脸威严的表情,两个哨兵虽然块头高大,却好像都很怕见大人物,大黑个子的一脸木然,彷佛没有听到;个子稍矮些的瑟瑟缩缩敬畏地道:“报告长官,林子那边放哨的兄弟发来信号,要我们分个人过去看看,好像是那边有动静,于是过去两个弟兄瞧瞧。”
“什么,既然有警示,为什么不报告?”总巡官严厉地质问。
被质问的小兵更加害怕了,说话都有点结巴起来,“属……属下们想可能是急于取水的牧民,不敢因为这点小事儿惊动大人。”
“什么叫‘惊动’,发现任何情况都应立即报告。他俩去了多长时间了?”
“有……有一会儿了,属下们也正心里纳闷呢!”小兵结结巴巴地答道。
“嗯──”那位总巡官略一思索,向身旁侍立的卫队长道:“我们过去看看。”说着不再理两个吓傻了的哨兵,当先向营外踱去。
卫队长行礼道:“是!大人。”向队伍一挥手,“全队跟上。”
一伙人拥着那位将军向营外走去。
明灭闪烁的火光下,那表情木然的大块头哨兵眼中掠过一丝狂喜,向对面的伙计们做了一个手势。
对面哨兵撇嘴一笑,用眼神示意他沉住气。
看着那队卫兵缓缓走出营门,树丛中的庞克呼吸都重浊了,激动地向左右道:“兄弟们,都把长弓拉满了,这伙不知死活的家伙竟然送上来当活靶子了。”
※※※※
卫队簇拥着范已经出离了营门约有百步,前面二百步远、齐胸高的灌木林随着疾风起伏如浪涛。枝叶摇摆瑟瑟作响,彷佛千百条手臂在召唤着他们,四野一片漆黑,卫队的火炬被风吹的明灭不定,这几团微弱的光亮在暗夜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孤弱。范手按佩刀,气定神闲地走在队伍最前面,边走边思忖着,下意识里他总感到这个营门的哨兵与别的营门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时却又说不上来。
他陡地停下了脚步,一拍额际,“是了,这个营门好像比别的营门暗了许多,对!是哨楼上的气死风灯!哨楼上的气死风灯没有点亮!”
范回头向大营望去,夜色中四座哨楼上果然空空如也,不但灯笼是黑的,也没有侍立一个哨兵。刚才那两个哨兵门神般把守在营门口,那黑大个子手持长柄狼牙棒,眯着眼睛不屑地盯着他们,方才说话的那位则两手抱肩、懒散地靠在营门柱上。看到他的回望,靠在门柱上的那位友善地向他挥了挥手,彷佛在为朋友送行。挥罢之后两人一齐闪入营门,在栅栏柱后藏起了身形。
“不好,有埋伏。”一个念头闪入脑际,他佩刀才拔出一半,空中便响起弓弩破风的轻啸,满天箭镞已如急雨般袭来,走在前面的士兵惨叫着倒下了十几个,队伍顿时乱了起来,身后的卫队长高喊着,“范将军,快退。”挺身挥刀挡在他身前,箭镞与刀刃相击的拨打声“叮当”不绝于耳。
未几,他突然身子一震,一枝雕翎箭插在了腿上,他的动作立时缓了下来,接着听到“噗噗”的箭镞入体之声,这个忠勇的战士挣动几步,仆倒在地。远处一层层端着弓弩、身着黑色皮甲的汉拓威轻甲步兵从灌木丛中涌现出来。左右的卫兵已经倒下大片,能站着的所剩无几。长枪手战死殆尽,只有几个刀牌手举着盾牌缓缓后退。
“这是敌军大部队夜袭,早一分报警部队就少一分伤亡,就是死也要死在大营之中,把警报传出!”范内心焦灼地想着,纵身向后平掠,三尺长的阔刃长刀挥的泼水不进,箭矢四下崩落。可范与众不同的衣甲早已使汉拓威士兵们认定他是一个大人物,士兵们缓缓前进,边走边射,弓矢密如蠓蝗,集中向他射来。范突然抖开熊皮大髦,内力灌注,逆风舞动,如挥铁板,羽箭纷纷拍落。
看着范从容地缓缓后退,勃雷向对面的张凤翼道:“看来这是个硬茬儿,儿郎们那几根弩箭奈何不了他,得咱们亲自出手才成。”
张凤翼看着范的身影抿嘴冷笑道:“此人横练的外功极强,他一接近营门,你我从左右合击,千万不要给他喘息之机。”
营门前的开阔地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汉拓威士兵,在三层弓弩手后面出现了掷矛手、刀牌手、长枪手,上千人的部队在暗夜中静悄悄地前进,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只闻“嗤嗤”的箭镞破空之声。范已经接近营门,前面的部队并无追赶之意,只是保持着节奏缓缓逼近,彷佛并不担心他能逃出格杀。范急切间向营门一瞥,五六个先他退向营门的刀牌手横尸在营门口,有三四人脑浆迸现,满地红白,惨不忍睹。
他想起了那个黑大个哨兵手中的长柄狼牙棒,一股杀意涌入心头,一手展翼般甩开插满箭镞已形如蓑衣的大髦,一手挺刀在手,箭步转身向营门跃进,口中喝道:“挡我者死!”
“奶奶的,敢在老子面前硬闯!”看到范来势凶恶,也激起了勃雷的狠劲,正要挥棒来个拦腰横扫。
张凤翼看出势头,急喝道:“勃雷,不要硬拚,声音太大,会惊动里面,让我来。”说着黑燕般纵身掠起,两个身形在空中相接。
范振刀疾劈,寒光一闪,并无兵器相格之声,只听到“嚓”的一声轻响,范的长刀被张凤翼用一柄普通的军刀顺势封带于外门,接着张凤翼揉身而进,两人几乎贴身,张凤翼另一只手奇迹般地递出一柄尺长的匕首,手腕一翻,刃口向上,由对手下腹向上反撩,刀锋未到,森寒的刀气即透体而入。范被惊得亡魂皆冒,变身疾退,直退出几丈方稳住身形,落地后头盔跌落,铠甲从胸前被分为两半,内衣尽裂。
张凤翼从容落下,提刀再次进逼,勃雷也拎狼牙棒跟上,两人呈犄角之势左右挟持。后面的汉拓威士兵也都停下了弓弩,在渐渐向他们接近。
范一把扯去衣甲,披散着头发,赤着古铜色精壮的上身,他心中明白自己遇到了怎样的对手,眉宇间满是视死如归的豪壮之气,挺刀厉喝道:“凭你们两个畏首缩尾的獐鼠也敢妄想拦下草原的雄鹰。”
张凤翼也不动怒,只是撇嘴嘿笑,颊上的刀痕微微扭曲着,口中淡淡地道:“多言无益,是鹰是鼠手底下见高低吧!”说罢挺刀前刺。
勃雷举棒下砸,范也嘶吼一声挥刀外格,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三个人又战在一起,张凤翼刀势绵密细腻,多用刺击,较少劈击,与范两刀相交时从不硬击硬格,总是用削、洗顺势引带,加之张凤翼身法灵动,进退倏忽捷如鬼魅,往往使出意料不到的险招,与勃雷步步为营、狂扫硬砸的刚猛打法刚柔相济、相得益彰。才十几个回合,范为了抵挡勃雷沉重的狼牙棒,被张凤翼屡次近身突刺成功,全仗着强硬的横练外功才没有受到致命重创,不过身上留下五六处创口,周身一片血红。此时的范形同疯虎,狂舞着长刀直取张凤翼,张凤翼冷笑着不退反进,战刀连环递出,刀刀直取范的咽喉,范却不理不睬,只管劈击,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张凤翼又刀势一改,变轻灵为沉滞,运刀如推盘,刀锋产生一股粘附之力,用削、抹之诀,将两刃粘附在一起,范抽刀不及,耳听背后破风之声陡起,却宁死不愿弃刀躲避,被勃雷碎石如粉的狼牙棒一棒砸在后背,喉头一甜,一股鲜血喷溅出来,一股横练之气立时散了。张凤翼轻盈后掠,避开飞溅的血沫。
范摇摆着身躯,蹒跚前冲几步,以刀拄地才稳住身子,他满身浴血,头发四散,面目狰狞地嘶声喝道:“大丈夫死于疆场,何憾之有,恨只恨中了你们两个汉狗的诡计,没能及时向营中报警,误了军中大事,我即使不能今夜生还,也要带你们一同去享死神的血宴。”说完挥刀又上,直取张凤翼。
张凤翼收刀入鞘,转身别过脸去不再看他,口中淡定地道:“这就是战争,只有胜负没有英雄,是汉子的还是就此认命吧!”
长刀已劈至张凤翼头顶,范再次听到耳后响起灌风之声,张凤翼静如渊岳,对范的攻击毫不理睬。和着狼牙棒入体时“噗”的闷响,范脊柱、胸骨尽皆碎裂,连一丝呻吟都没来得及发出,颓然倒地。
勃雷拎着血淋淋的狼牙棒兴奋地道:“好强横的横练功夫,生捱了我两棒才倒下,哈哈,太过瘾了,只不知这样的硬茬儿在这股敌军中还有几个?”言下颇有意犹未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