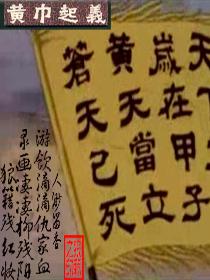西方的没落-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橄蟮氖旱奶匦缘奈侍狻J骸衝个独立有序的要素——是点的意象(image),因而亦可称之为是一个点。同样地,由此而逻辑地获得的方程式,亦可称之为是一个平面,是一个平面的意象。至于n维度中所有点的集合,则可称之为是一个n维空间。在这些远离任何感觉主义的超越性的空间世界里,就存在着所谓的关系,这便是我们的分析所要探讨的对象,而我们也发现,这些关系与实验物理学的数据常常是一致的。这种高级的空间,正是西方心灵的整个特性的一个象征。唯有这种心灵,才会尝试用这些形式去捕获“既成物”和广延物,才会尝试通过这种挪用或禁忌去祈唤和结合——或者说去“认识”——那陌生的东西,并会取得成功。这些数字思想的领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探得真谛。在尚未达到此等领域之前,诸如超复数(hypercomplex numbers)系统(亦即矢量微积分的四元法)这样的想象物,以及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符号表达,例如n;都不会获得什么实际的特征。在此,只有理解了此等数字思想的领域,那种现实性才不仅仅是感觉的现实性。精神为实现自己的观念,决不会把自己局限于感觉形式。
十八
从对象征性的空间世界的这种伟大的直观出发,便产生了西方数学最终的结论性的创造——在群论中把函数论加以扩展和精练。“群”,即是同源的数学意象的集合,例如,某一类型的所有微分方程之总体,便是一“群”。“群”在结构和秩序上类似于戴德金的“数体”(number…bodies)。在此,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全新的数的世界,对于行家的内在视觉而言,这世界并非全然地在感觉上是超越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在这些庞大的抽象形式系统中,找出一些元素,相对于一种特殊的运算(如系统的转换)时,它们却能不受影响,就是说,可以保持不变。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正如克莱因(Klein)所一般地阐述的:给定一n维的簇面(“空间”)及一组转换,需要考察的,乃是属于该簇面的诸形式不会因为“群”的转换而改变其既有的诸特性。
到了这一顶峰之后,我们的西方数学,作为浮士德心灵的观念的投影和最纯粹的表现,已耗尽了其每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完成了它的命运,就这样,它终止了自身的发展,一如古典文化的数学在公元前3世纪终结了一样。这两种科学(甚至在今天,能历史地考察其有机结构的,也只有这两种数学了),皆产生于一种全新的数的观念,在古典的情形中,是毕达哥拉斯的数的观念,在西方的情形中,是笛卡儿的数的观念。两者皆在百余年之后展尽了其所有的风采,达致其成熟的境界;两者皆在繁荣了三个世纪之后,皆于各自的文化步入大都市文明的时刻,完成了其观念的结构。这种相互依赖的深刻意义,马上就会给以说明。而此刻,对我们而言,明白伟大的数学家的时代已成过去,就已经够了。我们现今的工作,就是保存、润饰、修正、选择——而不再是伟大的动力性创造,这与晚期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数学所表现的巧妙的细节修补的特征是一样的。
下面的历史图表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古典数学 西方数学
1。新的数字概念
约公元前540年,约公元1630年
数作为数量数作为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笛卡儿、帕斯卡尔、费马)
(牛顿、莱布尼茨,1670年)
(约公元前470年,雕刻胜过壁画) (约公元1670年,音乐胜过油画)
2。系统发展的顶峰
公元前450~前350年 公元1750~1800年
柏拉图、阿基塔斯、欧多克斯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
[菲狄亚斯、普拉克西特列斯(格鲁克、海顿、莫扎特)
(Praxiteles)]
3。图形世界的内在完成与总结
公元前300~250年 公元1800年之后
欧几里得、阿波罗尼乌斯、阿基米德高斯、柯西、黎曼
[吕西波斯(Lysippus)、(贝多芬)
莱奥卡雷斯(Leochares)]
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1)
(A)观相的与系统的
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去描画出一个历史的意象了,这一意象独立于这样或那样的观察者所寄身的角度和历史时期的偶然性,亦独立于观察者本人的人格——他作为自身文化的一个带有偏私的成员,因其文化中宗教的、理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倾向,而总是想依据某一受到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视角去整理历史的材料,总是想形成一些武断任意的形式,并将历史的外表强行纳入其中,而实际上,这些武断任意的形式与历史的内在内容全然不合。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缺失的,正是与所思考的对象保持超然(detachment)的态度。就自然的方面而言,这种超然很久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当然,对于自然,相对比较容易达到这种态度,因为物理学家显然能够做到不带个人色彩地将他的世界的机械因果图象系统化,就仿佛他本人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一样。
然而,对历史的形式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我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其可能性而已。现代历史学家总为自己能保持“客观性”而自豪,可恰恰是在他们的这一引以为荣的行为中,他们天真地和下意识地显露了自己的先入之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说——在将来的某一天,还可以确然无误地说——迄今为止,一种真正的浮士德式的历史研究还根本没有出现。这样一种研究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超然去承认,任何的“现在”都只是因为有某个特殊的一代人为参照,才成其为现在的;世代的数目是无限的;因此,在看待现在本身的时候,必须像看待某个无限遥远和陌生的东西一样,必须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历史的整个图象中,其重要性既不比其他时段更大,也不比其他时段更小。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将不会运用任何个人理想的歪曲的模量(modulus),也不会设置任何源于个人的坐标系,也不会受到任何个人的希望或恐惧或其他内心驱动力的影响,尽管那些东西在解释实际生活的时候也许有效。还有,这样一种超然的意志——用尼采的话说(据说他本人对这一提法极其不以为然)——能使人们从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去认识到人的全部事实,去看待各别的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在内,如同一个人沿着遥远的地平线扫视绵延的山峰一样。
因此,又一次,有一个与哥白尼的行为相类似的行为有待于我们去完成,这就是以无限的名义摆脱显见的现在的行为。很久以前,当西方心灵从托勒密的世界体系过渡到只对今天的它有效的世界体系的时候,当这后一世界体系把处于某一特定星体上的观察者的位置看作是偶然的而非常规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自然领域完成了那一行为。
使世界历史摆脱偶然的角度,不断地重新界定“现代时期”,类似的这种行为既是可能的,亦是必要的。确实,在我们看来,公元19世纪要比公元前19世纪丰富得多、重要得多;但是,同样是在我们看来,月球也要比木星和土星大得多。物理学家很久以前就摆脱了因相对距离造成的先入之见,而历史学家还没有。我们总是把希腊人的文化视作是与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化有关的“古代”文化。可是,反过来,相对于伟大的图特摩斯——他生活的时代比荷马还要早一千年——的朝廷中那已经趋于完成而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熟的埃及人而言,希腊人不就是“现代人”么?对我们而言,在西欧土地上发生于1500~1800年间的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第三个阶段;相反,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当他们往后看并用4000年的中国历史来评判的时候,西方的那些世纪基本上是短暂的和不重要的插曲而已,比起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那些世纪来,其重要性简直差之万里,在他的“世界”历史里,汉朝的那些世纪才是划时代的。
因此,使历史摆脱观察者的偏见的擎制,将是接下来的全部目标。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这种偏见就体现在,我们把历史看作不过是某个导向偶然的现在的局部过去的记录,至于那一现在的理想和兴趣,则被看作是衡定成就和可能性的尺度。
二
自然和历史,是人的可能性范围里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借助于这两者,人便能整理那诸多的现实性,使其向他呈现为一个世界图象。自然,就其指定生成之物的位置为既成之物而言,它乃是一种现实性;历史,就其参照既成之物的生成过程来整理既成之物而言,则是另一种现实性。一种现实性作为对心智的唤起物,乃是沉思的对象,另一种现实性作为感官的保证,则是批判地理解的对象,前者在柏拉图、伦勃朗、歌德和贝多芬的世界里有生动的说明,后者则在巴门尼德、笛卡儿、康德和牛顿的世界里有所体现。在严格意义上说,认知乃是把已完成的东西称作“自然”这样一种经验的活动。被认知物和“自然”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数学的数字符号已向我们说明,被认知物的集合与机械地界定的物的世界是一回事,物一劳永逸地遵循着定律,物受制于定律。自然便是由定律所统摄的必然性的总和。所存在的只有自然的定律而已。凡是明其职责所在的物理学家,没有一个人愿意超越这些界限。他的任务就是去建立一个有序的代码,不仅要把他在自然图象——对于他本人而言,这图象是固有的——中所能发现的一切定律包括在内,而且要进一步详尽无遗地、不加保留地把那一图象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沉思或内视(vision)——我想起了歌德的话:“应当小心地把内视和观看区分开来”——则是这样一种经验的活动:它就是历史本身,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在完成的过程。那曾经存在的,即是已经发生的,而这就是历史。
每一个发生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它带有方向(“时间”)的标记,带有不可逆性的标记。那已经发生的,从此以后,即是既成的,而不再是生成的;是僵死的,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是属于不堪回首的过去的。我们的世界恐惧的情感就源出于此。相反,一切被认知的事物,都是无时间的meless),既无所谓过去,亦无所谓未来,而只是单纯的“在此”ere),因而具有持久的有效性,其实,自然定律的构成本身所要求的,就是它应当如是。定律和定律所统辖的领域,都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它们排除了偶然性和因果性。自然的定律是僵硬的、故而也是无机的必然性的形式。由此容易看出,为什么数学作为用数对既成之物的一种整理,一直且唯一只与定律和因果性有关。
生成没有定数。我们只能对无生命的东西进行计算、度量和解析,而只要是活生生的东西e living),就必定与现存的东西(livingness)是相分离的。纯粹的生成,纯粹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皆是不可限制的。它超越于因果的领域之外,超越于定律和度量之外。一种深刻的和纯粹的历史研究,决不会寻求与因果定律相一致——或者说,如果它这样做,那它就没有理解自身的本质。
同时,历史,若加以正面处理的话,并不是纯粹的生成:它是一种意象,是从历史学家的醒觉意识中发射出来的一种世界形式,在那一醒觉意识中,生成主导着既成。通过科学方法抽取任何结果的可能性,要取决于既成之物在所处理的题材中所占的比例;依据此假设,在历史的情形中,那些科学方法总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比例越高,所呈现的历史就越是机械、越是合乎理性、越是符合因果。甚至歌德所理解的“活生生的自然”——它完全是非数学的世界图象——也包含有许多死气沉沉的僵死之物,使得他至少要科学地处理他眼前的东西。但是,当既成之物的这一内涵缩至非常小时,历史便会变成几近纯粹的生成过程,沉思和内视就会成为一种只能在艺术的形式中发生的经验。但丁在他的精神之眼的面前看作世界之命运的东西,他通过科学是不可能达致此境的,同样,歌德也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获知他在创作《浮士德》的伟大时刻所看到的东西,普罗提诺和乔尔丹诺·布鲁诺也不可能从科学研究中提取他们的内心视象。所有有关历史之内在形式的争论,其根源皆在此对比中。面对相同的对象或事实集合,每个观察者都根据自己的倾向而对整体产生不同的印象,这一印象是捉摸不定的和不可言传的,它构成了他判断的基础,赋予了他的判断个人的色彩。既成之物被把握的程度,在各人那里是不一样的,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在任务和方法上从来就无法达成一致。每个人都指责别人缺乏“明晰的思维”,不过,这一短语所表达的东西,并非唾手可得的,也不意味着程度的优越性或优先性,而只是意味着种类的必然差异。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科学。
不过,我们不要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想要科学地写作历史的愿望,归根结底会产生一个矛盾。只要真理和虚假的概念还具有有效性,真正的科学就必能达成:这既适用于数学,亦适用于历史科学的艰苦的准备工作,如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筛选。但是,真正的历史视象(在这一点上还仅仅是开始)属于意义的领域,在那里,关键的词不是“正确”与“错误”,而是“深刻”与“肤浅”。真正的物理学家不是深刻的,而是敏锐的:只有当他离开作出假设的领域,回眸那终极的事物时,他才是深刻的,但到了这个阶段,他就已经是一个玄学家了。自然可以被科学地处理,而历史只能被诗意地处理。老列奥波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