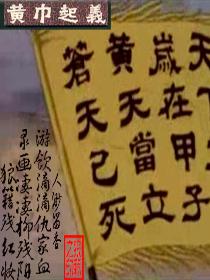西方的没落-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饰中,在马尔斯·乌尔托尔(Mars Ultor)神庙的装饰中,它显得更加凝重,也更为丰富;有机的搭配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致需要总体的研究,而充满表面的倾向也出现了。在拜占廷艺术中——三十年前,里格尔就注意到了它的“潜在的萨拉逊特征”,尽管他对这里所说明的联系没有任何认识——爵床叶饰被细化为无数的卷须饰品,它们被完全无机地配置在整个表面,例如在圣索非亚教堂中。在那里,古代阿拉米人的、已经在犹太装饰中使用的藤本和棕榈叶饰被加在了古典动机上。“晚期罗马”的马赛克路面和石棺边沿中那错花的边沿,甚至几何的平面样式,被引入并最终遍及波斯…安纳托利亚世界,灵活性和怪异性在阿拉伯风格的图案中达到顶峰。这是真正的麻葛动机——及至最后达到了反造型的程度,敌视图画和形体。它本身是无形体的,它脱离了客体,尽管它的无限丰富的图案就描画在这客体之上。这种动机的杰作——一座完全在装饰中展开的建筑——就是伽萨尼王朝(Ghassanids)在摩押(Moab)修建的麦撒城堡(Castle of Mashetta)的正立面。拜占廷…伊斯兰风格(迄今被称作伦巴第风格、法兰克风格、凯尔特风格或古北欧人的风格)的工艺一度侵入整个年轻的西方,并支配着加洛林帝国,这种工艺基本上被东方工匠所实践,或作为我们自己的编织工、金匠和武器制造者的典范被输入。拉韦纳、卢卡、威尼斯、格拉纳达、巴勒莫,是那时这种高度文明化的形式语言的有力的中心;在1000年的时候,当北方一种新文化的形式已经被发展和建立起来时,意大利还整个地被它所主导着。
最后,再看一下有关人体的观点的改变。随着阿拉伯世界感的胜利,人们的人体概念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在“梵蒂冈文集”所涵盖的100~250年期间几乎每一个罗马人的心目中,人们可以感觉到阿波罗世界感和麻葛世界感、肌肉的地位与“目光”的地位作为表现的不同基础之间的对立。甚至在罗马本身中,自哈德良时代起,雕刻家开始坚持使用钻头,这种工具整个地与欧几里得式的对石头的情感是相抵触的——因为凿子产生的是有限的表面,且事实上坚固了大理石块的形体的和物质的性质,而钻头在钻穿表面和创造光与阴影的效果的时候则否定了大理石的那些性质;并因此,雕刻家,不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失去了对裸体现象的古老情感。人们只能看到肤浅的和空洞的安提诺斯(Antinous)雕像——而且这些东西十分确定地是“古典的”。在这里,只有头像在观相上令人感兴趣——它在阿提卡雕刻中根本就不存在。服饰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完全地支配着整个表象。卡皮托利尼博物馆(Capitoline Museum)里的凿像是明显的例子。瞳孔出现了,目光看着远方,因而作品的整个表现不再在于它的形体,而在于新柏拉图主义和宗教会议的决议、密特拉主义和玛兹达主义都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的“普纽玛”的麻葛原则。
异教徒“教父”扬布利柯(Iamblichus)在300年左右写了一本有关神像的书,认为在神像中,神性实质上是在场的,且能对观者发挥作用。与这种形象观念相反——这是一种假晶现象的观念——东部和南部地区则掀起了圣像破坏的风暴;这种圣像破坏运动的源头就在于艺术创造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的。
第七章 音乐与雕塑(1)
(A)形式的艺术
一
高级人类的世界感为自己所找到的象征性表现的最明确的类型,除了我们所拥有的数学的和科学的展示领域及其基本观念的象征主义以外,便是那为数繁多的形式的艺术。形式的艺术,种类繁多且各不相同,在此我们也将音乐划归于其中;如果我们在艺术史研究的领域内来考察这些艺术,而不是把它们置于一个与绘画…造型艺术无关的类别,那我们在理解这一朝着一个目标的演进的意义时就能向前迈进一大步。因为在非文字的艺术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冲动,在我们认识到视觉手段与听觉手段之间的区分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区分之前,是不可能被理解的。去谈论视觉的艺术和听觉的艺术,并不能让我们有所深入。那不是把一种艺术与另一种艺术区分开来的问题。只有在19世纪的时候,才会如此过高地估计生理条件的影响,为的是将其运用于表现、概念或交流。克劳德·洛兰或华托的“歌唱性的”绘画实际上并不只是诉诸于肉眼,如同自巴赫以来的具有空间张力的音乐并不只是诉诸于肉身的耳朵一样。艺术作品与感觉器官之间的古典关系——我们也常常错误地想到这里所讲的这种关系——是与我们所认为的关系完全不同的某个东西,要比我们所认为的简单得多、也物质得多。我们阅读《奥塞罗》和《浮士德》,我们研究管弦乐的乐谱——也就是,我们用一种感官媒介取代另一种感官媒介,为的是让这些作品以其纯粹的精神对我们产生效果。在此,总是有一种力量,把我们从外部感官吸引到“内在感官”,吸引到真正浮士德式的和整个地非古典的想象力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莎士比亚何以要不停地变换场景来与古典的地点一致形成对照。实际上,在极端的情形中,例如在《浮士德》本身的情形中,对作品的描述(亦即对它的全部内涵的描述)实质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音乐中也是这样的情形——在帕勒斯特里纳风格的无伴奏“合唱”(A capella)以及在海因里希·舒策(Heinrich Schütz)的受难曲的“复调合唱”中,在巴赫的赋格曲中,在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中,以及在“特里斯坦”中——我们都活生生地体验到了感觉印象背后的一个完整的别样世界。只有通过这后一种世界,作品的所有丰富性和深度才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以此为中介——通过和声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淡黄|色、褐色、黑色和金黄|色的形象,落日、层峦叠嶂的山峰、暴风雨、春天的景色的形象,以及颓败的城市和陌生的面孔的形象——它才能向我们倾诉自身的某些东西。贝多芬在失听之后写出了他最后的作品,这决非偶然——耳聋只会使他摆脱最后的镣铐。对于这种音乐来说,视觉和听觉同等地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且只是如此。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幻象的艺术享受是全然陌生的。他用肉眼感觉大理石,奥洛斯管(aulos)的浑厚音调几乎是绘声绘色地感动他。在他看来,眼睛和耳朵就是他希望接受的印象的整体的接收器。但是,在我们看来,甚至在哥特阶段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实际上,音调是某种延展的、有限的、可计数的东西,如同线条和色彩一样;和声、旋律、节奏同样也具有透视、比例、明暗对比和轮廓。那使两种绘画区分开来的差距可能要比使某个时期的绘画和音乐区分开来的差距大出很多。请就米隆(Myron)的一尊塑像思考一下这中间的差距:普桑(Poussin)的风景画艺术与同时代的室内康塔塔艺术是一样的;伦勃朗的绘画艺术与柏格兹特胡德(Buxtehude)、帕黑尔贝尔(Pachebel)和巴赫的管风琴作品的艺术是一样的;瓜尔迪的风景画艺术与莫扎特的歌剧艺术是一样的——它们的内在的形式语言近乎同一,以致视觉手段与听觉手段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这些绘画艺术与米隆的雕塑艺术相比,其差距何其之远。
“艺术科学”总是依附于各别艺术领域无时间的、概念性的界定,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证明问题的基础根本没有受到冲击。艺术是活生生的单位,活生生的东西是不能被分割的。博学的学究们首先做的常常就是把无限广袤的领域分割成由完全表面的媒介和技术标准所支配的局部,然后赋予这些局部永恒的有效性和不可变换(!)的形式原则。他们就是这样来把“音乐”和“绘画”、“音乐”和“戏剧”、“绘画”和“雕刻”分割开来。再接着,着手界定绘画“之”艺术、雕刻“之”艺术等等。但事实上,技术的形式语言不过是实际作品的面具而已。风格并不是肤浅的桑泊(Semper)——算得上是达尔文和唯物主义的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种东西,即材料、技术和目的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艺术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是形而上秩序的一种揭示,是一种神秘的“必须”(must),一种命运。它与不同艺术的物质界限毫无关系。
()免费电子书下载
因此,要是依据感官印象的特征来对艺术进行分类,就会在阐述中曲解形式的问题。因为我们怎么可能设定一个“雕刻”种类具有如此普遍的特征,以便承认从那一特征中可推导出普遍的规则呢?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什么是“雕刻”?
再说到绘画。根本就没有绘画“之”艺术这种东西,只要比较一下拉斐尔的基于轮廓线之作用的素描同提香的基于光和阴影之作用的素描,就不会觉得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如果认识不到乔托或曼特尼亚(Mantegna)的作品——是由笔触所创造出来的浮雕——与弗美尔(Vermeer)或戈雅(Goya)的作品——是在涂满颜料的画布上创造出来的音乐——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就不可能把握更深刻的问题。至于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和拉韦纳的马赛克,甚至都没有技术手段上的相似性可把它们归于所认为的同一种类,在蚀刻画与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艺术之间,或在原始科林斯式的瓶绘与哥特式的教堂窗户之间,或在埃及的浮雕与帕台农的浮雕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呢?
如果说一种艺术真的有边界的话——它的心灵的既成形式的边界——那也是历史的而非技术的或生理的边界。艺术是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体系。根本没有一种艺术门类可贯穿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甚至在(例如在文艺复兴的情形中)所谓的技术传统暂时地欺骗我们相信古代艺术规则具有永恒有效性的地方,也根本上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在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中,没有什么东西与多那太罗(Donatello)的雕塑或西纽雷利(Signorelli)的绘画或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正立面有任何关系。本质上,“十五世纪”(Quattrocento)是与同时代的哥特风格而不是其他东西有关。古代希腊的阿波罗类型是受到了埃及肖像画或早期托斯卡纳的埃特鲁斯坎墓|穴绘画的表现方式的“影响”,这一事实所意味的东西恰恰就是巴赫利用外来的主题创作赋格曲的事实所意味的东西——他表明他能用那一主题来进行表现。每一个别艺术——中国的山水画、埃及的雕塑或哥特式的对位音乐——都是曾经存在的,它将随着它的心灵和它的象征主义的消失而一去不复返。
二
有此认识之后,则有关形式的概念便告豁然开朗。不仅技术工具,不仅形式语言,而且艺术门类的选择本身,都被看作是一种表现手段。一件杰作的创造之于个体的艺术家来说——《夜巡》之于伦勃朗或《纽伦堡的名歌手》之于瓦格纳——所意味的东西,正是某一种类的艺术的创造,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之于一种文化的生命史所意味的东西。它是划时代的。除了最纯粹的外部因素,每种这样的艺术都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个别有机体。它的理论、技术和传统全都分享有它的特征,且不具有任何永恒的或普遍的有效性。当这样的一种艺术诞生的时候,当它走完其生命历程的时候,它究竟是消亡了,还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为什么这样或那样的艺术在某一特殊的文化中是主导,或为某一特殊的文化所不具备——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意义上的形式的问题,恰如为什么个体的画家和音乐家无意识地回避某些阴影和和声,或相反,显得特别偏爱某类阴影和和声,以致作者的特性就整个地根基于此,这是形式的另一个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性尚未被理论、甚至当今的理论所承认。不过,恰恰是从这个方面、从艺术的观相的方面说,艺术是可以理解的。迄今还有人认定——对认定所涵盖的重大问题不加些许的考查——在传统的分类框架(其有效性是想当然的)中被详加说明的几种“艺术”是一切时代和地点最可能的艺术,如果在特殊情形中缺乏其中的某一种,乃是由于偶然缺乏创造性的个人、必需的环境或伯乐式的赞助人去指导“艺术”走上它的“正轨”所致。在此,我们所采取的乃是我所谓的把因果原则从既成的世界移至生成的世界的做法。如果对于活生生的东西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对于它的命运及其可能的表现和独特发生的必然性毫无洞察力,人们就得求助于实在的和显见的“因果”来建构他们的艺术史,因而这种艺术史必将是由一系列仅仅表面一致的事件所组成。
我在本书之开篇文字中就已经揭示了一种经由“古代”、“中古”和“近代”诸阶段构成的线性的“人类”进步观点的肤浅性,这一观点使我们对各高级文化的真正历史和结构视而不见。艺术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当的显著例子。人们假定艺术的大量持久的、完全确定的局部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进而依据——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去处理这几种局部的历史,当然,在这里,印度艺术、东亚艺术、阿克苏姆和示巴的艺术、萨珊王朝和俄罗斯的艺术全都被排除在外,它们即便不是全部被忽视,至多也只是作为增补而存在。没有一个人发觉这样的结果恰好证明了方法的不充足;框架就在那里,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且不惜任何代价把事实供给给框架,任其驱谴。就这样,一种无效的起伏不定的进程被笨拙地描画出来。静态的时代被描述为“自然的暂时休止”,当某种伟大的艺术实际上消亡了时,就被称之为是“没落”;而当一种真正摆脱了先见的慧眼看到另一种艺术在另一种景观中产生出来、并表现出另一种人性的时候,就被称之为“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