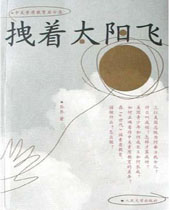千山看斜阳-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着,便听到一个声音趾高气扬地道:“什么?江从鸾你还知不知道好歹?规矩?什么规矩?太子爷的话就是规矩。告诉你,我们家爷今儿远道来了朋友,又说起曾在江南听过这殷小楼的戏,很喜欢他,太子爷已打了保票,今儿接小楼过去招待他。你是怎么着?想让我们家爷在朋友面前丢脸是吧?”
江从鸾的声音更低更柔了,低声下气地道:“小人那哪儿敢啊?只是……这……要客人来了问起来,小人也不好办呢,还请总管爷多体谅小人。”
“体谅?要怎么体谅?为了你扫我们家爷的兴吗?”那人连声冷笑。“今儿又不是做堂会,总共不过三两个朋友,你怕什么?”
说着,那人已是一掌推开了宁觉非房间的门。
江从鸾站在一旁,脸上十分无奈,只得道:“小楼,你还是跟杨总管去吧。”
宁觉非冷冷地瞧着那个满脸骄横的太子府总管,一言不发地便站起身来,走出门去。
被这阵吵闹惊起来的许多小官都又是惊悸又是怜悯地目送着他离去。
走到楼下,一姐端了一碗药递给他,低声道:“小楼,你身子还没好,把药喝了吧。”
那杨总管自也知道上次堂会闹得有多惨酷,这时倒没阻止。
宁觉非却知这是一碗迷药,接过来喝了,轻声说道:“谢谢一姐。”便跟着杨总管走了出去。
江从鸾看着他沉稳的背影,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
他这一走便是一天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又是昏迷着被抬回来的,身上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已是只剩了一口气。
江从鸾正张罗着请大夫来诊治,大门外已冲进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手握长剑,气势汹汹,一把抓住了一姐,怒道:“我问你,那个殷小楼在哪里?”
一姐战战兢兢地看着地上一溜血迹通到楼上,半晌没能说出一个字来。
这时,听到动静的江从鸾从宁觉非的房间里出来,看着那人凶神恶煞的模样,心下虽是惊诧,脸上却仍然挂着温和的笑。他从容地走下楼,温婉地道:“哟,这不是章大人章相爷吗?这是怎么说的?是谁让您老人家这么生气啊?”
“少废话。”右相章纪放开了一姐,手中紧握利剑,怒容满面。“快说,殷小楼在哪里?我今天要杀了这个祸国殃民的贱人。”
第七章
江从鸾看着章纪,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笑脸相迎,柔如春风的他也有点笑不出来了。他轻声说道:“章大人,请跟小人来。”
章纪大步流星地跟着他登上了二楼,进了宁觉非的房间。
江从鸾指了指床上的人:“章大人,你看,这就是小楼。您若要杀,自也可以。不过,您即使不杀,我看他也挨不了多久了。”
章纪看着床上的那个昏迷不醒的血人,微微有些惊愕,随即似乎明白了。他看了江从鸾一眼,沉沉地问道:“是不是又是太子把他找了去?”
江从鸾默默地点了点头。
章纪咬紧了牙关,脸色阴沉,足见其心中的气恼。
江从鸾却什么也不说,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宁觉非的头深陷在枕头里,脸色惨白,竟然比白色的软缎枕面还要白。他的神情十分平静,好似觉得就这么死了也是好事。
章纪凝目注视了一会儿,忽然道:“这人……我要了。他若就此死了,那便罢了。若他活了过来,便送到我府上去。要多少银子,你说就是。”
江从鸾微微有些吃惊,随即脸上浮现出职业性的笑容,配上他美丽的脸容,实是灿若春花。他笑道:“章大人,小楼有您老人家疼,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不过,他是武王爷特别关照过的,小人也不敢做主呢。”
章纪却道:“武王那边,我会去说,你只管照办便是。”说着,便出门而去。
江从鸾愣了一会儿,大夫也到了。他一时也不去想这事,先吩咐人尽心给小楼治伤,调养身子。
到得傍晚,钱琛又来了。他进房略看了一会儿仍然昏睡着的宁觉非,轻轻叹了口气:“这孩子,真是可怜。”
江从鸾陪在他身旁,微笑道:“是啊,只怕要辜负钱爷的厚爱了。”
“无妨。”钱琛却笑着摇了摇头。“你说是章纪要他去?”
“是啊。”
钱琛呵呵笑道:“我听说太子爷最近的一些事情已被人吹风吹到了皇上耳边,皇上今日在朝堂上大怒呢,拿别的事发作太子爷,说他荒唐透顶,不以身作则,反而带坏臣工,嘿嘿,话中有话啊。章大人是皇后娘娘的表兄,今番这场怒气,只怕就是冲着这事呢。”
江从鸾微微一惊:“那……如此说来,小楼送过去了,只怕也是个死吧?”
“他不敢。”钱琛轻笑。“这是武王爷送来要惩治的人,他不敢私自处死他的。虽说他是右相,一品重臣,太子也十分倚重,弄死一个戏子、小官,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过,到底碍着大皇子的面子,我谅他也不会这么鲁莽。”
“那……他要我们送小楼到他府上去呢。”江从鸾有些不解了。
钱琛却笑着摇头:“他也只能这样做,将这孩子拘在自己府中,也算是断了太子爷的念想吧。”
“哦,我明白了。”江从鸾伸手去探了探宁觉非的额头,看着钱琛道。“钱爷,小楼这伤,只怕要将养几天才会好,就不能侍候您了。”
钱琛笑着,却一把搂住了他的腰,在他耳边轻笑:“没关系,有你也是一样。”
江从鸾却嘻嘻笑着,轻轻地滑脱了出来:“钱爷,从鸾已经老了,我这里可有的是漂亮孩子,一定好好侍候你。”
钱琛却正经了一点,轻轻叹了口气:“从鸾,我们相识有十年了吧?你知道我不好这个,咱们去你屋里喝杯茶吧。”
“是,钱爷。”江从鸾低了低头,温顺地笑着,与他一起出了门。
这一次的伤,宁觉非养了八、九天才逐渐好转。不过,到第三天,他会每天夜里强撑着起身,练习走路,然后在白天的时候一直躺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睡。江从鸾看得出他伤得很重,也不去逼他。
这段时间里,醇王淳王朝却经常过来。他恒常穿着贵公子的文衫,也不说身份,只带了一个随从,便潇潇洒洒地走进来,对宁觉非说道:“小楼,我来看看你。”暮色中,他的眉目之间总是笑意。
不知不觉间,秋已深了,窗外总是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寒气一缕一缕地钻进来,将屋里的香气冲淡,冲散,使屋里很是清爽怡人,一点也不像是小官的屋子。
淳于朝喜欢陪着他吃晚饭。当他起不来床的时候,淳于朝就边在桌上吃着自己点的精致佳肴边看着一姐喂他吃,却也津津有味。等他能起来的时候,淳于朝便硬要拉他同桌,口里说着闲话,大部分却是戏文。他懒得听,只是沉默地吃着,不发一言。
偶尔,淳于朝会笑着央求:“小楼,你给我唱一段好吗?”
他会干脆地道:“不会。”
淳于朝看着他那冷冰冰的精致眉眼,只是好脾气地笑着,一点也不恼。
等到他全身的伤口结了痂之后,章纪到底还是派人来将他强行带走了。江从鸾十分无奈,却也不拦,只是对着在厅角守着的武王府侍卫耸了耸肩,以表示自己的无能为力。那两个侍卫自然也不敢乱拦右相府派来的兵丁,只好跑回武王府中报信。
宁觉非被安置在右相府中的一个角落里,管事来警告他不得随便出院子,便没再理会他。
这院子虽然小,却很清雅素静,还种了几竿青竹,风过处哗哗直响,靠墙处有几畦菊花,此时正在盛放,倒是满目缤纷。
一连几天,章纪都没有来,除了有个老妈子来给他送饭外,始终没人来过。
宁觉非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他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可以恢复身体,锻炼体力,再伺机逃走。
天气越来越冷,初冬的冷风也一直没有停过。宁觉非常常站在院中,有时候看看暗绿色的竹叶,有时候看看已经凋零的菊花,一呆就是很久。
屋中是简单的床和桌椅,却布置得比较舒适。窗下的书桌上有几本线装书,他只略翻了一下便不再去碰。里面都是繁体古字,通篇之乎者也,他半点兴趣都没有。
如此过了半个月,他常常站到院门口,看着外面,心想这总不算是违了规矩吧。
远远地看过去,是一个大大的湖,环绕着湖的自然是雕花的亭台楼阁,十分精美。他看着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径,揣摸着会是通向哪里。
这一日,他正在出神地看着远处的高墙,忽然发现有人也正在看着他,于是收回了视线,淡淡地扫了过去。
在湖边的垂柳下,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年轻人,锦衣金冠,气度华贵,身旁跟着几个随从,正是武王淳于乾。
他看着月洞门中站立着的那个美貌少年。
因为瘦削而显得更加高挑,穿着普通的宝蓝色长衫,乌发在风中轻扬,身后是徐徐飘落的竹叶,一张脸在初冬的黯淡天光下苍白如纸,却又晶莹如玉,眼神淡漠,全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
自他看见这个少年的第一眼起,直到那次的堂会,这孩子没有一次不是狼狈万状,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衣饰整齐形容完整的模样,却让他的心里大大地跳了一下。
宁觉非自然认得他,却仿佛早已不记得了,冷漠地看了他片刻,便转身进了院中。
夜色很快便扑了下来。
吃完饭,略坐了一会儿,便有管事的人来通知他,今夜相爷召他侍寝。
宁觉非无话可说,只是遵照着数个人不厌其烦的详细指示,沐浴,更衣,然后躺到床上。
外面的寒意随着章纪的进门而扑了进来。他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床上的人,这才脱掉衣服,吹熄灯,上了床。
两人从头到尾都很沉默。宁觉非固然维持着一贯的寡言少语,章纪也没有说过一句话。黑暗中,只有他沉重的喘息声在屋中回响。高潮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压在宁觉非身上,紧紧地抱着他。宁觉非的肌肤一直是凉的,仿佛连全身的血都是冷的,无论身上的人怎么折腾,根本就不会热。
寒冷的夜色里,两人仍是一声不吭。
忽然,有人在门外急急忙忙地高叫:“相爷,相爷。”
章纪转过了头,有些不耐烦地问道:“什么事?”
门外的人虽然急,却口齿清楚:“相爷,边关急报,北蓟皇帝与皇后御驾亲征,率大军猛攻燕北七郡,游将军虽全力守御,但寡不敌众,已经全线告急,现遣人回朝求援,皇上急召相爷前往商议对策。”
章纪一听,立刻跳下了床,边穿衣服边道:“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外面的人答应了一声,便静静地候在一边,待章纪打开门出去,立刻服侍着他急步离开。
虽未受伤,宁觉非却觉得很疲倦。他将被子拉上一点,紧紧地裹住自己,然后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第八章
自这一夜开始,章纪几乎夜夜都要到宁觉非这里来。他的情绪显得很混乱,心里似乎窝着火,在床上的动作十分粗野,不过倒也没什么虐待的癖好。
过了几天,章纪好似忙着,无暇分身,于是有管事过来叫了宁觉非,将他带到了章纪的书房。
这是宁觉非到这里后第一次走出那个小院,虽然已是夜幕四合,他仍然迅速地借着沿途挂着的灯笼那微弱的光线观察着四周的地形,根据道路的宽窄、形状、走向和沿途种植的花草树木来分析右相府的结构。
不紧不慢地走了一会儿,便来到了章纪的小院。
推开门,管事低头躬身,恭敬地禀报:“相爷,他来了。”
章纪“嗯”了一声,低声说:“进来吧。”
宁觉非便稳稳地迈步走了进去。
屋里还坐着两个人,穿着武将服饰,此时面红耳赤,似是在与章纪激烈争执,这时看到进来的是个弱不禁风的美少年,倒是一怔,一时说不出话来。
章纪对着宁觉非一摆头:“你过去坐着就是。”
宁觉非便坐到了角落里,仍然非常安静。
章纪本也心浮气躁,这时看见他,心里一静,缓缓地吁了口气,沉声说道:“你们放心,投降是万万不行的。他既是太子,更是必须以国家兴亡为重,岂能一心想苟安于世?我明日便会在朝上表明态度,要求即刻派兵增援燕北,不能坐以待毙。”
那两名武将一听,都是喜形于色,其中一人却略有些犹豫:“相爷,您这样做,会不会让人认为您倒向了武王那边?游玄之现在一力主战,心急如焚,人人皆知他有私心,不过是怕他儿子有个什么好歹。您这样一表态,岂不是会让武王爷那边的那起子小人利用来推波助澜,对殿下会不会不利?”
章纪哼了一声:“若是太子爷抢先提出进兵,我们便可利于不败之地,偏偏他……唉,让我们现在缚手缚脚,被动至极。不过,事有轻重缓急,现在若真如太子爷的意思,投降北蓟,上表称臣,那咱们便成了亡国奴了,此事万万不可行。为今之计,要将敌人先行击退,再安内政。”
那两人边听边点头,情绪显然安稳下来,略想了想,又道:“那……大人心里属意由谁率军?”
“此事不易办啊。”章纪慨叹。“若是荐我们的人去,只怕与游虎心生嫌隙,反是祸患,若是听凭游玄之荐他们那边的人去,只怕他们的势力更是坐大,将来就不好收拾了。”
其他两人也是显得苦恼万分。
宁觉非看着窗外的朦胧夜色,似是漠不关心,他们的对话却句句听在了耳中,不由得好笑。敌人已大军压境,这边还在算计着争权夺利。
三人又嗟叹商议了半晌,章纪方道:“若实在无法可想,老夫便请缨,亲自率军前往边关。”
那两个将军一惊,随即道:“大人舍身为国,令人敬佩,末将愿为大人马前卒。”
章纪点头微笑,似是放下了心头大石。
那两人于是起身告辞。章纪将他们送了出去。两人连声逊辞,要他“留步”。章纪略客气了一下,片刻之后便返身回来。
宁觉非仍然坐在那里,一直没动。
章纪走到他面前,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忽然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轻声道:“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安静?”
宁觉非抬眼看着他,神情间仍是十分淡漠,双唇紧抿,一言不发。
章纪放开了他,坐到桌边,看着他问道:“你在想什么?”
宁觉非没回答,只是转头看向了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