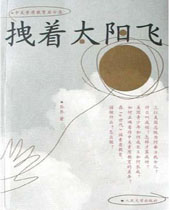千山看斜阳-第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宁觉非在小苍山下的望北苑中住着,已是心静如水。
此时已是盛夏,此地与蓟都相比,地势偏南,又是平原,对他的身体大有好处。望北苑中遍植花草树木,还有一个小小池塘,很是清幽怡人,便是树上聒噪不已的蝉声都让人不觉得讨厌,反而使园中更显宁静。
宁觉非每天便是吃药,浸药浴,让云扬按摩,睡觉。他绝口不提政事军事,也从来不问云深,醒来时便看着窗外的风景,有时候会试着起身走两步。
云深对他的表现感到纳闷,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实在没底,慌得厉害,便想找点事给他,也试探一下他现在的态度。
于是,澹台子庭便护送荆无双前来看他。一同跟来的,还有江从鸾。
宁觉非一见他们,情绪倒是活络了些,脸上有了点笑容,一迭声地请他们坐,又吩咐看茶。
这三个人看见宁觉非现在的模样,都有些发愣,随即便感到心疼。
江从鸾很自然地走到他床边,伸手贴在他的额上,试了试热度,这才放下了心,从婢女的托盘里端过茶来,却道:“觉非,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现下怎么样?好些了吗?”
宁觉非笑道:“好多了。”
荆无双神情复杂地看着他,犹豫半晌,方道:“觉非,我……真没想到,南楚会亡在你的手里。”
宁觉非温和地道:“大哥,南楚是亡在南楚朝廷手里的。今日不亡,明日必亡。不是北蓟,也会是西武,或者是别的什么国家。这些年来天怒人怨,是因为什么,大哥你不会不明白吧?”
荆无双坐在床边,轻轻叹了口气:“虽说如此,总是自己的国家……”
宁觉非轻声劝解:“大哥,改朝换代,其实是平常事,谁当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你看,朝中人虽然变了,但山河依旧,百姓平安喜乐,你也依然可以当它是你的国,你的家。”
荆无双沉默了一会儿,低低地道:“贤弟,愚兄宁死不当亡国奴。”
宁觉非温和地道:“大哥,没人会逼你为奴。你若心系天下苍生,便可入朝为官,造福于民。若想眼不见为净,你也大可放舟五湖,寄情山水,四海为家。”
荆无双冷冷地瞧了一眼身边的澹台子庭,对宁觉非说:“只怕你的话做不了准。我若一日不降,他们便一日不会放我离开。”
澹台子庭已改换了北蓟官服,风度气质却仍是南楚格调,显得温文尔雅,这时嘻嘻笑道:“荆将军放心,只要是宁大将军说出的话,陛下都认,一定算数。你要走,我也不拦你。不过,我劝你不如留在朝中,也可以监督我们,以免我们荼毒百姓。待将来亲眼看到四海升平,天下大治,咱们再与宁将军把酒戏说今日事,是非功过,那时才见分晓。”
宁觉非笑了笑,却没再多说什么,似是让他自己决定。
荆无双听了澹台子庭的话,心里一动,微微低头,反复思量起来。
澹台子庭十分诚恳地道:“荆将军,皇上敬你忠义传家,世代良将,皆以万民福祉为己任,实是诚心留你。你不用上降表,也不必奉承拍马,我们绝不会用这些形式来侮辱你。皇上希望你能够留在朝中,仍做护国将军,你可以不护朝廷护百姓,可好?”
荆无双听到这里,以身殉国的念头已然动摇。他犹豫着,看了一眼宁觉非。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江从鸾已经拿过来一个靠枕,将宁觉非扶起来,让他倚着床头,坐得舒服一些。宁觉非对他笑了笑,却没有再说“谢谢”。江从鸾顿时喜心翻倒,眉梢眼角全是笑意。
此时,宁觉非看着荆无双的眼神,笑着点头:“大哥,你一心想有个太平盛世,如今便是开端,不妨依澹台将军所言,暂且留下,以后若是你呆不惯,也随时可以离开。”
“是啊。”澹台子庭趁热打铁。“荆将军,无论何时,如果你想辞官,我们都不会强留。”
荆无双看了看满脸诚意的他,又看了一眼面带笑容的宁觉非,终于长叹一声:“也罢,我便暂且留下。”
澹台子庭立刻喜得手舞足蹈:“哈哈,太好了,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荆无双啼笑皆非:“孙将军,澹台将军,在下从未与你并肩作战过,只与你在鲁阳城外曾经有过并肩作战的打算,不过,那一战我可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澹台子庭笑嘻嘻地道:“我也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江从鸾实在忍不住,嗤地笑出声来。
宁觉非也笑,大声道:“云扬,去告诉厨房,好好整一桌拿手的菜来,我陪大哥喝两杯。”
荆无双看着这个令他一直心仪不已的兄弟,回首家国,终是无比感伤。
七十五
半个月后,澹台牧再次颁下圣旨,进行了一系列的封赏。他依宁觉非当日承诺,封淳于乾为靖王,食亲王双俸,移居原静王府,封淳于宏为理王,移居原武王府。淳于朝仍为醇王,淳于翰仍为景王,府邸家产均被保留。
各部大臣虽然早就纷纷上了降表奏折,称颂新君,但澹台牧只封了三个人,一是游虎,仍为定国将军,二是荆无双,仍是护国将军,三是李苏,还做镇南将军。这三人曾经同为南楚柱石,一镇西北,一镇东北,一镇西南,便为南楚保住了十年太平。如今三人齐齐投入北蓟,天下文人闻之,也只能摇头嗟叹。
不过,对这几人的封赏不过只是令南楚万民为之心安,真正引人注目的却不在此,而是威震天下的“烈火将军”宁觉非。
澹台牧专门下诏,历数宁觉非的功绩,赞他忠君爱国,泽被万民,敕封其为一字并肩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总理全国军事,并赐免死金牌,准皇宫骑马,殿前带刀,赏十万户,又赐黄金千两,翡翠明珠美玉两斗,骏马千匹,其余马牛羊无数……
宁觉非躺在床上,听古英滔滔不绝地读着给自己的封赏,眉头越皱越紧。
江从鸾一直在屋外回避,听着里面没了声音,这才端着一碗药进去。
宁觉非撑起身,从他手中接过药碗,一口喝下,这才躺了回去,叹道:“我要这些干什么?古英,你马上替我写折子,把这所有封赏全都推辞了。”
古英吃了一惊:“将军,这是为何?”
宁觉非清晰地道:“你先写,我万分感激陛下的抬爱看重,然后说我体弱多病,不堪重负,恐难以担当大任,为免误国误民,请准予辞官。”
“将军,这……”古英一脸为难。
宁觉非看着他:“古英,你现在仍是我的师爷,不打算听我的吩咐了吗?如果你不写,也可以,就回云大人那儿去吧,不用再呆在我这儿了。”
古英立刻躬身道:“是,将军,古英这就去草拟个折子。”
待他出去后,宁觉非看向江从鸾,温和地说:“从鸾,你这就离开吧。”
江从鸾大惊失色:“觉非,你这是何意?难道是厌弃我了?”
“怎么会?”宁觉非轻笑,拉过他的手,让他坐到床边。“别这么不自信,先听我说……”
等古英拿着拟好的奏折走回来时,江从鸾眼圈红红地站在墙角,背对着宁觉非,显得十分委屈。
古英有些疑惑地看了看他,宁觉非却道:“不用管他。折子拟好了吗?”
江从鸾霍地转身,微着颤道:“觉非,不,宁将军,从鸾想回乡去看望父母,这便告辞了。”
宁觉非微笑着说:“这样也好,如今天下初定,你父母不定有没受惊,你回去看看也好。古英,你从我的俸银里拿一千两出来,赠给从鸾,他照顾了我这么久,我很感激。”
江从鸾一听,顿时泪如泉涌,低低地道:“不用了,觉非,我照顾你……不是为了钱。”
古英听他要走,自是正中下怀,马上快手快脚地出门,拿过来一张千两银票,诚恳地递给他道:“所谓穷家富路,你既是要单身上路,身上总要有点银子,这是将军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江从鸾低着头,半晌,才伸手接了过去。他对着宁觉非躬身施了一礼,随即匆匆走了出去。
宁觉非看着他的背影,轻叹一声。
当晚,江从鸾便离开了望北苑。
等到古英把折子递到临淄后,宁觉非似是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又是常常昏睡,人也变得十分沉默。
三日后,云深快马自临淄赶来,出现在他的面前。
宁觉非看着他,见他也瘦了不少,便道:“你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有什么事让人过来说一声就行了,也不必自己亲来。”
云深走到床前,声音极柔和,情绪却有些激动地问:“觉非,你上表辞官,让陛下很是不解。你如今功高盖世,威名播于天下,又如此年轻,正是大展鸿图的好时候,却为何想激流勇退?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想要什么呢?”
“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毫无意义。”宁觉非躺在床上,微笑道。“我现在只想告老还乡。”
云深看着他温和平静的笑脸。在这一世,他不过才二十一岁,却已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雄心壮志、血气方刚。此时此刻,他眼神沉郁,神色平静,虽是满脸病容,却更显得不食人间烟火,一派仙人之姿。他忍不住过去,紧紧拥抱住他,轻声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宁觉非没力气挣脱他的怀抱,只是淡淡地道:“回不去了。”
云深听了,心里一酸,眼泪落了下来。他忽然热血上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抬头吻上了宁觉非的唇。他辗转地深吻着,热泪一直扑簌簌地滴到宁觉非的脸上。
宁觉非迟疑了一下,伸手想推开他。
云深却用力圈住了他,不肯与他分开。
宁觉非在心里轻叹,犹如有一根尖针在心里攒刺,疼得厉害。
良久,云深抬起头来看着他,诚恳地说:“觉非,这里就是你的家乡啊。临淄现在是北蓟的都城了,你可以在这里开开心心地过日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可以长相守,不分离。”
宁觉非听了,只是看着他,抬手缓缓地抚过他的眉眼,轻轻地笑了:“难道北蓟还想取西武不成?”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炸得云深耳边嗡嗡直响。他呆呆地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笑脸,半晌才喃喃地道:“觉非,觉非,你这话……却是何意?”
宁觉非只觉得十分疲倦,胸腔闷痛,四肢发麻。他不想再费神兜圈子,平心静气地说:“云深,你成亲吧。去生儿育女,过你自己本来该过的生活。”
云深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抱着他的双手忽然攥紧了,一时间浑身都在微微颤抖。他盯着他,沉沉地道:“觉非,你是不是听了什么流言?或者产生了什么误会?无论是什么,你都别闷在心里,说出来啊。圣人云:‘不教而诛谓之虐。’你一向宽以待人,却为何要如此苛待于我?我到底做了什么事,竟尔会让你心脉纠结,一病再病?觉非,你一直是个铁铮铮的爽朗汉子,却为何不肯对我明言?”说到这里,他再也撑不住,身子一软,伏到宁觉非身上,一时间泪落如雨。
宁觉非望着屋顶,心里只有自嘲的苦涩。如此尖锐的羞辱,让他又怎么说得出口?难道要他效那等愚夫愚妇,很白痴地问:“你什么要骗我?”就算人家是骗,自己上了当,也不过是自己蠢,与人无尤。
云深叹息着:“情到深时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
宁觉非听了,不由得苦笑:“这话真不知是说你还是说我。”
云深紧紧搂着他,连声问:“觉非,觉非,难道你后悔了吗?”
宁觉非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地道:“以前,没有。”
“那现在呢?”云深抬起头来,灼灼地盯着他。
宁觉非笑得十分苦:“是,你从来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你不悔。是我后悔了。”
云深看着他,神情凝重,眼中满是忧伤:“觉非,你话里有话,不妨明说。你我之间难道还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为什么要后悔?”
宁觉非却实在不想提起,只是说道:“云深,是我后悔了,我想与你分手。”
云深急切地问道:“为什么?”
宁觉非沉默着,不知该怎么说才妥当。
云深试探着问:“是你……想娶妻?”
“我娶妻?”宁觉非觉得此言极为荒唐,不由得仰天长叹,笑道。“我早已说过,我是终身不娶的。”
“那是为什么?”云深那两道秀气的眉紧紧皱在一起。“难道你还在为过去的事心存芥蒂?我都说了那不是你的错,你完全不必放在心上,想都不要再去想,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根本不是为了过去那些事。”宁觉非这时已恢复了平静。他垂下眼帘,声音低沉。“两情相悦,是要讲心的,身体如何,反而不重要。”
“是,是要讲心。”云深难以置信地盯着他。“难道……觉非,你对我已无心?”
宁觉非只是苦笑,却不肯再多说。
云深黯然神伤,转眼看向了窗外,茫然地喃喃自语:“你想让我对你说,你既无心我便休?”
宁觉非的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竟是觉得再贴切不过,于是闭上了眼,冷淡地道:“是,你既无心我便休。”
云深身子微微一颤,目中又是热泪盈眶,却强自忍耐着不肯落下。良久,他才点了点头,静静地说:“我明白了。”
宁觉非感觉着他伏在自己身上的重量,竟觉得不胜负荷。他是真的累了。
云深呆呆地起身,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直看着窗外。
屋子四周绿树成荫,有不少鸟儿在其上筑巢,清脆的啾啾声流淌在风中。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他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他的国师府,宁觉非躺在树下。那时候他也在病中,可他们却是两情相悦,亲密无间。那样的甜蜜,为什么竟会一去不复返?
他翻来覆去地想着宁觉非前后态度的变化,似乎便是在澹台昭云的生辰之后。难道是他听到了什么?产生了误会?
云深大致推测明白了前因后果,思来想去,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与他分开,于是轻声说道:“觉非,我曾经与昭云订过亲,本来也打算等她长大后就成亲的。可是,我看到了你。我倾慕你,关心你,一半是国家,一半也是为自己。一开始,我与你在一起,或许更多的是为了北蓟,为了天下,连我自己也以为如此。然后,你为了我,不惜以身犯险,我为了你……也什么都可以牺牲,这……应该就是真挚的感情了吧?可我当时愚钝,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觉非,当你开始冷淡我,疏远我,开始病重的时候,当我以为从此会失去你的时候,实是痛不欲生。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是爱你的,觉非,我是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