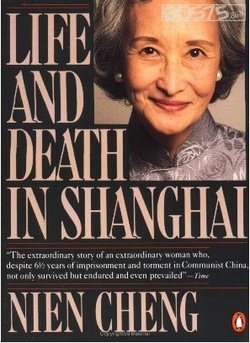上海·鼓声迟 by生还-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平静下来,关了灯,努力睡觉。
隔两天云逸回请小乔和路东伟,就把嘉兰也叫上。
菜的口味重了些,大多放了辣椒,只有一个汤,用冬瓜和几种菇类烧成。嘉兰看见皱皱眉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云逸,云逸小声说,他们都是四川人。
果然那两个人吃得开心,小乔笑说,我还以为云逸不会做饭,没想到厨艺这么好,我平时都不吃排骨的。
云逸一直在喝汤,微笑说,谢谢,帮你盛碗汤?
小乔喝一口汤,又说,哎呀,真好喝,你用什么佐料?云逸笑,葱、姜和盐罢了。小乔睁大眼,你连油都不用的?云逸一指,喏,我扔了一块排骨进去。
路东伟插嘴,云逸,你男朋友不在这里?
小乔和她住了这么久,彼此都不过问这类的事情,没想到路东伟这么直接。云逸笑笑,平静地道,我没有男朋友。
路东伟惊讶,你这样的女孩子,不会没人追啊,你眼界太高了罢?
云逸含笑,说,没遇见合适的,也没办法。
嘉兰替她圆场,说,云逸不交男朋友的。那两个人看着她,她喝一口汤,笑,她只交女朋友。路东伟马上拉住小乔,幸亏我来得及时啊。大家就笑。
回到房间里,嘉兰就皱眉头,说,那个路东伟,真不知道轻重。云逸叹口气,轻轻说,很多人觉得,这么问是关心,他们生性直爽罢了。嘉兰说,反正我不喜欢他。云逸看着她笑,说,别这样,人家也不错,模样过得去,体贴女朋友,讲浪漫能千里迢迢带花过来,讲实际还会洗手做羹汤,还能再要求什么?
嘉兰问,什么千里带花?云逸就把生虫子的玫瑰花讲给她,说,男孩子会哄人,大概还是油滑,但是有一点傻的浪漫,反而比较动人。嘉兰沉默一阵,道,云逸,你心思简单,你不知道,许多男生也知道适当装傻的。又笑,人家的男朋友,真傻假傻,我们操什么心来?
云逸说是。
过了一阵子,嘉兰忽然低声说,云逸,我要去北京一趟。
云逸问,做什么?去多久?嘉兰脸上微微一红,笑着去圈她脖子,中途又停下来,说,我也不知道多久。云逸忽然就明白了,从心里替她高兴,说,恭喜,良辰宝贵,要尽情享受。
嘉兰红着脸,笑得甜蜜,说,哎,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好,我一直以为绝对不会喜欢他,可是就这么奇怪。她搂一个抱枕在怀里,说,怎么办呢?我还有三年在上海,他又在北京不能过来,我怎么能喜欢他呢,不是自找苦吃么?
云逸笑着拍拍她,莫道相思苦,相思苦也甜。
嘉兰娇憨地笑。又说,我走了,就剩下你一个,希望那个老曲懂得抓住机会,趁虚而入。
云逸知道她是好意,可是事情并不是她所想的那样,她只能笑笑,说,嘉兰,不是的,我觉得老曲人很好,但是,跟喜欢没有关系。
嘉兰见她的表情,知道是真的,心里有些失望。云逸,你要勇敢些,她说。半晌,又小心地问,云逸,你是不是,还没有忘记初中的事情?
有那么几十秒的沉默,灯光下云逸的脸很平静,可是空气中有什么东西紧张起来,嘉兰似乎能感觉到一些微小的尘埃的厮杀,无声地,惨烈地,你死我活。她后悔问出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角落,存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不能碰,一碰到,就会放一些东西出来。
灰尘,血,憎恶,仇恨,如此种种。
云逸笑了笑,嘉兰,我如果说忘记了,你一定不相信,的确也不可能忘,但是,已经对我没有影响了,我都原谅了,包括我自己,毕竟那时候都小。
嘉兰不再说话。也许她真的原谅了,可是也不见得没有影响。这么多年,她绝口不提在烟城的生活,不提在烟城的任何旧人,包括对自己,从来没有一起回忆过往事,怎么会那么容易释然?
云逸说,你看,我现在看人多客观,就像对路东伟,我都是看别人的好。
嘉兰说,那我就放心了。
路东伟,那样的男孩子,如果云逸肯看他的好,也是因为关声罢。她记得那时候云逸考高中到涡城,关声随即转了过去。他认真,诚恳,开朗,而且生得好看,对云逸又是那么真,她以为他过去之后,多年相伴,他们会顺理成章走到一起,可是竟然没有。
她大三那年寒假回到烟城,在街上遇见关声。他们聊天,小心翼翼说很多话,却谁都不肯提云逸。过了很久,关声忽然问,你最近,有张云逸的消息么?她看着他,说,我还跟她联系,她很好。
买年货的人很多,在身边挤来挤去。关声落寞地笑笑,说,她大概就只跟你联系了。他个子高,在人群里,很显眼,连寂寞都那么突兀。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她心里忽然冒出这么两句话。关声说,杜嘉兰,我以后都见不到她了,请你,替我照顾她。
那时候她才知道云逸已经不跟他联系。那么多年,原来不爱还是不爱,感动与负疚都代替不了爱,而她那么决绝地与关声断绝联系,大约也是为了彻底与初中时代的记忆告别。
她理解云逸,也更加明白云逸肯和她来往,是多么看重她们的友谊。所以有时候,她固守原则,并不过问许多事情。
她说没有影响了,就当没有影响了。
正文 没有经过的人不会明了
嘉兰走了之后,云逸寂寞很多。晚上回去,一个人呆着,也懒得做饭。那阵子天气无常,她又感冒,半夜里发起烧,睡不着,睁着眼睛打量天花板。浑身绵软,疼痛的碎粒在身体里蠕动,心里反而平静。
她给许文发短信,春天渐深,人人都知道不辜负好时光,留下我一个人,真孤单。
许文回短信,妞,我支持你去谈一场恋爱。
云逸笑,啊妞,难道你不知道,其实我这么多年来爱的是你?
许文善解风情,回答,亲爱的,我一直都明白,可是老万跟了我那么久,我不忍心抛弃他,妞,只怪你和我相识得太晚,让我们来生再续缘。
云逸继续做怨妇状,一切都是借口,其实是爱得不够,你说,他哪里比我好?
许文回,噢,他比你先到。
云逸将手机合上,把脸埋在被子里笑。她不知道多庆幸有这样的朋友,容得她胡言乱语,并且默契配合。
许文是高她两届的师姐。云逸入校那年,美院与江城大学合并。许文在江城大学念应用数学,极其明敏的女孩子,长发,圆脸,皮肤白皙,有一双灵动的眼睛。她是美术社的元老,逢到活动,就笑笑地站在一边,贤淑温婉的模样,是云逸最喜欢的女孩子长相。
那时候她升大二,心血来潮报了美术社。入社有考试,社长是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给她出的题目是《曾经》。云逸画了一幅牡丹,大片留白的水墨,只托起花朵的一片叶子,用了暗的浅石青。社长看了半天,说,这么淡。仿佛并不欣赏。许文在旁边歪着头看了一眼,打量一下云逸,微笑说,你喜欢在石青里面调金粉?
云逸笑。她点点头,道,淡极始知花更艳。
云逸接口,十分红处便成灰。
许文走过去,笑着说,我见过的人里,只有你当得起这幅水墨牡丹。又说,他必定是个很精彩、很叫你眷恋的人。
云逸问,谁?
许文一笑,那片叶子。
云逸后来想,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人的,未必性格很像,但是内心某一处,却能毫无障碍地彼此会意。
那时候许文已经和老万在一起将近两年,但是很少见他们同进同出。大四学校管得宽松,她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小小的一室一厅,一个人住,倒也清爽干净。客厅其实作了画室,但是颜料盘子收拾得整齐,东西安置得井井有条,墙壁也干净,是习惯程序的人惯有的洁癖。云逸自己也是有一点看不得东西凌乱,看了更觉得投机。
她的厨艺就是在许文的厨房里突飞猛进。
许文第一次看她炒菜,只放少许油盐,其余一律省去,笑道,你口味真清淡。
云逸说,何必放太多调料,蔬菜有自己的味道,调料放多了,菜的味道就压下去了。
许文摇头,你油盐都不肯多用。她说,人家说口味轻的人一般清心寡欲,其实我倒觉得,表现得清心寡欲的人有两种,一个是真的清心寡欲,另外一种,是有着隐秘而又强烈的欲望,这个欲望太遥不可及,也许注定无法实现,于是宁愿把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跟小孩子撒娇一样,不给我这个,我就什么都不要,怎么都不能哄好。
她看着云逸,笑问,你是为了什么愿望呢?
云逸也笑,坦白,大约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一个人。
她问,你觉得你舍了别的,上苍会在那个人身上补偿你么?用其他的不完满,换取唯一的一个完满,有这个可能么?
云逸不说话。许文叹了口气,低低说道,如果可能,我宁愿以所有其他爱我的人,换自己没有看到那一幕。她语调艰难,说得也苦涩,嘴角一个笑,是力不从心的倔强。
那天许文情绪低落,下楼买了啤酒,两个人关在房间里喝。
到后来都有些醉意,许文眼睛里开始有泪光闪动。
她讲她第一段感情。高中时候,十七岁遇见的男生,唱歌很好听,于是就动了心。她是全校风头最劲的女孩子,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年级第一,那么明朗骄傲。而他习惯性地逃课,晚自习翻墙出去上网,打游戏,在外面喝酒游荡。可是还是爱了。替他整理笔记,帮他补作业,等他看着她温柔一笑,说一句“没有你怎么办”。
第一次牵的手,第一个认识的怀抱。
直到高三的第一个学期。她去他外头的房子里找他,打开门,看见纠缠着的两个身体。竟然是吓得说了句对不起,急急逃下去。大太阳晒着,跑得气喘吁吁,心怦怦地跳,一切恍惚迷离。对自己说,是做梦么?还是走错了门?不会是他不会是他。可是就是他。
末流肥皂剧的情节,真不敢想,就会出现在自己身上。
可是云逸,你知道最悲哀的是什么?许文端起酒,是几年之后,我想起来他,会觉得非常不堪,我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我怎么会那么愚蠢?她哈哈地笑,云逸转过头。
然而当时怎么能放下呢?每一夜每一夜,梦境重复的都是那一幕。整夜整夜地失眠,谁看过来的目光都带着嘲笑。是自己不够美么?那女孩子并不比她好看。是自己不够爱他么?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样更爱。
唯一的理由是,也许她太温顺。爱到那样的地步,将自己降低成他脚下的尘埃,可是他们习惯将目光向上,谁还会低头,赐你一点爱惜?
就那么过了一年,原本该考进最好的学校,却沦落到江城大学。但是庆幸得是,还不至于太不堪。她见过一些女孩子,抽烟,刺青,很夸张地笑,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每次看到都觉得心疼与不忍,比如踩到一脚污泥,擦干洗净也就算了,何苦再把它涂个满身?
她还是哈哈笑,说,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
云逸默默与她碰杯。
想起自己高中的时光。
考进涡城,与所有人保持距离,永远含着一点客套的笑,温和背后审视的目光。
对所有的男生都有一种额外的宽容,似乎是平易的,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内心深处居高临下的悲悯与抹不去的淡淡的厌恶。怎么试图说服自己,都是徒劳,只好尽力掩饰。甚至包括对关声。
她曾经问一个追她两年的男孩子,你知道关声?那男孩子点头,说,就是那个老在走廊上等你的,高高的男生。她含着笑,继续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和他做朋友?男孩子摇头。她笑,因为他知道分寸,不该说的话一句不说,不该做的事情从来不做。
关声转学到涡城的时候,她就告诉他,我一定要考大学的,这是我这三年唯一的目标,我要平静,挡我者,死。她说关声,别人不明白,你会明白的。
她语气温和,却自有一种决绝的力量。而关声始终含笑,温柔地看着她。爱一个人,是什么都能容忍的罢,包括这样明目张胆的威胁。但是多可惜,她是那么理智的一个人,她很清楚,自己不爱他,也不能爱他。
她也始终是平静的,直到高三暑假,她遇见沈之城。
之城是不同的。他不是同龄的男生,没有他们的狭隘与恶劣。他关心她,只是纯粹的关心,关心的是她的心,而非身;他拍她的头,揉她的头发,只觉得亲近,而没有狎昵;他让她觉得自己可以是抽象的一个人,没有身体这个累赘的皮囊,而只有清洁的灵魂。如果她还小,如果她已经鹤发鸡皮,如果她是个顽皮的少年,如果她是一棵树,她相信只要那躯壳里住的是一个叫张云逸的灵魂,他都会走过去,拍拍她的头,自然而然地说,丫头,别不开心了。
她一直对试图接近她的人心怀戒备,遇见他,才对自己说,这是安全的,于是放下所有疑虑,在他面前,做一个最真的自己。
可是之城。
可是之城啊。
她记得有一个男生,死缠烂打追她一年。她那时候不知道轻重,以最伤自尊的方式拒绝了他。最后一次他与她说话,他说张云逸,你也会爱上人,我祝你们,永远没有好结果!
她至今记得他的表情,那么怨毒。
这就是她中的咒语。
大一暑假她病好了之后,就很少见到之城。他在医院上班,大夜班小夜班,轮休的时候闷头睡大觉。云逸也不去找他,他跟父母同住,她若去了,还要叫爷爷奶奶。
总归觉得别扭。
就窝在三楼的画室里,调各种各样的颜色。一样一样试过去,总是不满意。也不懊恼,不过是换了颜料重来。偶尔也下厨,做一两道菜,煮一个汤,味道好坏不说,姑姑吃着,还是高兴的。
之城又来的时候,云逸在画室。他见她套了一件白色大T恤,七分裤,头发松松挽着,埋头对付一堆颜料。听到声音,她抬头,看见是他,笑,你来了?先坐。
她腮边有一抹淡淡的黄,才孵出的小鸡仔的颜色。之城走过去,看见颜料盘子旁边放着一盒子金色眼影粉,笑说,小姑娘长大了,用上眼影了?
云逸抬起头,瞥他一眼,道,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用那么麻烦的东西?我拿它调颜色。
他问,调好了么?什么颜色?
她拿一只中毫,蘸了一点,在画布上涂了一抹,问,怎么样?
是暗一点的石青色,隐隐闪着光泽,大约就是那眼影粉的功效。云逸说,眼影粉不太好,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金粉,哪里有呢?
之城问,这么冷僻的颜色,你拿它